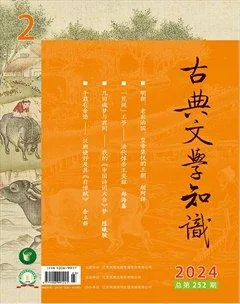《庭中有奇樹》中的記憶與時(shí)間
李子瞻
在《古詩十九首初探》中,馬茂元認(rèn)為《庭中有奇樹》“別經(jīng)時(shí)”的感慨,是全詩用意的歸宿。為何“別經(jīng)時(shí)”是全詩情感的落腳?這或許是由詩中的記憶和時(shí)間不斷地相互作用造成的。
詩作首句開門見山,直接交代 “庭中有奇樹”,這與耳熟的童謠“從前有座山”仿佛有異曲同工之處,都揭示了在某時(shí)某刻有某個(gè)故事發(fā)生,引起讀者的好奇和閱讀欲望—為什么庭中樹“奇”?樹究竟“奇”在何處?進(jìn)而通讀全詩: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fā)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yuǎn)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jīng)時(shí)。(馬茂元《古詩十九首初探》)
庭中樹平平無奇
不難發(fā)現(xiàn),庭中樹其實(shí)不奇,只是一棵種在庭院里會發(fā)芽、會開花的樹。主人公說樹奇,是因?yàn)樗麄冊诖顺ο鄬Γ瑯湟蛴洃浐蜁r(shí)間而奇。特別的不是庭中樹,是作者的記憶,是獨(dú)屬于主人公和她所思之人的記憶。在這個(gè)庭院中,在這棵樹下,他們產(chǎn)生了共同的記憶,記憶是確定不移的,是彌足珍貴的。記憶停駐在時(shí)間里,而時(shí)間又是不斷流動(dòng)的,時(shí)間的流動(dòng)無法阻擋,人在時(shí)間面前顯得渺小而無力,現(xiàn)實(shí)生活是不圓滿的,這是遺憾的,哀愁由此而生,產(chǎn)生情感的力度與溫度,這樣的力度與溫度凝結(jié)在時(shí)間和記憶里,融匯在“別經(jīng)時(shí)”中。
張庚評《庭中有奇樹》曰:“通篇只就‘奇樹一意寫到底,中間卻具千回百折;而妙在由樹而倏而榮而馨香,層層寫來以見美盛。”(張清鐘《古詩十九首匯說賞析與研究》)記憶是已經(jīng)發(fā)生過的事情,是客觀存在的;奇樹是記憶的物質(zhì)化,物質(zhì)是人看得見摸得著的,是確定的。奇樹佇立庭中,靜默無言,不曾改變。過去在庭中,現(xiàn)在亦在庭中,未來還會在庭中。而時(shí)間卻是無時(shí)無刻不在向前流動(dòng)的,時(shí)間所指向的是遙不可及和縹緲無知的未來,時(shí)間是不確定性的代名詞。沒有什么東西能在時(shí)間的洪流里保持永恒靜止,庭中奇樹亦然。即使它內(nèi)在里有記憶構(gòu)筑起的堅(jiān)實(shí)建構(gòu),但依然會“發(fā)華滋”,會敗落。但這樣會敗落的“奇樹”卻恰是全詩結(jié)構(gòu)上的動(dòng)力。
《庭中有奇樹》全詩圍繞“奇樹”構(gòu)筑了一個(gè)磁場,“奇樹”是磁場的中心,圍繞這個(gè)位置中心,記憶依次展開。“奇樹”有一種無形的磁力,使得時(shí)間和記憶在流動(dòng)的過程中徐徐鋪開,作品的進(jìn)程也由此推進(jìn)。“如果心中對位置有強(qiáng)烈的印象,記憶就變得容易”,“當(dāng)我們隔了一段時(shí)間以后回到某個(gè)地點(diǎn)時(shí),我們不僅會認(rèn)出這個(gè)地點(diǎn)本身,還會記起在那里做過的事情,想起在那里見過的人物,甚至是曾經(jīng)在我們心頭閃過的無言的思緒”(阿斯特莉特·埃爾、安斯加爾·紐寧主編《文化記憶研究指南》)。“奇樹”在庭中,這是一個(gè)確切的、具體的、不變的位置,這種不移的位置不僅是物質(zhì)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所有的故事都圍繞這一位置發(fā)生,這一位置是故事發(fā)生的物質(zhì)基礎(chǔ),是故事的底基。有底基才有后面在時(shí)間奔流中記憶的層累,才有“折芳寄遠(yuǎn)”的沖動(dòng),才有“路遠(yuǎn)莫致”的嘆息。
記憶里的時(shí)光溫暖哀愁
詩作的主人公應(yīng)為青年思婦,“因人而感到物,由物而說到人,忽說物可貴,忽又說物不足貴,何等變化”(隋樹森著《古詩十九首集釋》)。這樣的變化便是由時(shí)間造成的。飽含記憶與深情的奇樹“發(fā)華滋”,主人公難免想要“攀條”,“攀條”是為了“折其榮”,“折其榮”以“遺所思”,“所思”者是記憶里的他,是從未因時(shí)間流逝而被主人公淡忘的他。記憶在時(shí)間里發(fā)酵,女主人公“因物悟時(shí),而感別離之久也”(《古詩十九首集釋》),并為此折芳寄遠(yuǎn)。
“前四句就折花欲遺所思引起”(《古詩十九首匯說賞析與研究》),所遺的不僅是庭中奇樹所開的物質(zhì)上的花,更是記憶之花,是在時(shí)間流動(dòng)中而依然不減爛漫的思念之花。這花的馨香是記憶的馨香,馨香滿盈的懷袖是念及對方而感到溫情的懷袖。懷袖盈住的是時(shí)間,時(shí)間承載的是記憶,歷久彌新的是思念,是不知?dú)w期的翹首以盼,是終覺路遠(yuǎn)而黯然神傷的輕嘆。“馨香盈懷袖”或許是全詩的轉(zhuǎn)折點(diǎn),是“攀條折其榮”后卻反應(yīng)過來“路遠(yuǎn)”而無從“致之”。是欣喜和哀愁的交接,欣喜和哀愁的交界點(diǎn)是記憶和現(xiàn)實(shí),造成記憶和現(xiàn)實(shí)矛盾的是時(shí)間。從“綠葉發(fā)華滋”到“馨香盈懷袖”歷數(shù)奇樹的生長,是奇樹在時(shí)間流動(dòng)里再自然不過的變化,從發(fā)芽開花,到攀條折枝,再到芳香盈袖。這是對奇樹細(xì)致而全面的刻畫,使得樹木的生長歷歷在目,具體而確定,與記憶形成一種對照的關(guān)系,是對記憶的復(fù)刻與演繹,是脫離了記憶本身的對記憶的延伸,是時(shí)光流轉(zhuǎn),思念作祟。奇樹清晰而連貫的生長過程,是飽滿而鮮活的,而隱匿其中的記憶也隨著樹木的生長清晰地流露,可是即將到來的卻是哀愁,是被袖中清香環(huán)繞的哀愁,是因凝聚著無數(shù)回憶而飽滿溫情的哀愁。而面對這樣的哀愁,“以一語反振出‘感別便住,不更贅一語,正如山之蛇蜿蟮迤邐而來,至江以峭壁截住,格局筆力,千古無兩”(《古詩十九首匯說與賞析》)。
“但感別經(jīng)時(shí)”輕盈細(xì)膩而又婉轉(zhuǎn)自然地托出哀愁,也將哀愁背后的時(shí)間與記憶展示出來,與哀愁相連的不僅僅是時(shí)間和記憶,更是一種情感的溫度和力度。記憶一經(jīng)時(shí)間的催化,厚度增加。而時(shí)間的流逝也在奇樹上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樹之由萌芽以至榮盛,榮盛不過百日,則日衰矣。則其盛也不誠可惜哉!”(《古詩十九首集釋》)奇樹由發(fā)芽,到開花,再到被折枝,何嘗不又是一個(gè)逐漸老去的過程,是哀愁在絲絲縷縷鋪開的過程。詩中的主人公,一位擁有美好回憶卻有絲絲哀愁纏繞心頭的青年思婦,在良辰美景的春光里,在一日又一日的柴米油鹽里,在憔悴憂傷的歲月里,她有她的生活理想。她的生活理想就是她的記憶與時(shí)間,是在庭中,在奇樹下,和自己所念之人相守,一如他們從前相守那樣。而留住記憶,又何嘗不是另一種相守。
思念是對記憶的延展,記憶的延展是回憶的哀愁。主人公守著兩個(gè)人的記憶,“攀條折其榮”,“馨香盈懷袖”,這樣具體的物質(zhì)感受使得記憶呼之欲出,穿透了時(shí)間。“凡樹之奇特,全在枝條之位置扶疏得宜;及花葉茂盛之時(shí),樹之枝條倏盡為所蔽”(《古詩十九首集釋》)。而人的一生又怎么會十全十美,現(xiàn)實(shí)中的大多數(shù)是殘缺和遺憾,面對殘缺和遺憾,我們選擇哀愁。人們產(chǎn)生哀愁的根源是缺憾和無力,這種缺憾即世界的不完美,這種無力是因?yàn)槿祟愒跉v史面前的渺小。
《庭中有奇樹》的女主人公和所念之人相隔萬里,她守著記憶,守著時(shí)間,時(shí)間在流動(dòng),她選擇哀愁。而她的哀愁卻是一種溫暖而清新的哀愁。“當(dāng)未葉未花之前,乃冬春之交,其條枝位置歷歷可見,故顯其奇特耳。”(《古詩十九首集釋》)這“冬春之交”,是女主人公和所念之人相知相守最幸福的時(shí)刻,記憶將這個(gè)時(shí)刻定格,賦予這個(gè)時(shí)刻獨(dú)屬于兩個(gè)人的情愫與浪漫,這種浪漫與情愫在時(shí)間里流動(dòng),隨時(shí)間向前生長,在時(shí)間的流動(dòng)里釀出哀愁,這種哀愁極富生命力,因?yàn)樗Y(jié)了回憶里的愛與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