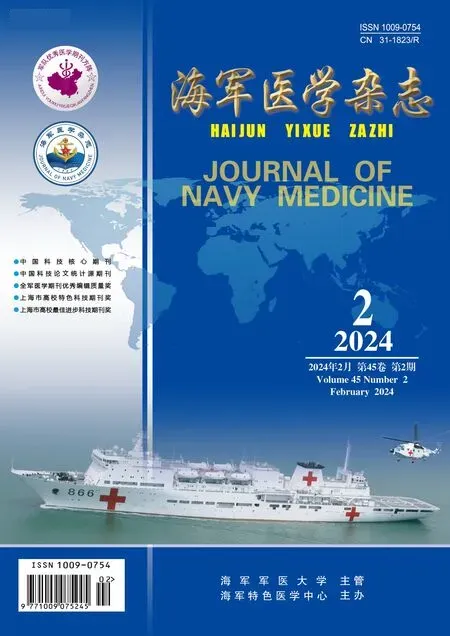新形勢下基層單位官兵戰救知識知曉及訓練情況調查與思考
張新宇,周忠彬,單毅,胡瑾,徐齊兵,楊穎
現代化戰爭在作戰環境和樣式方面發生較大變化,具有作戰強度大、機動性強、戰域廣、殺傷力大、救治機構分散且救治人員相對較少等特點[1],因此對戰現場自救互救及機動衛勤支援保障力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國內既往對于戰傷救治知識掌握情況的調查研究主要集中在單個軍兵種,如海軍[2]或者維和部隊等特殊群體上[3],而多軍兵種的現況調研比較罕見。為進一步做好衛勤準備,提高戰現場急救及自救互救訓練水平,本研究擬對新形勢下多軍兵種基層代表性單位官兵的戰場急救與自救互救知識知曉和訓練現狀進行調研和初步評估,辨識可能存在的影響因素,為實戰訓練轉型提供依據和參考。
1 研究設計
1.1 編制初稿
首先,采用文獻閱讀法整理我軍及外軍戰場急救關鍵知識點和訓練關注熱點,結合軍事訓練大綱相關科目要求,設計調查問卷,問卷以單選題為主,兼顧半開放式選擇題與開放式提問。其次,采用目的抽樣法邀請衛勤訓練、臨床醫學、衛生勤務專家進行焦點小組訪談,了解專家對量表初稿的結構框架、具體知識點的建議和意見,根據現場筆記內容進行主題提取,歸納總結后完善調查表。為加強質性研究的可信度,課題組采取認真反復閱讀筆記內容,對疑點及時與訪談對象確認核實等,并經綜合討論后形成調查問卷初稿。
1.2 德爾菲專家函詢
為了保證調查問卷的科學性和實用性,邀請了20 名相關領域專家對調查問卷所有條目進行內容效度評價,采用李克特5 點計分方式評價相關性。發放函詢問卷20 份,回收20 份,回收率100%,回收率高反映專家積極系數高。通常認為德爾菲法專家函詢問卷回收率>60% 表明專家積極性良好[4]。
20 名專家基本情況為男性14 人,女性6 人;年齡(47.0 ± 6.2)歲;學歷分布:博士10 人,碩士9 人,本科1 人;職稱分布:正高5 人,副高13 人,中職2 人;專業分布:臨床醫學專業12 人,衛勤訓練2 人,衛生勤務3 人,野戰護理3 人;執行重大任務次數最多的14 次,平均1.9 次;對本次調查問卷熟悉程度自評非常熟悉11 人,熟悉8 人,一般1 人,無不太熟悉和不熟悉者。李克特計分結果和專家熟悉程度經統計學計算,結果顯示此次函詢專家權威系數>0.7,代表專家對函詢條目內容的選擇有較大把握,具有權威性[5]。
1.3 調查問卷發放回收與質量控制
調查問卷為匿名調查,不涉及隱私,避免敏感性語言。問卷發放和收集由課題組成員與衛生主管部門共同組織,下發問卷前進行簡短培訓,告知填寫要求,保證問卷所填寫的內容真實、完整、有效。
1.4 統計學處理
采用整群抽樣法,各抽樣單位基礎知識得分均數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法(兩兩比較采用LSD 法)或t檢驗,統計軟件為SAS 9.3。P<0.05 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人員基本情況
本次調查共向L、H 和LB 3 個基層單位發放調查問卷349 份。共回收了349 份,其中L 135 份,H 139 份,LB 75 份。回收率100%。基本情況為:男性330 人,女性19 人;年齡為(24.56 ± 3.58)歲;學歷分布,高中占30.95%,大專占56.16%,本科占12.32%,研究生占0.57%;服役時間為(5.65 ± 3.11)年;人員類別分布,指揮軍官和專業技術軍官各占2.87%,士官占61.32%(其中含23.36% 衛生士官),戰士占32.95%(其中含6.96% 衛生員);參加過軍以上組織的重大軍事演練或執行過大項任務的占22.71%,未參加的占77.29%,參加人員平均參加1.74 次;有10.75%參加過重大軍事演練或執行過大項任務人員遇到急救情況。
2.2 急救知識知曉情況
基礎知識得分有效份數337 份(96.6%),按總分100 分計算,得分(62.69 ± 12.57)分,最高92 分。其中,低于60 分占30.56%,60~<70 分占39.47%,70~80 分占19.88%,80 分以上占10.99%。
比較各單位基礎得分情況,總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F=49.49,P<0.001)。各單位間兩兩比較,LB 高于L,L 高于H,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01)。見表1。

表1 各抽查單位自救互救基礎得分情況(分)
對LB 2 個小隊基礎得分進行比較,戰救隊高于保障隊(P<0.001)。見表2。

表2 LB 2 個小隊基礎得分比較(分)
2.3 訓練現狀與認知情況
參加過自救互救訓練的占85.00%。年度自救互救訓練時間分布見表3,自救互救訓練形式分布見表4,掌握自救互救知識和技能重要性分布見表5。

表3 年度自救互救訓練時間分布(例, n=330)

表4 自救互救訓練形式分布(例次, n=330)

表5 掌握自救互救知識和技能重要性分布(例, n=349)
了解掌握急救知識方式分布見表6,調查人員希望自救互救訓練時間分布見表7,最希望掌握的自救互救與急救知識技能分布見表8。

表6 了解掌握急救知識方式分布(例次, n=349)

表7 調查人員希望自救互救訓練時間分布(例, n=349)

表8 調查人員最希望掌握的自救互救與急救知識技能分布(例次, n=349)
自我認知與實際技能相關性,表現為整體相關性明顯(r=0.31,P<0.001)。具體到各軍種相關性,LB 相關性明顯(r=0.44,P<0.001),L(r=0.06,P=0.941)和H(r=0.15,P=0.081)無明顯相關性。
3 討論
3.1 現狀、分布特點及差異
本次調查發現,代表性基層單位急救知識掌握一般,高分少,各單位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LB 得分相對較高,得益于戰救隊人員從事專業主要為醫療、護理等。H 得分最低,考慮與船上訓練條件相對較差有關。個人得分差別較大,反映各單位急救知識掌握情況參差不齊,這與個人的自我認知和重視程度有關,也和單位組織力度和方法有關。
3.2 認知情況與影響因素分析
86.53%的調查人員認同掌握自救互救知識和技能非常重要,85.00%參加過多樣化的自救互救訓練,認為自己和身邊戰友自救互救知識和技能掌握情況較好,但實際卻不理想。分析原因可能一是部分調查人員自我感覺已經掌握了自救互救知識和技能,但實際上,很多技術未能完全掌握或者模棱兩可,導致在以后的訓練中缺乏進取心;二是部分調查人員清楚自己自救互救知識和技能掌握得不夠,但心理上不愿意承認,在填寫認知情況時出現向好的偏倚。
3.3 課題組實戰化訓練探索
課題組在研究期間進行了2 次實戰化訓練探索:一是全要素引進美戰術戰傷救治開展機動衛勤力量訓練[6],充分感受到戰場情景,設置具象化與實戰性的情景,對訓練對象生理、心理、體力、耐力進行綜合考驗,因地制宜地創造條件設置了炸彈襲擊、室內人質解救作戰、夜間巡邏交火和城市汽車爆炸等不同場景,訓練對象要在與平時或醫院環境截然不同的條件下,完成火線火力壓制回擊,在保證自身與傷員安全前提下接近傷員進行戰術機動,對傷員快速評估、果斷處置。這需要反復不斷訓練才可能熟練掌握。
此外,課題組借助野外駐訓時機組織了一次戰現場救治比武,將戰術通用要求如持槍躍進、匍匐前進、利用地形、觀察報知等技術與止血帶止血、火線搬運、包扎止血、骨折固定、通氣與心肺復蘇等戰現場戰救技術結合,充分利用氣候條件與土質地面和聲、光、電效果,探索了戰救技術標準的適應性、技術選擇的多樣性及戰術環境的實戰性。
3.4 訓練內容與方式建議
戰現場急救是整個戰傷救治工作的基礎,事關后續救治工作能否順利進行,對提升戰斗士氣、恢復戰斗力具有關鍵作用。課題組通過2 次實戰化訓練探索,結合其他研究成果,提出現場急救實戰化訓練內容和形式方面的建議。
3.4.1 訓練內容上 (1)救治與戰術及環境緊密結合,提高自救互救人員在模擬槍林彈雨、戰友負傷、心理應激等各種惡劣條件下的處置水平;(2)除了六大自救互救單項技術訓練以外,適當地增加預防低體溫、燒傷、眼外傷等核心技術訓練。如果只把重點放在單項技術上,會造成訓練內容創新不足,效果有待增強[7];(3)傷情快速評估與決策、器材與裝備使用掌握、時效救治與分級救治理念及整個救治流程訓練都是有機序貫的,需要通盤考慮。
3.4.2 訓練形式上 (1)采用模擬訓練手段,這是由戰場的不可重現性和環境的特殊性決定的,也是國際上實戰化衛勤訓練普遍采用的方式,但是要避免片面追求高仿真。不管是低、中還是高仿真環境或手段,都有其適應性和效果,應根據實際資源、條件和任務合理運用。(2)結合案例教學可產生更好的效果。將實戰案例導入課程,進行討論分析,可激發學員情景處置能力和批判性思維能力。實踐證明,案例教學是學員和基層骨干官兵認可度比較高的教學形式[8]。(3)充分利用軍職教育等進行遠程教學。軍職教育在我軍范圍內已經和院校教育、部隊實踐形成三位一體的培養體系,可充分利用其覆蓋層次多、分布范圍廣的特點[9],而且隨著多媒體技術和網絡技術加持,網絡在線學習、遠程學習更具有優勢,給戰救訓練帶來多樣化的載體選擇及學習方式。
4 結語
本研究尚存在以下局限性:(1)選擇調研的代表性單位的訓練現狀不能代表所有軍隊單位,且調研單位整群抽樣中不含外出任務官兵人群;(2)自救互救基礎知識掌握情況只選擇了戰術戰救結合、傷情評估和六大技術等基礎性技術性問題,未根據軍兵種等差異進行個性化調研,也未調查官兵的團隊協作、溝通及決策等非技術性問題,下一步可擴大調研單位范圍,完善調研內容,更加全面客觀地掌握我軍戰救訓練的動態更新與滾動發展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