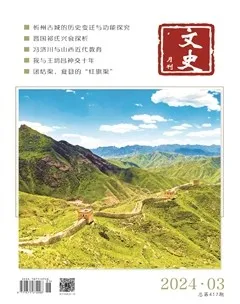梁漱溟的《中國文化要義》
常利兵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梁漱溟(1893—1988)不僅是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而且作為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更是被譽為“中國最后一位儒家”。
梁漱溟在其自述中多次強調“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是他的兩句口號。他不是“為學問而學問”的,而是“感受中國問題之刺激,切志中國問題之解決,從而根追到其歷史,其文化,不能不用番心,尋個明白”。在我的閱讀印象里,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鄉村建設理論》和《中國文化要義》四書是他在20世紀前半期探尋中國問題之解決、民族國家之出路的重要思想結晶,尤其是后兩書更是我們理解和把握他投身于鄉村建設運動及其歷史影響和時代意義的學術經典。
正如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的自序中指出的:“因要解決一個問題,必須先認識此一問題。中國問題蓋從近百年世界大交通,西洋人的勢力和西洋文化蔓延到東方來,乃發生的。要認識中國問題,即必得明白中國社會在近百年所引起之變化及其內外形勢,而明白當初未曾變的老中國社會,又為明白其變化之前提。”基于這樣的問題意識,梁漱溟在書中以“中國文化個性殊強”為討論中心,分別從中國人的家族本位、中國社會的倫理本位、中國的德性禮治傳統、中國的民族精神、中國文明中的治道與治世、中國文化早熟的弊病等角度,深入闡發了兩千年中國文化綿延不絕、且具有“極強度之個性”“高度之妥協性、調和性”,直至“已臻于文化成熟之境者”的要義和肌理。而且,這一切又都是與西方人“集團生活”的個人本位文化邏輯根本不同的。
在梁漱溟看來,中國文化之特殊,正須從“社會是倫理本位的社會”來認識的,即以倫理組織社會,由此決定了中國的社會構造是“舉社會各種關系而悉倫理化之,亦即家庭化之”。而身居此社會中者,每一個人對于“其四面八方的倫理關系”,各負有相當義務;同時“其四面八方與他有倫理關系之人”,也對他負有義務;這樣,全社會之人便“輾轉互相連鎖起來”,無形中“成為一大家庭……得以穩穩行之二千年”。而通常所說的“國家”“社會”等,并非傳統觀念中所有,而是“海通以后新輸入的觀念”,所以在中國人心目中,國家消融在社會里面,社會與國家渾融,“天下觀念就于此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