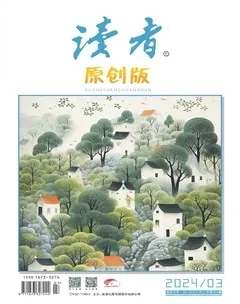遠去的除夕
孟永鵬
除夕是舊年與新春之間的門檻,舊歲至此而除,另換新歲。過年,其實就是跨過除夕。
20世紀80年代初,在我的記憶中,周圍的山村,其實鮮有貼春聯的人家,而我們家是一定要貼春聯的。大年三十這天,父親吩咐我們兄妹將家里唯一的桌子搬到院子里,父親拿出預先準備的紅紙,用鐮刀將其裁成巴掌寬的兩條,再把毛筆用水在碗中泡開,另一只碗里,倒進墨汁。父親站著,提筆,蘸墨,運氣,懸腕,開始寫春聯。
寫得不滿意的地方,父親會輕輕描上一兩筆,邊寫邊自言自語:“字是黑狗,越描越丑。”對聯寫好,父親便讓我們將其拉直,仔細端詳一番,對我們說:“人怕上床,字怕上墻。你們好好念書,以后長大了,我就不寫了,你們寫。”在廚房忙碌的母親已經用面粉打好了漿糊,我們把父親寫的春聯貼在兩側的門框上,紅紅的春聯讓屋里屋外立馬透出滿滿的喜慶。
我家的年夜飯不是北方地區傳統的餃子,而是“寬心面”。老輩人說,年三十吃了寬心面,來年一定心寬氣順、吉祥平安。
年三十,母親早早就開始和面,一手倒水,一手攪拌;和好的面團,要醒一會兒再揉,然后再醒、再揉。揉好醒好的面團,緊緊地裹著長長的搟面杖,在案板上來回翻滾;母親的身體,有節奏地前后移動。“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啪”,伴隨著舞動的韻律,面團在母親的手下越來越大,越來越薄,如一輪巨大的圓月,又好似一張偌大的鼓皮,光潔、平整地攤在案板上。
和平時吃的面條不同,“寬心面”有一指寬。澆面的臊子,用洋芋丁、胡蘿卜丁、豆腐丁、肉末等做成,條件好一點兒的人家,還會在臊子里加上木耳、黃花菜。各家的臊子可能各有不同,但是,有一點卻是相同的:澆上臊子的面條,一定還要撥拉一點點熗炒的蒜苗進去。如此,筷子一攪,湯汁上漂起大大小小的油花,香氣撲面而來,喉間瞬時無法控制地有了反應。面條很筋道,若不攔腰咬斷,一口氣怎么也吸不完;面條很順滑,在舌齒之間柔膩地游動,一不小心就會自己溜進喉嚨。田野的麥香、蒜苗的香氣,都集結在這“寬心面”里,傳遞滲透于全身的故鄉味道,這味道潛伏在記憶深處,把歲月發酵得綿長醇厚。年味,也在“寬心面”的熱氣中回旋升騰起來。

吃完年夜飯,就該上墳了。一只木制的盤子里,放上蒸饃或花卷、紙錢、香燭,領頭的人雙手端著,一屋的男人,都肅穆地跟在后面,到了墳地,站在某個墳頭前面,我們一起恭恭敬敬地焚香,雙手捧香打躬,給每個墳頭都插上一炷香,再打躬作揖,然后跪下來燒紙。紙錢燃盡了,我們便一起磕頭。
一掛鞭炮,搭在墳地的樹枝上,噼啪炸響。暮色如墨跡一樣洇開來,慢慢掩蓋了山巒、田野和村莊,遠遠近近,都是星星點點燃燒的火光。家家戶戶都在這個時候上墳,斷斷續續的鞭炮聲四處作響。上墳是鄉村少有的莊重的儀式,身居大山深處的人們,無論日子過得如何粗糙鄙陋,一年之中的最后一個夜晚,總會以虔誠的姿態和空前的隆重,表達和延續對先人的追思,給后輩傳遞祭祖的形式和禮儀。
放炮的聲音越來越稠密,像是要一比高低,把濃濃的夜色炸出一道道裂縫。幾聲清脆的鞭炮聲從不遠處傳來,弟弟笑道:“這是誰家在折麻稈呢?放我們的‘大炮聽一下!”所謂“大炮”,是爺爺自制的大鞭炮。爺爺點燃了導火索,火苗噴了出來,爺爺揚起手臂,將“大鞭炮”擲向院子前面的山坡下,少頃,“轟—”一聲巨響,腳下的地在顫動,“唰—”空中有泥土飛向樹梢,轟鳴聲如老牛的長哞,在山中來回沖撞,仿佛要尋一條路奔向山外。一聲接一聲的轟響在山中迸放,如農人們拼盡全力生活,迎接來年的平安吉祥。
沒過兩天,有人找上門來,老遠就喊:“你們家放鞭炮,把我的麥地炸出了炕大的兩個坑,要少打多少麥哩!”父親趕忙迎過去:“他姨父,麻利來!坐下坐下,我給你煨茶。”父親雙手遞過煙,用火箸夾起火盆里的木炭點著了,笑道:“我才說叫娃給你拜年去哩!多拿上兩把掛面,再拿上一包點心。過年哩嘛,就聽個響聲,圖個歡鬧!他爺上歲數了,手上沒勁了,沒甩遠。”來人猛咂了一口煙,低頭說:“過年嘛!”
1984或者1985年,西秦嶺余脈深處的一戶農家,沒有電視機,除夕之夜,在窗外此起彼伏的鞭炮聲中,一家人圍著爐火,坐在或大或小、或高或低的各式椅子、板凳上,還有的坐在炕沿上,在守歲中上演了一場家庭春晚。
火盆里,剛添加的木炭間或發出一兩聲脆響并迸出火星,黑色的木炭很快變得通身紅亮,火越燒越旺,手被炙烤得熱乎乎的,臉上多了些許紅潤。火盆周圍,烤著饃饃和金黃的柿子。一只小炕桌上,擺著點心、柿餅、核桃,還有幾個青青的如乒乓球大小的蘋果。父親從墻上取下一年都沒摸過的二胡,仔細擦拭上面的灰塵,吱吱呀呀地調音,他按弦的手指并不很靈活,拉的都是簡單的曲子,如《東方紅》《我愛北京天安門》《我的祖國》《送別》等。大弟弟手中攥著口琴,自然也要吹奏一曲。父親指著我們說:“天天念書哩,也學唱歌,你們都唱一下!”我們兄妹平時都怕父親,忸怩著不敢張口。父親說:“我帶個頭。”他輕聲唱:“紅巖上紅梅開,千里冰霜腳下踩,三九嚴寒何所懼,一片丹心向陽開……”
父親唱完了,我們使勁拍手,喊:“媽也唱一個!”母親笑道:“我就算了,你們好好唱!”她嘴里這樣說,卻坐直了身子,揚頭說:“我唱個《南泥灣》—花籃的花兒香,聽我來唱一唱……”我們兄妹低聲商量之后,站成一排,放開喉嚨唱《山里的孩子心愛山》:“山里的孩子呀心愛山,從小就生長在山路間,山里的泉水香噴噴,山里的果子肥又甜……”父親抱著二胡,斷斷續續地拉弓,手在弦上摸索著尋找音符,試圖為我們伴奏。一支歌唱完了,母親帶頭拍手,大聲說:“好!唱得好得很!再唱一個。”我們又唱《媽媽的吻》:“在那遙遠的小山村,小呀小山村,我那親愛的媽媽,已白發鬢鬢……”
窗外的鞭炮聲已然稀疏輕淡了,我們家里的琴聲、歌聲、歡笑聲,愈顯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