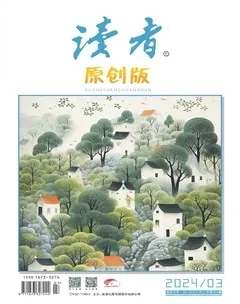那些時(shí)光
周玉潔

一
小時(shí)候,我有大把時(shí)間。時(shí)間多到能從早到晚看同一本連環(huán)畫(huà),把書(shū)角看卷、書(shū)頁(yè)看散,丟失了封底封面,仍記得封底封面上的圖文。許多連環(huán)畫(huà)就那樣被我看得爛熟于心,看到不用再看,閉著眼睛,那些圖畫(huà)都能在眼前浮現(xiàn)。
我等鄰居菜地旁的蘋(píng)果樹(shù)豐收,便常去看葉子、看花,看果子一天天變化。下過(guò)雨去看果子被打落沒(méi)有,刮過(guò)風(fēng)去看落了多少葉子。倒也不十分惦記,倒也不十分期待,就是那么有一搭沒(méi)一搭,這里走走,那里瞧瞧,想起蘋(píng)果樹(shù)來(lái)就往菜地那邊去。
前檐蜘蛛結(jié)網(wǎng),后院井水落漲,太陽(yáng)升到多高,晚霞幾種顏色……我細(xì)數(shù)慢看,時(shí)間像是用不完。不用定鬧鐘,沒(méi)有具體責(zé)任,也沒(méi)有誰(shuí)派給我需要趕緊完成的任務(wù)。不慌不忙,無(wú)憂無(wú)慮,那是何等奢侈、愜意。
年少時(shí)讀雨果的《悲慘世界》,厚厚一部書(shū),讀了好幾遍。可是人到中年的我居然在有一天想起這本書(shū)時(shí),發(fā)現(xiàn)自己除了冉·阿讓這個(gè)名字,許多情節(jié)已忘了。我想再讀一遍,總沒(méi)有時(shí)間。于是找到有聲書(shū),做飯時(shí)聽(tīng),擦地板時(shí)聽(tīng),上下班路上聽(tīng)……情節(jié)被切割成不規(guī)則的小塊,一本書(shū)聽(tīng)得斷斷續(xù)續(xù),夾雜著我莫名的焦慮。
一天24小時(shí),每小時(shí)60分鐘,每分鐘60秒,每天86400秒……不是這么算的。而是—時(shí)間周而復(fù)始,不增不減,不流逝。時(shí)間不過(guò)是個(gè)概念,我仍可以像小時(shí)候那樣奢侈。
我決定每晚專門(mén)空出一些時(shí)間來(lái),悠悠閑閑再聽(tīng)一本書(shū)。以此打破時(shí)鐘對(duì)我的捆綁,重溫那沒(méi)有時(shí)間概念的美妙時(shí)光。
找到香港作家西西《飛氈》的有聲書(shū),播讀者是香港的一對(duì)戀人,軟軟的口音,斷句略生硬,讀得有點(diǎn)磕巴,卻認(rèn)真。
夜晚的同一時(shí)刻,他們準(zhǔn)點(diǎn)開(kāi)讀,我準(zhǔn)點(diǎn)去聽(tīng)。他們不知道我的存在,我卻像他倆的老朋友一樣,熟悉他們的聲音。
“我是阿Sion……”男孩的聲音,溫暖、有磁性。“我是阿Yok……”女孩的聲音,溫柔、甜美。
“阿Sion、阿Yok,晚上好……”他們道開(kāi)場(chǎng)白時(shí),我也暗自向他們問(wèn)好。
阿Sion讀的時(shí)候,我和阿Yok聽(tīng)著,他讀錯(cuò)字詞時(shí)會(huì)帶著歉意嚴(yán)謹(jǐn)?shù)丶m正,重讀一遍整個(gè)句子。有時(shí)他停頓,過(guò)了好一會(huì)兒,才忍不住尷尬地說(shuō):“抱歉,這個(gè)字我不認(rèn)得。”我和阿Yok一起笑出聲來(lái)。有時(shí),到了劇情關(guān)鍵處,他只管自己看字,忘了讀,好一會(huì)兒不出聲,我和阿Yok會(huì)忍不住催問(wèn):“后來(lái)呢?”
我們都關(guān)注小說(shuō)里花初三和葉重生的愛(ài)情故事,每當(dāng)劇情不如我們意愿時(shí),阿Yok會(huì)在一旁嘆息;到了令人發(fā)笑的情節(jié),阿Yok笑得停不下來(lái),阿Sion無(wú)法繼續(xù)讀,索性也跟著笑起來(lái),我這個(gè)他們不知道的聽(tīng)眾也在笑。
阿Sion翻書(shū)的聲音,阿Yok咳嗽的聲音,阿Sion倒水的聲音,阿Yok推開(kāi)窗戶的聲音,穿插在朗讀聲中……西西的《飛氈》寫(xiě)得很美,我認(rèn)為阿Sion和阿Yok也是很美的人,他們陪我度過(guò)了一段很美的時(shí)光。這本書(shū)讀完后的一個(gè)節(jié)日,我第一次給他們發(fā)去留言,祝福并感謝了他們。那段時(shí)間,我眼睛疲勞,看書(shū)費(fèi)勁,卻惦記著這本《飛氈》。在聽(tīng)書(shū)的App上意外地遇到有人在讀這本書(shū),于是阿Sion、阿Yok這兩個(gè)陌生人的聲音和《飛氈》的情節(jié)融在一起,使得這本書(shū)和其他我讀過(guò)的書(shū)變得不一樣了。
二
時(shí)間漸漸多起來(lái),我也會(huì)在音樂(lè)網(wǎng)站東游西逛。我去找記憶中那些聽(tīng)過(guò)的老曲調(diào),發(fā)現(xiàn)很多曲名都變了。吉他曲的名字以前多是《愛(ài)的紀(jì)念》《愛(ài)的羅曼史》一類,后來(lái)的吉他曲曲目變得似乎不知所云一點(diǎn),異樣一點(diǎn),我忘了聽(tīng)曲,單單去看曲名。
有一首吉他曲名叫《坐在門(mén)前石階上等太陽(yáng)下沉》,有一首叫《黃昏成河云成墨》,還有一首叫《晝夜如你》;有一首鋼琴曲的名字叫《誰(shuí)是誰(shuí)的誰(shuí)》,有一首叫《我在那一角落患過(guò)傷風(fēng)》,還有一首叫《洋蔥》……
歌詞也和我記憶中的老歌不一樣了,我跟著旋律哼唱,卻總是記不得歌詞,索性自己編了幾句詞:樹(shù)上的蘋(píng)果熟了/你去年沒(méi)送我梯子/我夠不著……
我這么悠閑地度過(guò)了許多感到有味道的小時(shí)光,體驗(yàn)到很多我匆匆忙忙做事時(shí)體驗(yàn)不到的小樂(lè)趣。一天,在外地上學(xué)的孩子給我發(fā)來(lái)一首歌《你還在我身旁》:瀑布的水逆流而上/蒲公英的種子從遠(yuǎn)處飄回,聚成傘的模樣/太陽(yáng)從西邊升起,落向東方/子彈退回槍膛/運(yùn)動(dòng)員回到起跑線上/我交回錄取通知書(shū),忘了十年寒窗/廚房里飄來(lái)飯菜的香/你把我的卷子簽好名字/關(guān)掉電視,幫我把書(shū)包背上/你還在我身旁……
我們聽(tīng)著歌,聊起一首關(guān)于螃蟹的詩(shī),又聊起英國(guó)無(wú)名氏的那首類似創(chuàng)意的詩(shī):“我跑上門(mén),打開(kāi)樓梯。說(shuō)完睡衣,穿上祈禱,關(guān)上床,鉆進(jìn)燈……”
我們繞來(lái)繞去,好像在躲避著什么。《你還在我身旁》這首歌里寫(xiě)的是我和孩子也經(jīng)歷過(guò)的,她準(zhǔn)點(diǎn)放學(xué)回家,我在廚房里忙活,我就著餐桌在她的卷子上簽字,她換鞋時(shí)我提著她的書(shū)包在門(mén)內(nèi)送她出門(mén)……我們一起度過(guò)的那些爭(zhēng)分奪秒,在鬧鐘聲中起床、在鬧鐘聲中準(zhǔn)時(shí)開(kāi)飯的日子。
東拉西扯了好一會(huì)兒,我們才又回到她發(fā)給我的那首歌。
我說(shuō):“這首‘交回錄取通知書(shū)‘幫我把書(shū)包背上的歌,估計(jì)是大學(xué)生回憶上學(xué)的時(shí)候……”
她說(shuō):“就像那首螃蟹詩(shī),反過(guò)來(lái)看是一種意思,可以理解為,我在想你。也可以是,螃蟹不可能剝我的殼,筆記本不可能寫(xiě)我,所以你不可能想我,但我還在想你。”
我們不直白地說(shuō)愛(ài)和想念,通過(guò)分享,我們各自把想說(shuō)的說(shuō)了,仍舊有一種意趣,借別人的詩(shī)和句子,說(shuō)我們的話。
在那首歌的網(wǎng)頁(yè)底下,很多人留言。
有人說(shuō):“我很認(rèn)真地看了歌詞。多年后,這絕對(duì)是最下酒的那一首。”
有人說(shuō):“媽媽沒(méi)等到我將錄取通知書(shū)交到她手上就離開(kāi)了,她離開(kāi)那年我讀初三。不久,我收到了重點(diǎn)高中的錄取通知書(shū)。如今,我就讀于省內(nèi)數(shù)一數(shù)二的大學(xué),猶記得,前年拿到通知書(shū)的時(shí)候,哭得稀里嘩啦,因?yàn)檫@些是媽媽希望看到的,但她都錯(cuò)過(guò)了。她的一生僅僅四十幾年,卻全是艱難。”
有人說(shuō):“聽(tīng)到‘我交回錄取通知書(shū),忘了十年寒窗這兩句的時(shí)候有點(diǎn)流淚的沖動(dòng),今年輪到我高考了……”
我發(fā)現(xiàn)網(wǎng)頁(yè)上盡是孩子們的留言,而“母親們”并未出現(xiàn)。母親們?cè)诟蓡崮兀克齻兇蠹s是不愿提及那些辛苦和付出,她們也許會(huì)淡淡一笑,說(shuō)孩子們真的都長(zhǎng)大了,孩子們已經(jīng)體會(huì)并懂得;母親們也許仍舊忙碌著,甚至都沒(méi)有聽(tīng)過(guò)有這樣一首歌。
我們匆匆忙忙在忙些什么?
于是,我對(duì)孩子說(shuō):“我想你啦,我也知道你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