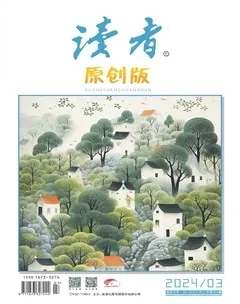雪落城墻上
蟠桃叔

一
在西安的城墻底下時常碰見賣蓮蓬的,高一聲低一聲地叫賣。這蓮蓬多出自王莽。王莽是地名,在西安的郊區。
很多年前,有一次,我遇到了,便去挑幾個,忍不住和那賣蓮蓬的聊了幾句閑話。那賣蓮蓬的漢子果然是王莽人,善談,話匣子一打開,倒豆子一般,啥都往外倒。
他夸王莽物產豐饒,產蓮產桃,還產桂花球大米。說他爸生前,正值壯年時,天天騎輛自行車馱幾袋子桂花球大米,進西安城換面粉。那時物資供應不豐富,西安城里人想要吃大米,只能用面粉跟農民換。
有一天,他爸騎到陜西話劇團門口,剛吆喝了一聲“換大米”,就跑出來一個人把他爸的自行車后座拉住了,說要拜他爸為師學這聲吆喝。后來,央視春晚上演了個節目《換大米》,把全國人民都逗笑了。沒準兒這里面就有他爸的功勞。
又說他媽手巧人善,會剪窗花,會蒸花饃,愛打花花牌,牌搭子有兩個,也都是農村的巧婆婆,一個煎餅攤得好,一個蘿卜干曬得好,都有本事。
又說他弟兄三個,老大老二調皮搗蛋,都沒有念下書。老大就是他,不愛種地,愛提桿秤做小生意,有桃了賣桃,有蓮蓬了賣蓮蓬;老二是個直人,愛犯倔,在城墻上穿個鎧甲演古代的兵;老三卻有出息,在北京念大學……
我看他說得收不住了,忙說:“有空到你們王莽看荷花去,歡迎不?”
賣蓮蓬的漢子說:“歡迎啊!來了就找姓曲的,碰見村里人,你就隨便打聽,說這曲家兄弟三個,老大是個逛蕩子,老二是個倔倔子,老三是個書呆子,一說就都知道了。”
我笑著和熱情爽朗的曲大哥告別。
二
過了一年或者兩年,我到城墻上做一個活動的采訪—那時我在報社做記者。采訪結束,下了城墻天上都出月亮了,找了個地方吃了飯,然后順著城墻根兒溜達著往回走。天黑,沒注意,一個人蹲在地上,我一腳就踩到了那人的腳背。我趕緊說對不起。那人卻說:“哦,這巧的,是你呀!”
我認不出是誰,也不好意思問,隨口說:“哦,真巧,真巧。你蹲在地上干啥呢?撿錢了嗎?”
那人說:“燒紙,送錢呢。”說著,就掏出一沓黃表紙和打火機。火焰起來了,他說:“爸呀,天冷了,穿厚些。給你送些錢,你在底下慢慢花,想吃醪糟你買醪糟,想吃甑糕你買甑糕……”
原來是兒子給老子燒紙。我退了三步,站在一旁靜觀。
火就是世上最絢爛的花,一開一敗,紙燒成灰,風一吹就四散開來,那人誠誠懇懇磕了頭,就算完了。
我也是話多,問他今天燒啥紙,不是送寒衣的時候呀。那人說今天是他爸的祭日。
那人問想聽他爸的故事不,我自然求之不得。
我們在馬路牙子上一坐,就諞開了。夜色濃,互相也看不清楚嘴臉。可是,那有什么關系呢?
那人說開了:“我爸雖然是個農村人,但是這一輩子愛城里,愛西安。我看他比西安人還愛西安。世上的人,百人百性,有人愛唱戲,有人愛種菜,有人愛吃辣子,有人愛做媒,有人愛養狗攆兔子,有人愛逛廟會,還有人愛認干親……這都是愛好。我爸的愛好就是愛西安。從記事起,我就沒見過我爸做農活。肯定也做過吧,反正我的印象里沒有,感覺我爸連镢頭和锨都沒有摸過。整天干啥呢?就是進城換大米。你知道換大米不?哦,你知道啊。
“我爸就是換大米的。天不亮,他就騎上加重自行車,馱幾袋子從村里收的米進西安城了,一去一天,回來就出星星了。我爸有時候開玩笑,說他是半個西安人,半個農村人。因為他的白天給了西安,晚上給了農村。一到天黑,我媽就把米湯跟饃在后鍋餾著,我爸回來,飯還是熱的。
“我爸餓了一天回來,剛一拿筷子,我兄弟幾個就把我爸圍住了。我爸一邊吃一邊跟我們胡諞,主要就是諞西安。我爸說西安的無軌電車,頭上拖著電線,車廂是兩節子,中間是橡膠連著的,車一拐彎,中間的橡膠也跟著打彎;我爸說西安電信大樓的大鐘準點報時,放‘東方紅,太陽升的音樂,好聽得很。為啥要弄這大鐘?一是方便西安人手表不準了對表,二是提醒人按時進場看戲,因為跟前就是易俗社,易俗社唱的是天底下最好的秦腔戲。
“我爸說他過北關時,看到一個戴藍套袖的老漢在賣元宵。他在人家攤子上坐下歇腳,老漢給他端了一碗元宵湯,就是煮了元宵的熱湯水,免費的,不要錢。那元宵湯不知道煮過多少元宵了,熬得稠稠的,白白的,油油的,燙燙的。哎呀,真好喝,這一輩子都沒喝過這么好喝的元宵湯。我爸說得我們都流口水了……
“我們兄弟幾個太愛聽我爸諞西安了。但是有一回,我爸跟我們諞西安,我們都難過了。我爸說,他差一點在西安挨打。說在一個家屬區,他換完大米,高高興興推著自行車正準備出大門,追出來一個人,說給他換的大米不夠斤兩。那人上去一把揪住我爸的衣服領,車子上當時有我爸用大米換的幾百斤面粉,這一撕扯,車子就倒了,面袋子掉了一地。那個人愣了一下,就幫著我爸把車子扶起來,又把面袋子抬到車上。弄完了,那人說,本來想打你一頓呢,看你也可憐,你走吧,下回不要短斤少兩了。
“我爸一句多余的話都沒說,騎上車就回來了。我爸還讓我們看他被撕扯的袖子。他說,掙西安人的錢你以為容易?我們兄弟幾個低下頭都沒話說了,心里跟刀割一樣。其實,我們還偷偷思考了一個問題,我爸看著老老實實一個人,到底有沒有缺斤少兩?應該沒有吧,那是我爸呀。如果我爸真干了那缺德事,把人丟到西安了,我們會更難過。人家西安人還給他喝元宵湯,都不要他的錢。缺斤少兩咋對得起人家西安人呢?但是年紀小,憋在心里,死活都不敢問我爸。其實到現在我都沒搞清,成謎了……
“后來國家經濟發展了,糧食夠吃了,沒人換大米了,我爸身體也不行了,就不去西安了。不不不,也去西安呢。上西安看病嘛。一查,癌癥,醫生說吃藥打針不頂啥了,做手術也不頂啥了。那就不治了,回來給他買了只奶羊放著,一是圖放羊解心慌,二是圖每天給他擠羊奶喝,補充營養。
“有一天,我爸不見了,羊也不見了。滿村尋他,尋不見。到晚上回來了,人和羊都累癱了,說他進城去了。問他進城干啥,他說賣羊奶,西安人要喝現擠的羊奶呢。我媽就罵我爸有病。我爸說,他就是有病,愛西安的病。
“也不知道是不是遺傳,我也有愛西安的病,跟我爸的癥狀一模一樣,農村待不下,魂丟到西安了,就愛往西安鉆。我爸說他的魂在城墻底下胡逛,我是天天在城墻上面胡逛。我還有個哥,在城墻底下賣桃賣蓮蓬。早上騎個自行車來,晚上再騎自行車回去,太晚了就不回去,住我那里……”
那人絮絮叨叨一串話說出來,我突然醒悟過來:這人在城墻上扮演古代的士兵,我今天還給他拍了照的。下班了,盔甲一脫,我就認不出來了。又聽他說賣蓮蓬的大哥,心里更明白了。
我說:“我知道啦,你姓曲,你是曲二哥,你家在王莽。你家兄弟三個,老大是個逛蕩子,老二是個倔倔子,老三是個書呆子。你看我說得對不對?”
曲二哥驚道:“我的天神,你在八仙庵門口擺過攤子算過卦嗎?”
我把緣由說了,曲二哥驚得直拍大腿。
三
不由分說,曲二哥非要拉我去他的住處喝兩杯。我無事,和曲二哥氣味也相投,就去了。曲二哥把我引出城門,走了一段路,進了一個叫仁義村的城中村。進村一看,簡易樓蓋得密密麻麻的,一家挨著一家,熱鬧是熱鬧,臟亂是免不了的。曲二哥說:“不要嫌棄環境不好啊。”
我說:“哪里會。我也是住城中村的,我住大雁塔跟前的后村。”
曲二哥說:“古人說人生如寄,這話對著呢,世上的人住哪兒都是暫住,住再闊再大的房都是暫住。故宮前前后后住了兩朝幾十個皇帝,皇帝都不在了,故宮還在,那就是暫住—后來末代皇帝溥儀進故宮博物院,不是還要自己買票才能進嘛!哈哈哈,你在后村是暫住,過幾年就在這西安城里買房了。我在這仁義村也是暫住。過幾年,還是要回王莽的。再愛這西安又能咋,說到底,西安不是我的。”
我無話可說了,不知道是該點頭還是搖頭。
曲二哥在村里的攤子上買了涼菜,又買了一瓶太白酒,我要付賬,被曲二哥扭住手腕,只能作罷。
帶著酒菜來到曲二哥的房子,我驚呆了。小小一間房,也沒啥家當,四壁掛滿了碑帖拓片,什么曹全碑、多寶塔,都是在碑林門口的攤子上買的復制品。書案上有筆墨紙硯,還有撕開的方便面袋子。沒看出來,這曲二哥竟是搞書法的。我不懂書法,但是一看曲二哥的字,也知道是好的,正經路子。不過也沒有夸贊,什么都沒有說,只是靜靜地看了一會兒。
曲二哥陪我靜靜看了一會兒,然后把書案騰開,擺上酒菜。那天是曲家伯伯的祭日,第一杯酒就敬曲家伯伯了。窗外,可以看到城墻上的紅燈籠,被風吹得搖搖晃晃。
那晚酒把心喝熱了。我也多多少少有些醉了。喝到半夜,要回家了,我說我能走,他不放心,一定要送我回去。一出門,天呀,下雪了。整個西安成了一個銀裝素裹的琉璃世界。我們都很歡喜,雀躍起來,索性踏雪而行,到了南門廣場耍雪。
廣場上安安靜靜的,能聽到雪落在地上的聲音。廣場成了好大一張白紙。曲二哥張狂起來,說他想在這雪上來個驢打滾,想在這雪上寫字。說著就俯身用手指頭為筆,大開大合地寫了“西安最美下雪時”。我寫了“長安何曾負少年”。
六棱子的雪越下越大,片片都朝我們撲來,把人糊成雪人了;不遠處的城墻,披上了雪毯。我就在想,這西安有那么多人,能來的,都是愛西安的。這城墻多像一個臂彎啊,把這些愛西安的人都摟在懷里了。
那是2005年的第一場雪,真大啊,飄飄灑灑,足足下了三天才停,此后西安就再也沒有下過那么大的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