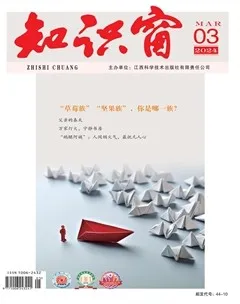有些燈火,永遠(yuǎn)蓬勃
彭妤

看完電影《我本是高山》后,剛走出電影院,我迫不及待地打開珍藏很久的關(guān)于張桂梅校長的紀(jì)錄片。有個鏡頭,我每次都是含著淚看完的——和十多年來的每個凌晨5點一樣,張校長打著手電筒,將5層教學(xué)樓的樓道一一點亮。她站在2樓,手持喇叭,喊道:“起床嘍,姑娘!上課嘍,姑娘!”在黎明前的夜幕下,明暗對比令人心疼,不知道是她站在光里,還是她散發(fā)著光。她催促學(xué)生跑步洗漱、跑步進(jìn)教室,她希望順時針推進(jìn)的每一分鐘都能逆轉(zhuǎn)命運。她的小喇叭喊醒了一座座大山,她的手電筒照亮了一個個山鄉(xiāng)女孩的未來。
這是“燃燈校長”張桂梅的故事,其實也是無數(shù)個老師的故事。師者如燈,永遠(yuǎn)是精神之燈,常常也是實物之燈。
有些燈是“菜油燈”
1938年,浙江大學(xué)被迫一遷浙江天目山、建德,二遷江西吉安、泰和,三遷廣西宜山,四遷貴州遵義、湄潭。遷徙途中,費鞏先生臨危受托,擔(dān)任浙江大學(xué)訓(xùn)導(dǎo)長。在就職演講中,費先生只說:“吾愿意做你們的顧問,做你們的保姆,以全體同學(xué)的幸福為己任。”這個“保姆”首先去了條件極差的學(xué)生宿舍:大雜間,上下鋪,自習(xí)只能坐床上,看書只有桐油燈。每晚,光照暗、油煙大的桐油燈都把學(xué)生的鼻孔熏黑。這個不拿工資的“保姆”迅即自費定做了800余盞由浙江大學(xué)教授改良的有玻璃罩的植物油燈,一一發(fā)給學(xué)生。當(dāng)年的學(xué)生回憶那一盞燈時,說:“油燈的光焰,像孩子的一雙閃動的明眸。燈火微弱,卻給人光亮,給人溫暖。”學(xué)生給這盞燈取名“費鞏燈”。
有些燈是“手提燈”
2009年,廣州市天河區(qū)有個叫棠東的村子,是當(dāng)時的農(nóng)民工集中租住村。有村子,就該有學(xué)校,61歲的熊傳德老師就是村里民辦學(xué)校的副校長。他在湖北老家以民辦教師身份退休后,輾轉(zhuǎn)來到廣州。到學(xué)校后不久,他便發(fā)現(xiàn)學(xué)生每天往返一條50多米長的隧道,這也是200多名農(nóng)民工子女上學(xué)放學(xué)的必經(jīng)路,因沒有路燈,即使白天,隧道里也伸手不見五指。擔(dān)心學(xué)生被車撞傷、摸黑摔倒,熊老師買來充電的手提燈,每天早上6點起床,6點30分趕到隧道口等著,護(hù)送學(xué)生過隧道,一直到8點,再匆匆趕回學(xué)校準(zhǔn)備上課。得到幫助的不僅僅是學(xué)生,周圍的村民都因這盞燈受益。他們漸漸發(fā)現(xiàn),遇到下雨天時,熊老師更不容易,他有嚴(yán)重的關(guān)節(jié)炎,雨天發(fā)作時疼得厲害,只能蹲在地上舉起手提燈。在他的感染下,學(xué)校其他老師也來“代班提燈”。有網(wǎng)友深情地留言:“你即使蹲下,仍是一座高高的燈塔!”
有些燈是“電筒燈”
2022年,在湖南常德的一所鄉(xiāng)村學(xué)校,有個叫麻小娟的老師,完成了她的“一千零一夜”故事,又繼續(xù)著她的“一千零一夜”故事。擔(dān)任鄉(xiāng)村教師七年,除去寒暑假和休息日,上千個夜晚,她都是陪著住校的學(xué)生入睡。一千多個晚上,一千多個故事,從利用每天睡前半小時,打著手電筒為學(xué)生講故事,到把“故事教學(xué)”引入課堂;從以“老師”的身份管理住校學(xué)生,到以“媽媽”的角色用心陪伴;從關(guān)心學(xué)生怕不怕黑、孤不孤單,到呼吁社會關(guān)注留守兒童群體……成為全國人大代表的麻小娟,和學(xué)生一同在成長。
張桂梅校長的手電筒照亮每一個早晨,麻小娟老師的手電筒溫暖每一個夜晚。
有些燈是“汽車燈”
2023年6月初的一個晚上,在安徽廬江一所中學(xué),高三年級學(xué)生最后一節(jié)晚自習(xí)下課后,教學(xué)樓前的通道旁,一輛車、兩輛車、三輛車……幾十輛車的車燈照亮了前方。這是老師集體打開車燈為即將參加高考的學(xué)生照明,寓意前途似錦、一路明亮。師者之燈,永遠(yuǎn)是為照亮別人。
菜油燈、手提燈、電筒燈、汽車燈……當(dāng)這些質(zhì)樸的實物之燈與精神之燈在一種職業(yè)身上重疊,林林總總的修辭手法瞬間失去了力量,語言顯得蒼白,歌頌變得淺薄。但,有個事實永遠(yuǎn)改變不了——在學(xué)生心田,在民眾眼中,在時代深處,有些燈火永遠(yuǎn)蓬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