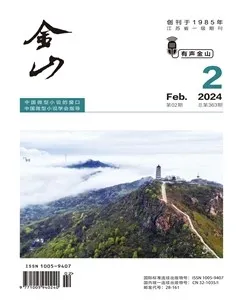書記的禮物
周起
福根一接電話,不禁心驚肉跳:老媽要跳井。原因是村里搞旅游開發(fā),福根媽不愿離開老屋搬到集中居住區(qū)。
父親過世早,是母親含辛茹苦撐起了這個(gè)家。福根讀完大學(xué),在縣城一中當(dāng)了老師,兩個(gè)妹妹先后出嫁,也有了自己的生活。福根夫妻多次想接老人來城里住,可老媽不愿離開老屋。福根媽說,老屋里有家的記憶。福根的頭一下子大了,如何是好?他當(dāng)機(jī)立斷,去超市買了兩瓶五糧液和一條軟中華,找崔書記想辦法。
福根的同學(xué)崔書記,是鎮(zhèn)里的一把手。平時(shí)各忙各的事,福根也不曾拜訪過。為了老媽,福根不得不硬著頭皮找書記了。
晚上,福根提溜著煙酒,做賊一樣來到云森小區(qū)。一次同學(xué)聚會(huì),崔書記客氣地邀請同學(xué)們來家做客,說了住址,至于幾號(hào)樓哪一戶,福根沒記住。小區(qū)里高樓林立,一輪孤月懸在樓頂?shù)拈g隙。福根徘徊再三,猶猶豫豫,撥打了崔書記的電話。
一呼,對(duì)方通話中;再呼,對(duì)方仍然通話中。福根的心涼了半截,埋怨自己,平時(shí)不燒香,臨時(shí)抱佛腳,連老同學(xué)家門都找不到。他抬頭望月,清輝凜冽,如罩冰雪。
福根覺得自己如墜深淵,忽然電話響起,是崔書記來電,福根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崔書記態(tài)度親和,把他接到家中,說:“老同學(xué)怎么忽然想起了我?”
也許在黑暗中待長了,燈光耀眼,福根眼角一陣潮熱。他囁嚅著,簡要陳述了家里的難處,說老媽要拼命了,懇請書記關(guān)心。
崔書記說:“村里匯報(bào)搬遷工作順利,怎么搞成這樣?我明天去你老家調(diào)研,現(xiàn)場辦公。”福根說:“那好那好,請您多關(guān)心。”崔書記笑了:“百姓的事,只要政策允許,關(guān)心是理所應(yīng)當(dāng)?shù)模螞r你我同窗。”福根變得笨嘴拙舌,只會(huì)點(diǎn)頭。
書記去廚房給福根泡茶,福根說:“不啦不啦,不打攪了。”便逃也似的離開了。待崔書記看到煙酒追出門時(shí),福根早已不見了蹤影。出了小區(qū),福根定定神,用手扯扯衣服后擺,背上汗出如漿。
第二天晚上,老媽樂呵呵地打來電話,讓他周末回家。福根已經(jīng)猜到了八九分,心想早該打點(diǎn)打點(diǎn)。
周末,福根回家,母子相見,分外話多。老媽口口聲聲說崔書記好,平易近人。老媽說:“我告訴書記,我為什么不搬遷。我要守著家門口的那棵柿子樹,那棵柿子樹有五十多年了,結(jié)婚那年,我和你爸一起栽的。你爸說秋天的柿子,紅紅火火,吉祥喜慶。唉!你爸命苦,沒等到今天的好日子,但是我要守著這棵樹,留著念想。”
老媽絮絮叨叨:“我還告訴書記,我要留著門口的水井。以前沒有自來水,這井水可養(yǎng)活了村子里好幾十口人。崔書記來到井邊,摸摸轆轤,看看井壁上有水泥字:南面是‘滴水之恩涌泉相報(bào),北面是‘吃水不忘挖井人。我告訴崔書記多年以前孩子小,挑水困難,溝里的水又臟,是你爸借了債,打下了這口井!”
老媽告訴我,崔書記是菩薩心腸。他對(duì)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鄉(xiāng)村搞旅游開發(fā),不求千篇一律,要因地制宜,最終還是為了老百姓滿意,讓老百姓有幸福感。把那棵柿子樹留著,讓老人家‘柿柿如意,那口水井也要留著,當(dāng)柿子開花時(shí),這里就‘井上添花了!”崔書記的話,老媽不是很懂,看別人鼓掌,她也跟著鼓掌。
福根心想,如果我沒去他家拜訪,他會(huì)來替老媽說話嗎?
老媽還告訴福根,現(xiàn)在“養(yǎng)老不出村莊”,老年公寓建在村子里,想家就回去看看。老人把自家多余的房子租給集體辦民宿,自己住老年公寓,一年的房租收入有一萬多。現(xiàn)在,老媽已經(jīng)愿意搬了,說老年人住一起熱鬧,公寓里有食堂,吃飯政府還有補(bǔ)貼。再者,老年公寓離老屋也不過幾里遠(yuǎn)。想家,就去看看。
難于上青天的事,瞬間變得易如反掌。福根暗自慶幸,打通領(lǐng)導(dǎo)關(guān),事事好商量。
傍晚,福根返城。老媽照舊在車?yán)锓判╇u蛋和自己種的白菜蘿卜等,最后竟然拎出兩瓶五糧液和一條軟中華。老媽說:“哪有領(lǐng)導(dǎo)給群眾送禮的!書記的車跑得快,我沒追上。”
福根的臉一下子漲得通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