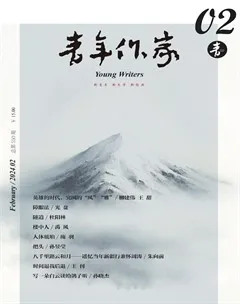八千里路云和月
我是解放軍藝術(shù)學(xué)院首屆文學(xué)系學(xué)員,1984年9月1日入學(xué),學(xué)制兩年。轉(zhuǎn)眼就到了1986年春節(jié)。在軍藝文學(xué)系學(xué)習(xí)的一年半,也是我此生中的黃金歲月——是知識上如饑似渴的一年半,也是創(chuàng)作上激情迸發(fā)的一年半;是時間上爭分奪秒的一年半,也是身心放松空前愉悅的一年半。好日子總是過得特別快,眼看就要畢業(yè)了,第四個學(xué)期是實習(xí)和創(chuàng)作畢業(yè)作品,基本上是在校外完成,時間自己掌握。
2月23日元宵節(jié)一過,春節(jié)也就過完了。滿打滿算,距6月1日返校還有三個月時間,除去五月實習(xí),創(chuàng)作時間只剩兩個月了,好不緊張!畢業(yè)作品沒有規(guī)定寫什么體裁、篇幅多少,只有一個要求,返校報到時把作品交給系辦公室。這就是徐懷中的風(fēng)格,舉重若輕,欲擒故縱,把壓力甩給大家。一年半下來,他心里明鏡似的,誰不想把這一年半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學(xué)以致用,來它一個總爆發(fā),露它一手,放它一炮——至于怎么露,怎么放,大家心里還沒數(shù)嗎?莫言在前面走著呢……
我當(dāng)時因搭上了莫言的快車道,儼然搖身一變?yōu)榍嗄昱u家,畢業(yè)作品寫一篇論文是必須的。但是寫小說的夢想就這樣放棄了?似乎心有不甘。于是從春節(jié)到三月份,整整用了一個半月,整出了一朵“奇葩”——贛西方言小說《地牯的屋·樹·河》。三十多年后,江西文學(xué)界進(jìn)行回顧時,還中允公正地評價道:“朱向前受到新時期文學(xué)創(chuàng)新的精神鼓舞,大膽嘗試、艱辛探索,用贛西方言寫出了小說《地牯的屋·樹·河》。作品在1987年《青年文學(xué)》4月號隆重推出,并同期配發(fā)了文學(xué)系首任主任徐懷中先生的評論《探索性的,又是深思熟慮的》,隨即又被《小說選刊》7月號轉(zhuǎn)載,并入圍1987年度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評選最后一輪。雖然最終鎩羽而歸,但是,該小說不僅首開用宜春方言介入新時期文學(xué)創(chuàng)新的先河,并以一朵絕對奇葩的風(fēng)采挺立于80年代文學(xué)尋根之潮頭。”
再說論文。當(dāng)時我心說,小說就算告別演出吧,咱看家的還得是評論呀,評論家的氣質(zhì)必須拿捏得妥妥的。4月份倒真是憋了一個大招——把一年多來深思熟慮的一個“理論發(fā)現(xiàn)”——軍門子弟與農(nóng)家子弟兩類青年軍旅作家創(chuàng)作之異同撰寫成文:《尋找合點——新時期兩類青年軍旅作家的互參觀照》。該文由《文學(xué)評論》1988年第1期隆重推出,成了我榮登此刊的第一篇正式論文(此前上過一篇筆讀和一個短論,都還不足為據(jù)),也成了此后一個階段內(nèi)我的軍旅文學(xué)批評和部分青年軍旅作家創(chuàng)作的重要參照。
過了五一勞動節(jié),到了“驢友”的約定時間,該岀發(fā)實習(xí)了,問題也來了——按上學(xué)期末系里通知,實習(xí)時間一個月左右,自選方向,自由組隊,差旅費憑票報銷(團(tuán)以下干部不能坐飛機(jī)——同學(xué)中只有李存葆到了團(tuán)級)。條件太寬松了,太優(yōu)渥了。我第一個報名新疆——要跑就跑一個最遠(yuǎn)的地方,不跑白不跑。跟著就有李荃、劉宏偉等五六人報名新疆,系辦公室指定以我為領(lǐng)隊……我心里美滋滋的,覺得自己還有點號召力。殊不料,過了一個年,全都“叛了變”,各有各的理由,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jīng),反正,沒有一個跟我去新疆的了。我心說,不去是你們的損失,我還是我,我還非新疆不去了!正要打點行裝出發(fā)時,還真來了一個小插曲。這事跟我愛人有關(guān)。
我愛人張聚寧,時任江西省宜春行署文化局長,是全省數(shù)得著的最年輕正縣級干部,已經(jīng)列入了好幾個后備梯隊。這不,好事又來了,省委組織部通知她做好準(zhǔn)備,九月一日上中央黨校青干班,學(xué)期一年。怎么辦?莫非我畢業(yè)剛要回來她又去北京?要不然我也找個機(jī)會看能不能先留北京?靈機(jī)一動,我提起筆來就給徐懷中主任寫了一封信,說了一下原因:愛人進(jìn)京學(xué)習(xí);提了一個請求:本人愿在任何一個駐京部隊從事文字工作。第二天把信往軍藝文學(xué)系一寄,我便出發(fā)了。我的目的地是新疆,是南疆喀什,一不做二不休,我要走就走到頭,單槍匹馬,勇闖天涯。
回到北京,屈指一算,時間緊迫。坐火車到烏魯木齊就要三天,往返六天,來不及了。我當(dāng)機(jī)立斷做了一個重要決定:坐飛機(jī)!無非就是機(jī)票自理唄,雖說單程500多元在當(dāng)年堪稱巨款,但借機(jī)開個洋葷也值了!沒想到,有了這一個第一次,就將帶出來一串第一次。我趕到東直門購了票,直通機(jī)場的大巴剛開走了,如等下一班還得一小時,又是一個來不及。怎么辦?坐出租!單程40多元,貴是貴了點,但不是又開了一個洋葷么?值!
待我慢嚼細(xì)咽了飛機(jī)上的免費午餐之后,就品著免費的西湖龍井,雙肘支在小桌板上點燃一支煙——那時我還是一天一包的標(biāo)準(zhǔn)煙槍,那時飛機(jī)上還允許抽煙——此后再無此待遇了,俯瞰窗外藍(lán)天如洗,一朵朵白云之下,西部群山綿延,一望無際,真是心曠神怡,感覺到了人生巔峰。
當(dāng)日傍晚7時許,飛機(jī)降落烏魯木齊機(jī)場。當(dāng)同機(jī)乘客全部走完了,我還沒有看到周濤。
周濤,著名西部邊塞詩人,軍旅詩壇大將,我雖不認(rèn)識,但神交已久——我曾多次拜讀他此前的詩作,散文《蠕動的屋脊》等更見奇氣,堪稱妙品。當(dāng)時我是托新疆軍區(qū)創(chuàng)作室評論家周政保與他聯(lián)系,請他關(guān)照朱氏新疆之行包括接機(jī)。他也都答應(yīng)了,但他卻沒有來。
我跟了一個便車,自己找到軍區(qū)招待所住下了。洗漱之后,約9時許,正是烏市吃晚飯的飯點。我信步軍區(qū)大門之外,尋入一巴扎,找到一烤羊肉攤前坐定,要了40串羊肉串,2瓶啤酒,開始擼串。不夸張地說,這是我此生吃過的最美大餐,妙處難與君說。
雖然當(dāng)天傍晚周濤沒去機(jī)場接我,但我并不在意,一是我們原本就不認(rèn)識,只是托了周政保的關(guān)系,他沒接我是不給周政保面子;二是周濤已是詩歌大咖,我至多是文學(xué)新人,而他還不一定認(rèn)可,他講究的是實力派,這個我懂;三是我獨闖新疆,目的地還在南疆,這人生地不熟的,有問題我找誰去呀?不是還得找周濤嘛。
翌日早飯后,我尋尋覓覓,徑直找上了周濤家。這是我倆第一次見面,年方40的周濤英氣逼人,但說起頭晚接機(jī)之事,略有尷尬,我哈哈一笑,就算過去了。不冷不熱地寒暄了幾分鐘,突然之間話題就跳到了莫言身上——應(yīng)該是因為說起了《紅高粱》,可能周濤剛剛看過。一般情況下,我不是一個善于聊天的人,但只要一說到文學(xué),特別是說到莫言,那就算打開了話匣子啰,主要是他問我說。周濤是智者,又善于傾聽,加上他長期偏于西北一隅,比較閉塞,他有點信息饑渴感;此外,以我在解放軍藝術(shù)學(xué)院一年半的學(xué)習(xí)儲備,聊文學(xué)、聊莫言,可以說都是上好的話題,他聽著還受用。而他每日與博格達(dá)峰對視,所獲得的神示一樣的有關(guān)人生和藝術(shù)的感悟,也不是一般課堂上能聽得到的。我們的投緣是一種相互的激發(fā)與吸引、碰撞與啟迪。就這樣,我上午9點進(jìn)的周家,下午9點出的周家,中飯晚飯都吃在周家。不可思議吧!事后連我自己也覺得匪夷所思,兩個人第一次見面就一連聊了整整三天!好像我此番來新疆就是專門來找周濤聊天的。那真是聊得天昏地暗,樂此不疲,具體聊了什么早都不復(fù)記憶了,但彼時彼地我們對文學(xué)的熱忱與激情由此可見一斑。這在我的交友史上也絕無僅有。
聊了三天既無疲倦也不厭倦,只是時間確實不夠了,我的目的地還在南疆的喀什呢。剛開始兩天,周濤老說不急,路途太遙遠(yuǎn)了,一千五百公里,要坐三天長途汽車,太辛苦了,等我給你找個便車吧……等聊到了第三天下午,他也繃不住了,怕耽誤了我完成實習(xí)計劃,同意我翌日坐長途汽車去喀什。他交給我兩封手札,一封給他的大學(xué)同學(xué)時任喀什公安局長的柳耀華,請他幫忙解決交通工具,爭取把我送到紅其拉甫口岸;一封給喀什文聯(lián)某主席,主要請他給我安排一場講座,原話大意是:這個小老弟肚子里有油水,要好好榨一榨他,不要輕易放過此人……我把此二信札視為周濤從心底里認(rèn)可并接納我的通行證。
翌日一早,我終于爬上了一輛去喀什的長途汽車,坐在最后一排最左邊,還好有半個窗戶透氣。它的一切的臟、亂、差都在預(yù)料中,唯一沒想到的是,腳下軟乎乎的總踩不實在,到底怎么回事?待人們都把大小包裹從空中放下并逐一落座后,我才能彎下腰看清楚,原來瓜子殼和香煙頭在下面鋪了一層,足足有兩寸厚。這得多久沒清掃啊。但這一切都沒妨礙客車在煙霧彌漫和歡聲笑語中歡快地前進(jìn)。當(dāng)?shù)嘏笥训臉酚^情緒也感染了我,雖然聽不懂他們的語言,但他們的笑聲不用翻譯,而且極富感染力。況且,上世紀(jì)70年代中期,我曾反復(fù)深入福建閩西山區(qū)采訪,坐簡易汽車跑簡易公路是常態(tài),早就練出了半天不喝水不撒尿不說話的過硬功夫,現(xiàn)在跑在這廣闊平坦的大路上,只感覺到了一個爽字。
真正突破我認(rèn)知的是晚上住店的情形。
為了將三天的路程兩天跑完,司機(jī)師傅兩頭搶時間,早上7點出發(fā),下午9點收工。車子在一個前不靠村后不著店的地方拐進(jìn)了一個圍子里面,像是一個小學(xué)校操場,圍墻口外有一個小餐飲店,每人吃完一碗羊肉面天就向黑了。司機(jī)大喊:住店了,住店了!人們跟著他復(fù)又進(jìn)了操場,走到一排平房的門口,他大腳一踹,人們往里一瞧,只見一枚15瓦的燈泡散發(fā)出昏黃的光,照著一間足有一百平米的教室一般的房間,里面貼著兩邊的墻筑了兩長條炕,均勻間隔一米,擺放著一坨坨黑乎乎的被子,用手摸上去,厚厚的、潮潮的,還有點滑膩……司機(jī)又喊道:住店的5毛一個哈。有人嘀咕:這能住嗎?我們不住,我們要回車上去……司機(jī)又說:車上過夜3毛一個。忽啦啦一伙人復(fù)又涌上車去,過一會兒,又有一半的人退回來了。這時天已黑下來,困勁也上來了,由不得你不睡。我交了5毛錢,走到最里邊,挨著被子和衣躺下。剛迷迷糊糊要犯困時,起風(fēng)了。風(fēng)越來越大,很快就隨著風(fēng)聲起伏,聽到頭上嘩嘩的響動。趕緊打開電筒查看,原來在天花板的高度上,用尼龍繩拉成的網(wǎng)格托了一層報紙,就權(quán)當(dāng)是天花板了。這時風(fēng)一吹,沙子便落下來,我只好脫下上衣反過來蒙在臉上。在風(fēng)聲中,細(xì)微地感到沙子落在報紙上、衣服上、臉上,還是睡著了……我終生難忘這次住店的經(jīng)歷。
到得喀什,入住地委招待所后,速將周濤手札送到收信人手中。柳耀華局長很重視,在得知我想去紅其拉甫口岸后立馬就告訴我,每周只有一班車,你等不及了,這樣吧,你留下電話等我通知,我來幫你協(xié)調(diào)車子……文聯(lián)某主席看了周濤的信,只是對我笑了笑,說:“我盡量給你安排一次講座吧……”
一早就得到了柳局長的信息,喀什市外經(jīng)委有一部日產(chǎn)巡洋艦要上紅其拉甫口岸接巴基斯坦外商,后排有空位可以帶我上去,但回來時有外商,就不能跟車下山了。去不去?去的話半小時后車來招待所接我。我二話不說,半小時后帶了一件外套就上車坐在了后排。
紅其拉甫位于帕米爾高原,在塔什庫爾干塔吉克縣境內(nèi),海拔5100米。從喀什到塔什庫爾干塔吉克縣城300公里,從塔縣再到紅其拉甫口岸100多公里。在內(nèi)地這絕對算得上是長距離,但我剛從北京飛了近5000公里到烏魯木齊,又坐了1500公里長途汽車到喀什,深切感受到了不到新疆不知祖國之大,1000公里以內(nèi)在新疆不算長途。而且又有巡洋艦這么高大上的越野車,再加上一路大道遼闊平坦,就更有觀景心境了,只覺得滿眼都是風(fēng)光大片,痛惜沒有帶相機(jī)!
不料跑了200多公里后,路況出問題了,一打聽,方知前方在修路,如若繼續(xù)前進(jìn),只能脫離公路主干道,進(jìn)入與路伴行的河道。好在河床裸露,基本沒水,但由無數(shù)大小不同高低不一的鵝卵石鋪就的“路基”實在是太顛簸了,車子就像一個喝得酩酊的醉漢,左右搖晃,高低跳躍著以大約每小時10公里的速度頑強(qiáng)前行,讓人在內(nèi)心深處佩服這車的抗造性。前面4人不時地發(fā)出驚叫,足可以據(jù)其音量大小來判斷車子底盤下面“路基”的狀況。坐在最后一排的我,屁股不能挨座,只要坐實了,就隨時可能伴著車子一個大跳,腦袋咚地一聲撞在車頂棚上。有一陣子搞得我手足無措,無所遁形,幾乎被撞得頭昏眼花。好在我很快就發(fā)現(xiàn)了一個竅門,即雙手伸開抓住兩側(cè)車窗上的把手,將身體提至懸空,屁股始終和座位若即若離地保持15厘米的間隔,完全用雙手和雙腳來支撐身體并調(diào)節(jié)緩沖車子的顛簸,達(dá)到人車一體,自動減震。如此一來,雙手吃勁,但身體獲得了自由,顛簸能奈我何?就這樣,我利用這種獨一無二的“雙杠式坐車法”堅持了一個多小時,熬過河床路。車到塔縣時,暮色四合,天已向晚。因海拔超過了4000,雙臂酸脹疲勞,加上大腦缺氧,草草洗漱,倒頭便睡,一夜無話。
第二天上午我們輕松抵達(dá)紅其拉甫口岸,結(jié)果又大出意外:巴基斯坦商人因故未來赴約,外經(jīng)委同志準(zhǔn)備即刻原車返回,征詢我的意見,是否繼續(xù)跟車,如果不跟那么就此別過了,也就是說把我放下,什么時候再有車?yán)蚁律骄椭荒芸催\氣了。環(huán)顧四周,此處除了口岸,和遠(yuǎn)處的一個哨所、一個雷達(dá)站之外,別無所有。見我一臉糾結(jié),他們又開起了玩笑:你面子好大呀,我們?yōu)槟闵仙讲还馀闪藢\噥恚€派了我們做陪同,你要不跟車走,我們的任務(wù)就沒完成好呢……雖說是玩笑話,但道出了實情,此行我成了最大受益者。我也不能不識抬舉了。在他們的注視下,我走到口岸邊佇立片刻,再默默遠(yuǎn)眺了一下著名的紅其拉甫哨所,就算是到此一游吧。
回到喀什又是晚上。
翌日,終于有一段放松的時間了,看清真寺,逛大巴扎,領(lǐng)略一下南疆風(fēng)情,買了兩把著名的英吉沙小刀……身體放松了,心里卻不知不覺又緊張起來。喀什文聯(lián)主席上午就通知我,已經(jīng)為我安排好了晚上的講座,文聯(lián)人太少,專門協(xié)調(diào)了喀什師專中文系的師生,頗費周章。下午7點半來招待所接我,其他問題見面再聊……電話中我已聽出了主席的一些話外音:安排此講,純屬落實周濤信中所囑,你小伙子面子好大喲……講什么呢?怎么講呢?這畢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個講座,我有點心中無數(shù),有點小激動、小興奮、小緊張。我早早回到招待所午休,養(yǎng)精蓄銳。
下午7點半,文聯(lián)主席領(lǐng)我出門,走出了招待所小樓,也沒見到一個隨員,比如辦公室主任啥的,我們在一輛自行車跟前停住了。這是啥情況呀?文聯(lián)主席開腔說:朱作家,不好意思,我請你就近去吃個便飯,單位也沒個車啥的,這樣吧,你上來,我馱著你,好在不太遠(yuǎn)……我急忙搶過自行車龍頭說:主席,您是老前輩,您坐上去,您指路,我來……就這樣,我騎著講座主持者的自行車并馱著他向著講座地騎去,開始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講座之旅。
9時許,我們趕到了一個我始終沒搞清楚的什么單位,找到辦事員,被告知場地臨時調(diào)整了。到了會場,只見兩個人正在打掃衛(wèi)生,塵土飛揚。到了預(yù)定時間9點半,又有人告訴主席,喀什師專的車還在路上……整個過程,都顯露著人們對這個即將開始的講座的不熱情、不歡迎,甚至是不耐煩。
9點45分,當(dāng)那個小一百人的會議室基本坐滿之后,文聯(lián)主席開始了主持。在他介紹時,會場仍被一片嚶嚶嗡嗡的雜音所籠罩。但這時,我的心中已經(jīng)沒有一絲一毫的緊張了,有的只是一股難以抑制的演講甚至是辯論的沖動。
我忘了怎么開的頭,但反正沒有按設(shè)計的套路來。開言三分鐘后,全場變得雅靜了。在這個暮春的西部邊陲小城喀什,我恣意地與大家分享著新時期中國文學(xué)大潮的壯麗景觀。很快就來到了11點半,聽眾剎不住車了,問答階段更加熱烈。12點時,文聯(lián)主席搶過話筒強(qiáng)行結(jié)束,他激情洋溢,與主持開場時判若兩人。他最高調(diào)最夸張的結(jié)束語讓我至今記憶猶新:同志們,同學(xué)們,我們今晚見證了一個著名評論家脫穎而出的歷史時刻。以后跟人聊起朱向前的時候,大家都可以自豪地說,我聽過了朱向前的第一場演講!
這時候,文聯(lián)的攝影師背著相機(jī)鉆出來,“咔嚓咔嚓”一通猛拍。大家簇?fù)砦蚁聵牵艺龑に贾@下是我馱他呢還是他馱我?結(jié)果出門一看,一輛黑色桑塔納橫臥門前,主席帶著兩個隨員護(hù)送我上車,送到地委招待所。待他們走后,我又獨自出去就著啤酒擼了20串烤羊肉。那才叫一個爽啊!
翌日下午,柳局長請我吃了一個便飯便安排車子把我送到了喀什機(jī)場。雖然飛機(jī)延誤兩小時,夜里11點才到烏魯木齊,但我相信這一次周濤肯定會在機(jī)場等我。果然。上車后,周濤說了一件事:昌吉市文聯(lián)擬請他去作一場演講,咱們倆一塊去講如何?這樣的好機(jī)會和好隊友,我自然很心動,但是我實在不能再待了,急著要回北京返校報到了。
當(dāng)我提前5天回到系里時,卻不由地大吃一驚,多數(shù)同學(xué)早已經(jīng)回來了。我問他們都在干嗎呢?答曰聯(lián)系留京啦、留校啦。我稍一打聽,就基本有數(shù)了,各軍兵種和各大軍區(qū)創(chuàng)作室是第一選項,差不多有一多半同學(xué)——比如我同宿舍的李存葆、李荃、苗長水三位,來自濟(jì)南軍區(qū),這次都一塊進(jìn)了軍區(qū)創(chuàng)作室。另有幾位京外同學(xué)進(jìn)了八一電影制片廠,還有幾個留在系里了……哦,還能留系里嗎?我心想怎么沒早想到這一步呢,給徐主任的信也寫得太晚了……咱就別吭聲了,就當(dāng)啥事也沒發(fā)生過,翻篇吧,該干嗎干嗎。我正在宿舍里聽同學(xué)們講八卦時,系秘書林曉波來敲門了:朱向前,你到趙副主任辦公室來一下。同學(xué)們都怪異地瞪了我一眼。
我剛剛知道徐懷中主任已經(jīng)升任總政文化部副部長了,此刻系里工作由趙羽副主任負(fù)責(zé)。他笑瞇瞇地問我:你是不是給徐主任,不,徐部長寫了一封信?
哦,我不了解情況,考慮不周,給領(lǐng)導(dǎo)添麻煩了,我……
不,我現(xiàn)在代表系里正式通知你,你留系當(dāng)老師了!就在前天,就在這間辦公室,徐部長拿著你的信,請胡可院長、魏風(fēng)政委一起當(dāng)面商定的。祝賀你,向前同志!
幸福來得太突然,我不知所措,有一種缺氧或者醉氧的眩暈感。趙副主任又說道:后天徐部長就要下部隊去檢查工作了,你是不是抓緊時間上家里去看看老主任?
徐主任、徐部長他家住在哪里啊?
在總政歌舞團(tuán),來,這是門牌號……
就這樣,徐懷中把我留校了!
留校以后的多年間,我會偶爾翻出珍藏的“留言布”來摩挲——“留言布”諧了“留言簿”的音,它就是一塊樸素而別致的30厘米×50厘米的小白布,但卻充分體現(xiàn)了徐懷中的個人風(fēng)格和匠心,體現(xiàn)了徐懷中對弟子們的深情和厚望。它是專為1985年12月25日圣誕節(jié)晚會設(shè)計的,全系師生和員工人手一塊,用于晚會上相互留言——考慮到第四個學(xué)期是實習(xí),大家實際上把這個晚會當(dāng)成了畢業(yè)晚會,把這個留言當(dāng)成了臨別贈言。大家寫起來都非常認(rèn)真,覺得一時措不好辭的,還留到第二天甚至下一周再寫。徐主任顯然經(jīng)過深思熟慮,他在我的留言布上提起筆來就寫了一句:我一想到你,就記起你在文學(xué)系第一次討論會上的發(fā)言。
隨后,錢鋼馬上就跟了一句:你的成功在于選擇。莫言倒是十分慎重,先寫了一句魯迅語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第二天又把布要去補(bǔ)了一句:足上又加聚寧嫂。
這塊留言布上這些飽含師生情誼的金玉良言,伴隨我度過了漫長的軍藝歲月。
實際上,除了徐懷中主任,還有趙羽副主任,還有呂永澤、冉淮舟兩位老師和林曉波秘書、劉毅然參謀,他們都見證了我在文學(xué)系的成長。此后的歲月里,我也努力向他們學(xué)習(xí),傳承文學(xué)系的優(yōu)秀基因。比如在不拘一格招人才方面,我學(xué)習(xí)老主任,在打破常規(guī)方面,也創(chuàng)造了兩個紀(jì)錄。一是第四屆的學(xué)生柳建偉,是第三屆的閻連科向我推薦,推薦的作品是一篇萬字評論《偉大的夭折——評<古船>》。評論家不好找,文學(xué)系自第一屆至第三屆,學(xué)生總?cè)藬?shù)已過百,但從事評論者僅我一人。閻連科帶信來說,柳建偉是通訊工程學(xué)院畢業(yè),已獲得學(xué)士學(xué)位,這個大專上不上,他還要考慮考慮……這也許是柳建偉的欲擒故縱之計,但是我已經(jīng)沉不住氣了,立馬寫下了苦口婆心勸柳建偉上學(xué)的信,請閻連科傳遞。大家都知道,歷屆文學(xué)系,特別是前六屆干部班,都是打破腦袋往里擠,只有柳建偉是一個例外,是被朱向前寫信動員來考學(xué)的。這算是創(chuàng)造了一個紀(jì)錄。
第二個紀(jì)錄是第六屆的余飛創(chuàng)造的。他的報考作品是中篇小說《老虎臉排長》的打印稿,也就是說他報考時還沒有正式發(fā)表過作品——而兩部公開發(fā)表的作品是報考前提,也是底線。但是我從這部打印稿中看到了余飛可以預(yù)期的潛質(zhì),于是就力排眾議將他招進(jìn)來了。結(jié)果余飛是個典型的大器晚成者,此后二十多年我一直默默地關(guān)注著他,總是在檢驗自己是否判斷失誤。一直到了前兩年,兩部由余飛總編劇的電視劇《跨過鴨綠江》《巡回檢察組》橫空出世,我才終于松了一口氣。
我在文學(xué)系前后13年,和文學(xué)系一道成長,尤其結(jié)合自己的評論專業(yè),為以后的著名學(xué)員如閻連科、徐貴祥、麥家、柳建偉、石鐘山、趙琪、陳懷國、李鳴生、余飛等人的脫穎而出錦上添花,從推薦作品、撰寫評論到作序,無不竭盡綿薄之力。
【作者簡介】 朱向前,著名文學(xué)評論家;1954年1月出生于江西宜春,原解放軍藝術(shù)學(xué)院副院長;著有《詩史合一——毛澤東詩詞的另一種解讀》《莫言:諾獎的榮幸》《軍旅文學(xué)史論》等專著、文論集二十余種;主編《中國軍旅文學(xué)史(1949-2019)》《中國軍旅文學(xué)經(jīng)典大系》等;曾獲魯迅文學(xué)獎、解放軍文藝獎、2008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優(yōu)秀成果獎;現(xiàn)居宜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