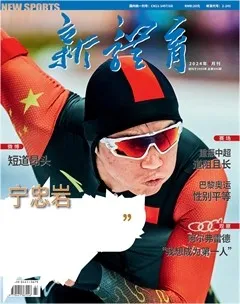外援新規死水微瀾
張子淵

曾經的中超射手王扎哈維,提升了廣州富力的成績,也提升了中超比賽的觀賞度。
一場中超比賽,除了守門員,雙方20名球員中有10名外援,這樣的一幕在新賽季的中超出現。
1月3日,中國足協發布了2024賽季中國職業聯賽相關文件,其中引人矚目的是中超聯賽外援人數的變動。根據新的規定,新賽季各隊可以讓5名外援一同登場。這一巨大改變頗為無奈,但這種無奈激發了各界對中國足球的關注,給這潭死水帶來了一些活力。
謹慎對待 調整頻繁
中國足協在2024賽季相關文件中提出,中超各俱樂部注冊外援人數累計不得超過7名,每場比賽外援報名最多5名,上場最多5名。相比上賽季,最大的變化就是中超外援上場人數從4名調整到5名,意味著一支球隊中除守門員外,一半位置將可能由外援承擔。這是中國足球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戰。
自從職業化起,對外援的出場限制一直非常謹慎,30年來調整了13次,最近幾年受到疫情和U23規定等影響,調整尤其頻繁。“平衡”外援和本土球員的出場機會,始終是調整的根本。
1994年中國足球開始推行職業化,允許各隊配備外援,但當時各隊的理念還沒有跟上,很多球隊沒有外援。從1994年到2002年間,各隊可以擁有3名外援,同時登場,那個年代,“三個火槍手”、“三劍客”、“三駕馬車”都是送給各隊外援組合的常見稱號,最有名的就是北京國安的“三桿洋槍”。從2001年起,中國足協要求各隊不得引進外援門將,這個規定一直延續到今天。
到2003甲A末年,為了增加頂級聯賽競爭力,中國足協允許各隊同期注冊4名外援,出場人數仍是3人,外援也要“ 競爭上崗”了。2004年中超啟動后,外援規定回到了注冊3人、上場3人,到2007年放開為注冊4人、上場3人。
2009年起,外援規定發生比較大的變化。亞足聯改革亞冠聯賽,中超球隊參加亞冠聯賽要遵守亞足聯的外援規定,由此產生了所謂的“亞洲外援”,即亞足聯成員協會的球員。2009-2016年,中超聯賽實行的外援規定是注冊“4+1”,上場“3+1”,各隊可以同時注冊4名非亞洲外援和1名亞洲外援,但只能有3名非亞洲外援和1名亞洲外援同時上場。
2009-2016年間,中超外援規定沒有經歷過大幅調整,但4名外援同時登場的情況壓縮了本土球員的出場機會,尤其是還存在一名替補外援。各隊往往把替補外援用在進攻線上,直接導致本土前鋒的生存空間受到擠壓。
于是,從2017年開始,中超外援規定屢屢調整。中超取消了所謂的“亞外”規定,外援人數變成注冊5人,出場3人,明顯是“保護”本土球員的出場機會。2018年,為了增加本土年輕球員鍛煉機會,外援出場人數開始與U23球員掛鉤,仍為3人,但不能多于U23的出場人數。2019年的外援規定一年兩變,先是注冊4人出場3人,隨后又將累計上場3人次更改為同時上場不得超過3人。到了2020年,中超聯賽外援規定調整為“同時上場4人、同時報名5人、同時注冊6人、累計注冊7人”。直到2023賽季,中超聯賽各隊外援出場名額都是4人。
從中國足球職業聯賽的歷史來看,2024年中超聯賽允許各隊同時有5名外援登場前所未有,創外援同時登場人數新高。
國際潮流 被迫順應
總的來說,中國足球對外援的放開非常謹慎,因為在外援身上吃過虧。
2009年起,中國足協緊跟亞冠外援“3+1”的規定,推出了注冊“4+1”,上場“3+1”。很多中超俱樂部把外援用在了球隊的中軸線上,即中衛、中前衛、中鋒這些關鍵位置,中國球員只能成為外援的輔助,去踢邊后衛、邊前衛。還有一名替補外援,往往是前場攻擊手。
各隊往往配備兩名外援前鋒作“雙保險”,直接導致本土前鋒失去了展示空間,郜林、楊旭等前鋒只能被迫改踢邊路,有的中鋒要么淪為替補,要么被改造成中后衛。后來在國家隊擔任中鋒的肖智、畢津浩等人,都在不同時期踢過中后衛。

2021賽季因疫情改為賽會制,廣州賽區舉行圣誕節活動,各隊外援齊聚一堂。
當外援占據整條中軸線,成為球隊前場、中場和后場的核心以后,中國球員對他們的依賴感越來越強。“不知怎么弄,球給外援送”,成了中國球員的本能反應。北京國安的法國外教熱內西奧曾直接點出這一問題:“他們太依賴外援了,不敢承擔場上的任何責任。”
一些本來有能力和特點、可以擔當組織重任的球員也被迫改踢邊路,如蒿俊閔、張稀哲、尹鴻博等,導致國家隊層面缺少好的中場球員,國際比賽中往往群龍無首,一盤散沙。
中國足協現在做出增加外援的決定,其實也是無奈之舉。畢竟,增加外援是職業足球全球化的必然趨勢。尤其是在亞洲,增加名額或取消外援限制成為一股無法阻擋的潮流。
亞足聯將2023-24賽季的亞冠聯賽外援使用名額從過去的“3+1”增加到“5+1”。從2024-25賽季開始,亞冠精英聯賽為首的三個級別聯賽將全部取消外援限制。亞洲其他國家已經搶先調整了外援規定:沙特聯賽外援名額從8人擴展到10人;日本J聯賽和阿聯酋聯賽已經不受外援名額限制;韓國K聯賽緊跟亞足聯腳步實行“5+1”,并將在2025年起取消亞外名額,允許6名外援;泰超聯賽外援增加到9人;澳大利亞聯賽外援名額是“5+N”,即5名外援和生長在海外或代表其他足協出場的澳大利亞球員。
相比之下,中超聯賽的5外援雖然對自身是一次大的突破,但仍然落后于整個亞洲足壇。

上海上港奪得2018賽季中超冠軍,艾克森與奧斯卡手捧火神杯。
除了順應大環境之外,增加外援的另一背景在于當前中國球員水平已經沒有競爭力。無論3外援還是5外援,給中國球員再多的機會,鍛煉意義都不大,只能使中超聯賽的水平和影響力越來越低,中國足球越來越脫離國際軌道。
80后球員老去,1993-2000年齡段的本土球員就算沒有外援競爭,就算中國足協制定再多的規定來扶植,也很難有大的突破。過去,中國足球還有武磊、楊旭這樣的前鋒和蒿俊閔、張稀哲這樣的中場球員值得保護,但93后球員需要的不是機會,而是必須在嚴苛的環境中激發潛能。
那么,增加外援反而是一種不錯的嘗試,更激烈的競爭也許會帶來更多的驚喜。
無論是近鄰日韓,還是西亞的沙特、卡塔爾、阿聯酋,亦或是足球水平并不高的泰國、越南、菲律賓,都沒有因為單純增加外援數量而導致本國足球水平下降。在外援的帶動下,這些球隊都取得了不小的進步。
維持水平 鍛煉球員
幾年前有一種說法,既然本土球員不留洋,何不放開外援限制?本土聯賽多些外援,不就相當于中國球員實現留洋了嗎?如今,這種“反向留洋”的說法眼看要實現。
“反向留洋”確實能夠促進現有中國球員水平的提高。因為外援增多了,訓練和比賽的質量就會提高,同場訓練和競技的中國球員自然也在更高水平的環境中得到了鍛煉。
這些年來,中超聯賽一直靠外援維持水平,相比甲A時期,本土球員的影響力大大降低。過去甲A時代還有范志毅、高峰、彭偉國等明星球員,京派、海派、粵派的足球風格也十分清晰。現在的中超賽場如果把外援拿掉,水平甚至不如當年的甲B。從上賽季足協杯來看,很多中超球隊在失去外援后,競爭力與低級別球隊沒有多大區別。前幾年中超球隊在亞冠賽場取得好成績也能夠佐證這一點,即外援是中超球隊的支柱,也是整個中超聯賽水平的保障。

金玟哉(中)是少有的離開中超加入歐洲豪門的外援。
增加外援,提高聯賽水平,有助于本土球員成長,也勢必擠壓他們的成長空間,但這種競爭是職業聯賽的優勝劣汰。一部分球員會從中超賽場流向中甲、中乙,提高低級別聯賽的整體水平。
增加外援后,聯賽水平有了保障,才能夠吸引更多關注,從而盤活整個聯賽和俱樂部的經濟運轉。企業需要的是效益,投入看的是回報,聯賽和球隊水平提高是吸引投資的關鍵。
中超聯賽這些年的運營舉步維艱,多數俱樂部陷入經濟困境,與多年來球隊培養不出明星球員形成相互影響。本土球員羸弱,球迷和贊助商都提不起興趣,不如把這個展示球隊、展示城市的機會留給外援。而且,跟此前總有一名外援處于替補相比,增加上場名額避免了俱樂部浪費資源。
外援帶動聯賽提高水平,成績乃至生存都與外援的聯系更加緊密。有好外援就能出好成績,沒有好外援就只能保級。如何找到物美價廉的外援,成了各家俱樂部的重要任務。當前,中國足協對俱樂部的投入限制沒有改變,俱樂部不能像以前那樣一擲千金。這種環境考驗著俱樂部高層的眼光,5名外援的發揮和作用將左右球隊的成績和聯賽走勢。
出場外援增加到5名,只是中國足球發展過程中的一小步,未來可能會有更大幅度的調整,讓出場外援增加到6名、7名,甚至更多。
不難發現,當外援只有3名的時候,球隊往往把他們放在中路或集中在進攻線上。當外援增加到4名時,就有球隊把外援分散在進攻和防守位置。當外援增加到5名時,使用就更加靈活了。若提升到6名,位置一定會分散。之前人們擔心外援增多導致某一位置長期被外援占據,這種情況會迎刃而解。
放開外援限制對球迷和中超都是好事,對各俱樂部也非壞事。既然利大于弊,堅持跟隨國際潮流走下去便是。至于擠壓中國球員生存空間,可能是投向中國足球這潭死水的一塊石頭,本土球員不能總靠規定的傾斜才踢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