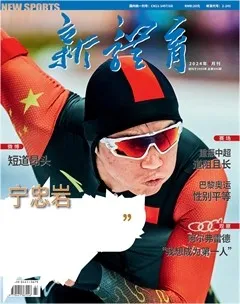乘風破浪的加納女孩
廖建蓉


上世紀60年代,《沖浪者》雜志刊發標題為《非洲:沖浪之家?》的文章,并制作了一幅漫畫配圖,畫的是一名部落男子從海浪中拖出一塊木板。近60年后,電影制作人薩拉·休恩在社交平臺上將那篇文章發給同事本尼托·拉蘭德,與他談論新項目。沒過多久,拉蘭德和休恩帶著團隊前往加納海灘小鎮布蘇阿,將鏡頭對準在晨光下乘風破浪的沖浪者,拍攝了一部以女性沖浪愛好者為主題的短片。
在布蘇阿,沖浪是一項歷史悠久的傳統運動,不過,影片中出現的所有沖浪者都是女孩。這些女孩正在顛覆傳統,因為在加納,不允許女孩參加沖浪運動。瓦妮莎·特克森笑著回憶說:“有一天我去沖浪,媽媽用平底鍋揍了我一頓。媽媽告訴我:‘我不想失去你。”特克森的一名朋友透露,她的父母會檢查她的腳,一旦發現有砂礫,就會懲罰她。
從某種意義上講,當地村民之所以不允許女孩沖浪,并非沒有道理。在加納海岸線附近,幾內亞灣充滿危險的洋流,人們出海捕魚謀生,每年都有很多人溺水身亡。幾乎每隔幾個月,就會有一具尸體被沖上海灘。奇怪的是父母對待男孩的態度與對女孩完全不同,會鼓勵男孩學習如何駕馭當地的海浪。
直到賈斯蒂斯·科沃菲和6個兄弟共同創辦并經營一家沖浪學校,在當地延續了幾十年的傳統才逐漸被打破。科沃菲發現每當放學后,女孩們總是待在家里幫父母做飯,或者做家務活。“我年齡很小的時候就失去了父母,和祖母一起生活。祖母去世后,另一個女人照顧我。我的沖浪學校也得到了一位女性的支持。我意識到,非洲女性的生活非常艱苦。男孩們經常去海邊玩,回到家就等著吃飯。這不對,我們也需要做些什么,讓女孩成為我們的一部分。”
5年前,科沃菲發起了被稱為“黑人女孩沖浪”的項目,教布蘇阿當地女孩先學游泳,然后學習沖浪。那個曾經被揮舞著平底鍋的母親在廚房里追來追去的女孩特克森取得了父母支持,是首批報名參加的學員之一。通過這個項目,特克森不僅學會了沖浪,還收獲了快樂和友情。她笑道:“每當和朋友們坐在水邊聊天時,我都覺得很開心。我站在沖浪板上,感覺就像在飛翔。沖浪是一項非常解壓的運動,人人都可以參加,就像跳舞那樣。以前人們常說女孩不能沖浪,現在我知道了,男孩能做的事情,女孩都可以做得更好!”
科沃菲表示,自從沖浪俱樂部在布蘇安成立以來,當地未成年少女懷孕率有所下降。這是加納唯一的女子沖浪俱樂部,旨在為年輕女性提供一個游玩、學習和社交的場所。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沖浪運動在非洲有悠久歷史,不是從波利尼西亞、加利福尼亞或其他地方引進來的。有人發現早在1834年,一位隨部隊駐扎在布蘇阿海岸的蘇格蘭士兵就記錄了當地人的一項奇怪活動,“在海灘上,有時可能看到幾個男孩在海里游泳,肚子下放著一塊輕型木板。他們等待海浪到來,然后像云那樣在浪頭翻滾。”
如今,布蘇阿的風景和沖浪熱潮吸引了許多電影制作人和攝影師,還帶來了商機。一家名為“沖浪加納”的機構創始人桑迪·阿利伯指出,無論當年的故事多么動聽,加納沖浪業的發展仍然依賴于冰冷冷的數字,“在村子里,人們首先想到的是錢。當地人的生活非常艱苦,月均收入僅26到32英鎊。父母的首要工作是照顧好女兒,確保女兒嫁給有能力照顧她,甚至照顧全家的人。”
阿利伯說:“沖浪仍然是一項奢侈運動,大部分女孩從未接觸過。按照村莊的傳統,女孩甚至不應該出門,每天從學校放學后回到家,幫助父母做家務。我想,如果父母發現沖浪能夠賺錢,他們或許就會愿意讓女孩學習沖浪。我還在阿克拉發展沖浪運動,留意到只要某項運動能夠創造工作機會,父母就會鼓勵孩子參加。這種轉變既直接又有效:如果是沖浪者,就能找到工作。這是讓當地人意識到他們能夠從中受益的唯一途徑。”
在體育用品品牌的支持下,“沖浪加納”建造了一家俱樂部,喜歡沖浪的年輕人可以在那里交流,參加各種活動。科沃菲在談到他曾經教過的沖浪女孩時感嘆道:“每當看到她們乘風破浪時,我都會心情激動。在這里,沖浪運動確實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