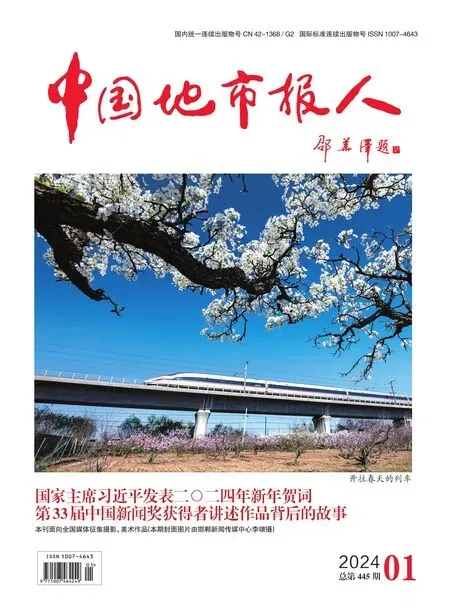新聞報道中使用監控錄像素材須注意的倫理問題
趙志強 李 薇
電子監控視頻具有真實、客觀及無可辯駁的實證性,在新聞報道中,發揮著無可替代的傳播作用。在了解其積極意義的同時,監控視頻在新聞報道中的不當使用而引發的影像倫理問題,包括監控視頻的使用授權、保護民眾屏幕形象、隱匿敏感暴力畫面等問題值得深入探討。
一、注意監控錄像的使用授權
面對浩如煙海的視頻監控影像庫,新聞媒體可自由使用監控錄像的空間并不是無限廣闊的,而是有所限制的。
首先,使用一些特定的監控錄像必須得到相關部門的授權。我國頒布實施的《公共安全圖像信息管理條例》中規定了公安部門的直接管理權限,另外,發生突發公共事件(社會治安、公共衛生、自然和事故災害)時,新聞媒體可以作為調查組成員(信息發布平臺)的身份,將相關監控視頻信息公開,而在關乎警務信息和政務信息公開的問題上,相關部門對媒體的配合與協助同樣是責無旁貸的。
其次,使用授權問題還表現在是否征得被攝錄者的同意。我國是一個法治國家,對普通公民的跟蹤、偷拍、監控等行為,涉嫌侵犯公民的安全及隱私權。故而,在新聞運用中監控錄像素材需要尊重被攝錄者個人的意愿。
二、防止公共權力對個人空間的過度“侵入”
監控網密密麻麻地分布在城市之中,其目的不是要盯著每一個實際的故事看,盡管這始終是一個重要目標,不如說,這更多的是為了預見行動,為不測事件做準備。[1]然而,公眾現在已經普遍對公共視頻監控系統的定位、攝錄等功能產生了顧慮,同時現階段這種監控使人們感受到了不斷增加的侵入性壓力,擠壓了個人空間,讓個人隱私無處遁形。漢斯林德在文章中說到,“國家在保護高重要性權利時是采用限制低重要性的個人權利來實現的,而實際生活中當個人權利受到侵害時它和自由表達同等重要”。[2]米克爾約翰認為公民在公共場所享有匿名權,從而確保自己在公共場所不留名。[3]2020年8月18日,一段監控錄像視頻在各大短視頻平臺上廣為傳播,視頻中人們能夠看到兩只大型寵物犬在路上奔跑戲鬧,一只狗的牽繩帶倒路邊一位老人,老人摔倒后,一名未成年人牽著狗飛快地逃離現場。而各媒體在轉發過程中并沒有依據法律規定,遮擋其面部以體現對未成年人的保護,未能實現“未成年人的利益最大化”。
個人隱私權和公共監控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沖突。現在只要我們走出家門,觸目所及的都是視頻監控。網友曾調侃說,現在的人們都是透明人,因為我們無時無刻不處于監控監視之下,我們的一舉一動,無論是路上,還是餐廳抑或是商場,都已暴露在監控錄像的攝像頭之下。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個人隱私與公共場所監控之間的矛盾已經愈演愈烈。
公共場所的隱私權本來就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使原本止于房門之內隱私權擴展而來的,只要離開家門進入其他公共性場所,也就被迫放棄了自身的部分隱私權,這是理論界形成共識的一種觀點,也就是隱私權的克減,同時這種觀點也獲得了實踐的檢驗。解決公共場所監控和個人隱私權保護間的矛盾,如果只依賴于公民來克減隱私權利并非是最佳手段,而且也無法起到有效的緩解效果,一味地規制公眾而不規制監控主體,也不符合社會公序良俗。而最有效的辦法應由國家層面來制定明確具體的監控設備管理制度體系,其中應包括監控設備安裝前、中、后涉及的所有內容,不僅要規范安裝管理,而且要規范安裝后的應用,更要規范其中獲取的相關信息,以有效遏制公共場所視頻監控對公眾個人空間的“侵蝕”。[4]
三、避免監控錄像的“視覺侵擾”
本文中的“視覺侵擾”是對監控錄像實時記錄下的部分包含視覺恐怖和視覺“品味”等具有視覺沖擊力的探討。
視覺恐怖是指影像中包含的視覺侵擾的部分,以至于讀者在閱讀和觀看情況下感受到視覺上的“恐怖”。通過借鑒攝影行為,一方面賦予影像生產者一個介入他人生活的緣由,另外將他置身于旁觀者的境地。在這兩種原因的推動下,部分不考慮被拍攝者的感受,不講情面地爭奪影像的行為便會發生,而從本質上來說這種掠奪行為也是一種視覺暴力,是對他人生活一種極其野蠻的入侵。[5]
新聞報道任務中的視頻監控圖像內容大部分是犯罪違法案件證據,另外還包括被社會廣泛關注的公共安全或意外事故等。這些監控錄像中大多數含有暴力情節,特別是關于刑事案件的錄像。若是不進行任何加工就播放出來是完全背離了對當事人的人道主義關懷。一直以來有很多未經處理的重大刑事案件的現場監控錄像被直接播放出來,引起公眾一片嘩然,甚至在網上迅速轉發,引發網絡輿情。
作為公共安全防控的監控拍攝的視頻在拍攝時間與拍攝角度上都保證了其“客觀中立性”,但電子監控視頻中存有大量原生態的畫面,這些畫面可能是通過道路監控攝像頭記錄的車禍慘劇,也可能是犯罪分子作案過程中的慘烈現場,還可能是普通人的激情犯罪,或是幼兒慘遭傷害的畫面,慘不忍睹。這種未經處理的“原生態”畫面對每個看到它的人來說,都是一種心靈的傷害,這些錄像被媒體報道并對外播放過程中應該進行處理并接受更嚴格的審核。
視覺“品味”多指新聞媒體的報道偏向,是對新聞題材的選擇傾向。[6]正如真人秀、直播等直觀的播放形式,監控錄像所展示的東西,通常憑借其戲劇性的變化、難以預料的結果以及現場真人展示效果,吸引了眾多觀眾。
媒體人在編輯新聞素材的視覺元素過程中,通常采用“視覺沖擊力”這個定義。比如《巴黎競賽》這部作品,以敢于采用圖片而著稱,它給自己的評價是:圖片大膽,文字內涵豐富,這個評價的定位是認為自己的視頻內容和文字內容是非常厚重的,而采用視頻的目的是引起廣大觀眾的興趣。而恐怖的、嚇人的,讓人們感到威脅的照片往往先天具備生理意義上的視覺沖擊力,然而它所造成的沖擊力不是出于人的理性,而是一種最原始的生理反應。對于廣大觀眾而言,這種沖動是出于本能,是不能通過理性情感所影響的。大眾的這種感官特性,就被部分僅關注注意力的媒體利用,形成這樣一個惡性循環,為吸引更多的注意力,繼續生產更多恐怖圖像。作為商品生產無可替代的背景,并對主題進行闡述,作為利用媒體傳播獲得的行業,景觀是他們目前的主要產品。[7]實際上,奇特的景象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中一直以來的現象。圣像崇拜(中世紀)、狂歡節(拉伯雷時代)、人類祖先舉行的宗教儀式、大革命時代的慶典、斷頭臺,這都形成了奇特的景觀。[8]觀者的恐懼感成就了影像發布者的財富,對視覺沖擊力的執著追求也逐步轉化為視覺上的一種暴行,在經濟社會中展現在媒體面前的就是一種“奇觀”,變為廣大觀眾與媒體人的一種畸形的愛好,成為影響社會的隱患。
四、糾正監控錄像偏離新聞真實的報道傾向
視頻錄像包含著眾多內容信息,它在公共傳播過程中因為其特殊性關系到各種權利和利益,所以在這些視頻監控錄像通過媒體傳播被公眾看到之前,必須對其進行一定的編輯處理。比如對于隱私性信息必須給予保護,或是將部分無關的圖像信息刪除,尤其對于涉及犯罪案件的監控錄像的報道中,更容易走入“媒介審判”的誤區,真相的展露是一個過程。視頻的過度剪輯也會造成真相的失真。圖像本身是客觀的,但人們的解讀可以是多元的,應避免主觀性太強的報道傾向。
監控錄像素材的剪輯方式影響著新聞事件真相的揭露。鏡頭的切換和視頻不同角度的呈現,都左右著真相的展露。監控視頻自身也存在一定的限制,這種限制就是攝像頭,這種物理設備限制了拍攝的范圍。然而有所區分的是,拍攝者能夠通過選擇影像的內容,通過靜止與運動物體的科學組合,采用蒙太奇表現主觀意象,給畫面賦予一些特定的含義,使觀眾能夠從多種角度解讀錄像的內涵,可以不以拍攝者的主觀想法去解讀其中的意義。[9]監控攝像頭完全是客觀記錄,具備客觀性,沒有剪輯、沒有暫停、景別單一,然而錄像信息通過剪輯表達出的含義并非只有一個。這是監控錄像的客觀性使部分創作者忘記了某個方面:圖像是其創作作品的本質,具備多義性。監控視頻所展現出來的多是聲音影像,信息內容有限,監控視頻拍攝者在編輯過程中有些偏差。在新聞事件中,監控視頻由于沒有聲音,使圖像內涵的多義性凸顯,加之視頻經過加工,略過了許多細節,在文字報道的配合下,使圖像的多義性消解。
在重慶萬江公交車墜江事件中,僅憑事件當場后車的行車記錄視頻,不足以看清事情真相,事件持續發酵之時,紅色轎車的女主被推到風口浪尖,眾聲喧嘩。視頻監控所展現出來的并不一定是事情的全部,圖像可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正如前面提到的,視頻監控含義的多義性可以對它做出多種解釋。未進行深入、翔實的訪談,就想當然地主觀臆斷,結論下得太過隨意。而始終持客觀公正態度報道新聞事件,報道過程中務求不帶任何感情色彩地敘述事實,為事件的相關當事人提供公平的陳述事實的機會,避免以自己的主觀傾向進行事件的報道傳播。在以前的新聞媒體報道中,新聞從業者違背媒體傳播的客觀性要求開展媒體傳播工作,導致做出了錯誤結論,造成新聞報道失去真實性的情況而造成新聞反轉,這是要特別引起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