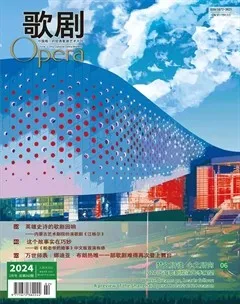推開一扇新世界的大門
鄭夢雨
2023年10月20日晚,由廈門市鄭小瑛歌劇藝術中心制作的《帕老爺的婚事》中文版在泉州大劇院歌劇廳拉開了帷幕。中場休息時,熱情的觀眾們,紛紛涌向了同樣坐在觀眾席中的本劇藝術總監、著名指揮家鄭小瑛身邊,希望得到她的簽名、合影留念,更希望向鄭小瑛表達自己的所聞所想,以及自己激動的心情。
《帕老爺的婚事》,原譯作《唐帕斯夸萊》,是多尼采蒂最后一部喜歌劇作品。1990年,由鄭小瑛執棒,該劇意大利語版在國內首演。時隔22年后的2012年,鄭小瑛帶領團隊,重新創排了該劇的中文演唱版本。2023年6月,該中文版首次以音樂會版形式在福建大劇院成功上演,導演王杰與制作團隊對于該劇的理解及設計理念在這場演出中初現端倪。10月,《帕老爺的婚事》帶著全新升級的制作規格來到了泉州。這更是泉州第一次上演西方經典歌劇,這顆諾麗娜口中最愛的“音樂皇冠上最燦爛的珍珠”,第一次在現實中,以完全的姿態展現在了泉州觀眾們的面前。
當場燈暗下,當鄭小瑛的導賞視頻結束,當指揮鄧卓銳帶領上海愛樂樂團在樂池中奏響序曲的那一刻,現場觀眾感覺到:暫時離開了現實,來到了一個似是非是、美輪美奐的夢幻世界。隨著劇情的推進,現場歡笑此起彼伏,甚至摻雜著不少孩子的笑聲,這可是在被視為“曲高和寡”的歌劇演出現場極少見到的現象。這種良好的舞臺上下呼應,歸功于鄭小瑛理念方向上的明確把握,歸功于王杰導演帶領整個劇組團隊的精心制作,歸功于鄧卓銳指揮與上海愛樂各位演奏家們細膩的音樂表達,歸功于李鰲、周旎、馮浩然、李彪等主演與合唱隊員們的精彩演繹。
讓大眾聽懂歌劇、看懂歌劇,這是鄭小瑛歌劇藝術中心的工作初心,也是工作重心。在本劇前期籌備階段,鄭小瑛便規定了如下基調:劇中所有人物必須嚴格遵照并符合其時代特性與形象風貌;在此基礎上要盡可能貼近大眾,加強大眾理解之便利性。
圍繞這一理念,以中文演唱為核心,王杰導演進行了從舞美服裝等視覺效果,到表演形式與風格的一系列適配性設計創作。首先,如何去定義這16米×9米的舞臺空間。在明確了大多劇情均在室內完成,僅有一場花園的室外戲也可依托室內構景延伸發展后,王杰導演攜同以李耿為首的舞美設計團隊,提出了旋轉的鏤空八音盒這一布景思路。
轉臺的使用強調了劇目中始終存在的流動概念:時間的流動、空間的流動、音樂的流動、劇情的流動。同時,舞美團隊給出的鏤空方盒場景設計方案極大助力了這一概念的實現。方盒的四面,表象上是四個不同的空間場景,但因方盒內部鏤空的特征,使得四個場景之間存在著超越時空限制的互動可能,也大大擴展了觀眾的想象余地。
在這樣的布景下,觀眾看到了第一幕中,叔侄倆爭吵的同時,諾麗娜正翹首盼待醫生即將帶來的好消息,對未婚夫此時身處絕望一無所知;看到了第二幕開始時,悲傷的埃內斯托提著箱子,帶著離別的痛苦,走過他生活的家,走過心愛之人的窗沿之下,也走過他曾經富足美好的那些歡樂時光與回憶;看到了第三幕里,當一對心愛的年輕人正陶醉在相聚的愛情甜蜜中互吐衷腸之時,可憐的帕老爺還蒙在鼓里,和醫生喋喋不休地討論著計謀,全然沒有注意到自己的“大舅哥”眼中奇怪的閃動……場景成為抓牢觀眾深入戲中的絕佳協助。
而在顏色屬性上,導演大膽地選用了粉色作為舞臺主色調。帕老爺的婚事里一定要有浪漫、有美好,這決定了應以暖色調為主;婚事中又存在著各種輕松詼諧的喜劇元素,淺色調也闖進了舞美設計團隊的思考之中;婚事里更充斥著各種荒誕離譜的橋段與體驗,粉色這一奪人眼球的色彩,便成為最能體現劇目精神的色調選擇。這抹亮色,更是在帕老爺表面的主角形象之下,實際突出了這個機敏又帶有一絲狡黠的諾麗娜。這個被一群男人圍繞著、自信張揚游刃有余的年輕姑娘,她,才是本劇真正的主角。
服裝同樣也是一大亮點。在布景拿出了如此現代思維且富有沖擊力的視覺方案后,雷晉巍帶來的服裝設計卻極為嚴謹地遵照了19世紀時羅馬的社會風貌。大到整體形制,小到某一處的蕾絲裝飾與雕花,都鮮明地表現出了角色的人物身份、社會地位與性格特征。細節分明的設計豐富充實了角色形象,而扎實的角色形象又與造景形成了人實景虛的獨特搭配,這讓觀眾在欣賞中既能具象地認識角色、理解角色,同時又可以在更為超越的層面展開自己的想象,不被限制與束縛。
配合著充滿新意的視覺效果,在具體的表演風格上,各位演員也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劇中充滿了大量“啞劇”式的表演特點,這同樣也是在其他劇作排演中非常少見的:帕老爺氣急敗壞時漫天揮舞著手臂、諾麗娜在驚詫時瞪大的雙眼與夸張的捂嘴、公證員在做婚姻登記記錄時幾乎要埋到稿紙里去的頭……夸張的肢體動作,既強調了作為一部喜歌劇的幽默屬性,又對臺詞念白與歌唱做了大量的表現補充。

而這種夸張,除了在表演風格上的展示,甚至在歌者實際演唱中也有所體現。第二幕中的公證員在聲部上被定義為男高音,但演員陳鵬駿完全放棄了自己本身的男高音音色,換掉了歌唱中正常的腔體狀態和技術要求,寥寥幾句歌詞,被他用一種類似于鴨子叫一般扁平、高亢且尖銳的滑稽聲音表現了出來,這也引發了全場的熱烈回應與反響。
值得一提的是,伴隨著臺本的中文譯配化,劇作無論是在音樂進行上,還是在表演設計上,都做了大量的適配工作。
鄧卓銳指揮與上海愛樂樂團展現出了對音樂極強的控制力與表現力。弦樂的處理格外細膩精致,管樂組的表現富有閃光點,整體不過分追求奔放與進攻,而是引領劇情娓娓道來,并根據漢語的重音及語速特點,在節奏感與速度上多處進行了配合處理。
導演在表演細節上設計了諸多本土化的“包袱”。比如帕老爺與諾麗娜在醫生馬拉泰斯塔的引領下第一次見面時,大多數版本在此的處理都是將帕老爺的心態與行為展現為一個害羞、羞澀,同時又想展現自己作為一位男性的紳士風范這樣一種富有西方思維的效果表現。但在李鰲精彩的演繹下,此時的帕老爺緊張、無措,渾身發抖,說話結巴,口齒不清,沒說兩句就趕緊躲到了醫生的身后,這不僅充分利用了中文的語言特點,又將傳統的西方思維巧妙的轉化成我們中國人所熟悉的一種表現形象,從而更為貼近了大眾視角。
采用了大量的戲曲表演形式與表現手法。正像前面所提,導演團隊一直在追求一種“人實景虛”的表現效果,在諸多室內布景中,家具的呈現大多僅僅是一桌一椅或一桌二椅,與本劇的其他一些傳統制作形成鮮明對比。中文版中這種高度假定性的抽象表現,也更符合中國大眾的審美認知與喜好傾向。
在純文字念白的表現上,本制作也借鑒了大量的戲曲與音樂劇的表現元素。由于涉及翻譯的特性,會有原版中諸多宣敘調內容被改寫成了純文字念白。為了更好地表現語言特點,提高念白與歌唱之間過渡的自然感,導演做了大量的類似于戲曲中鑼鼓點配合的節奏處理,以及音樂劇式的過渡手法。
這場“鬧劇”在經歷了“花園風波”后,伴隨著諾麗娜唱起歡快的圓舞曲,帕老爺坐在角落里悶悶不樂,有情人終成眷屬,大幕也緩緩拉上。經久不息的掌聲與喝彩令人無法忽視這樣一個事實:這畢竟是泉州第一次上演歌劇啊!而我們的觀眾,大多數并不了解這種藝術形式,甚至可以說,他們對古典音樂是陌生的。而就是這些觀眾,在這個夜晚對歌劇爆發出了極大的熱情,因為他們在這場戲中,真正地看懂了近200年前,作曲家想讓觀眾們看懂的東西——一個可笑又可愛的故事。
鄭小瑛發起的這項事業,無疑是極具魄力的。因為長期以來,西方古典聲樂作品,無論體裁是歌劇、室內樂還是當地民歌等,是否應被允許以中譯本形式演唱,在學界一直存在著強烈爭議,持反對態度者也占大多數。理由不外乎如下幾項:唱漢語版本是一種逃避學習原文語言的偷懶行為,也在一定形式上違背了遵照原譜的基本要求;使用漢語演唱在實踐中存在大量的歌唱技術沖突,因為美聲體系本就是依照意大利語的發聲習慣及特點建立起來的……

或許大家都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的提出,推崇也好批駁也罷,本就沒有在一個視角、一個目標上去探討、去分析。誠然,在教學中,尤其是古典音樂聲樂教學的初期階段,以上所有的觀點都是正確且不容辯駁的。但中譯化的提出,實質上難道不是為了在群眾中更好地推廣普及歌劇藝術文化嗎?難道不是為了更好地培養大眾對歌劇的欣賞習慣嗎?難道不是為了提升高雅藝術在社會層面上更大的影響力嗎?
但是,我們面對的觀眾們,畢竟不是人人就讀于外語專業,也不是人人都畢業于音樂學院的歌劇表演專業。他們只是觀眾,他們只需要一個好故事,以及講好這個故事的過程體驗。
中譯版的歌劇排演,從來不是要替代原文版,而是與原文版并存并行,為演員與觀眾均提供更多的選擇機會。對廣大的觀眾聽眾而言,中譯版的歌劇排演,大大拓寬了群眾認識理解歌劇藝術的進入通道。對古典音樂的從業者來說,站在表演與教學的角度,中譯版也并非毫無意義。而對學習聲樂表演的學生們來說,中譯版的推動,一方面可以幫助學生更準確地理解劇情,理解角色,有利于歌劇教學中“表演”能力的建立與提高,改善大量存在于教學實踐中“聲富情貧”的現象。另外,以“美聲唱法”演唱漢語內容,本也正是目前聲樂演唱技術急需攻克的重難點。

因此,從技術角度出發,我們的專業從業者、廣大的師生必須意識到,西方歌劇中譯化演唱,非但不是降低了歌唱與表演難度,反而是在歌者演員充分掌握了原文演唱能力的基礎上,難度指數級地躍遷。很難想象,如果帕老爺的扮演者李鰲,不是擁有著十多年對這一角色的詮釋經驗,不是原意大利文幾乎可說是爛在了他的嘴皮子上,不是年少時期出于對相聲、話劇等藝術門類的熱愛練就出清晰的漢語咬字發音能力,如何克服重重困難,輕松地唱響那中文版的“讓我們悄悄地去花園”呢?
回賓館的路上,泉州大劇院在身后越來越遠,耳邊的一段歌聲卻始終揮之不去。中文版的“帕老爺”,聽懂的不只是語言的內容,更是藏于內心深處,靈魂貼近的那一份愉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