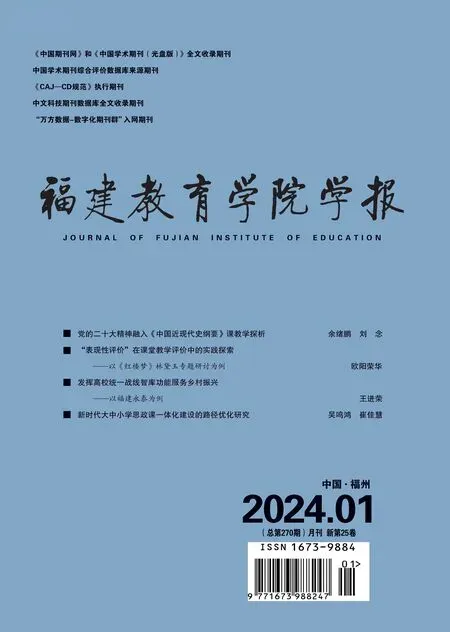杜威教育目的論在中國的早期傳播與影響
周佳斌
(華東師范大學 教育學部,上海 200062)
隨著1919 年杜威來華、杜威著作的譯介及胡適、蔣夢麟、陶行知等弟子對其思想的持續傳播,杜威思想深度參與了中國五四運動后的歷史進程,研究杜威具有深遠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從時人對于杜威觀點的引介和評價中,能夠理解杜威在中國產生的真實影響。教育目的是古今中外教育家思考的重要問題,直接影響著教育的性質、內容與途徑。在華期間,杜威對教育目的進行了重點闡釋。本文嘗試理清杜威教育目的論在中國的早期傳播與影響脈絡,分析其在中國的本土解讀及在中國教育實踐與改革中的重要影響。
一、杜威來華與杜威教育目的論的廣泛傳播
教育目的直接影響教育方法與路徑的選擇,對教育活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其確立受到經濟、社會、文化的多重影響。在中國傳統教育中,歷來對教育目的的闡發十分重視。傳統中國以倫理為本位,《大學》強調“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張載亦有名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而在科舉制下的古代中國,入仕被長期作為教育的主要目的,眾多士子皓首窮經,嚴重脫離社會實際。這種現象一直飽受詬病,歷代有識之士進行了諸多反對功利性教育目的的努力,但“學而優則仕”的教育目的始終未能得到質的改變。
近代以來,在內憂外患之下,教育暴露的問題越來越多。在反對袁世凱復辟的浪潮下,新文化運動對舊制度與舊文化展開全面批判,平民主義盛行,眾多知識分子紛紛開始勾勒新教育的藍圖。杜威來華正契合了近代中國急于進行教育變革的需要。在來華之前,杜威教育目的論便受到重點介紹。1919 年3 月,陶行知在《介紹杜威先生的教育學說》指出“杜威先生素來所主張的,是要拿平民主義做教育目的,實驗主義做教學方法。這次來……必定與我們教育的基本改革上有密切關系。”[1]杜威來華適逢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和五四運動的爆發,其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得到迅速傳播。杜威教育目的論在杜威教育思想中據有核心性地位,杜威在華期間充分考察了各地教育情況,發表演講達二百余次,其中多次涉及教育目的。
除通過演講在當地產生強烈反響外,杜威教育目的論還經《晨報》《民國日報》等各地書報競相刊載出版的講演記錄、活動報道、著作譯介等廣泛傳播。常道直在編譯《平民主義與教育》時專門指出“本篇第九章至第十一章論教育之目的,編者以其在教育理論上及實際上甚屬重要,爰就杜威博士原意參考所著書及其他名著數種,將原稿約擴充二分之一,但理論上絕無背馳或沖突之處。”[2]表明其時對教育目的的重視。
二、杜威教育目的論與中國重要教育問題的討論
杜威思想傳入中國后,其教育目的論逐漸成為教育學人進行理論探索和教育實踐的重要參照。在編譯、傳播、討論杜威教育目的論過程中,實際是對其有條件地、有選擇地吸收與運用。一方面反映中國教育界和知識界對杜威教育目的論的理解和認識,另一方面是受到中國本土關切的教育問題及社會問題的影響。在這其中,杜威教育目的論能夠有助于長期以來中國教育目的討論中的諸多二元問題,帶來了新的視角和取向,推動了近代教育目的觀的轉變。
(一)實用目的與道德目的的貼合
為何而教是教育中的根本問題。傳統教育理想以培養君子作為教育的重要目標,將道德教育置于至高地位,認為通過教育能夠使人達到完美境界,《荀子·勸學》言:“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圣人。”在實際中,傳統教育與科舉制度緊密聯系,科舉考試以選拔功能為主,希冀通過對儒家經典的閱讀和知識累積的考察,篩選具備道德文化的個人輔佐君王教化民眾,多表現為一種文人教育。而這種“從文到道”的傳導機制,并不能確保其必然有效,反而出現了在科考中高談闊論且只關心功名利祿的現象。中舉與落舉的巨大落差使士子們競相爭逐,紛尋捷徑,選拔理想與實踐相背離。時至明清,八股文寫作使這一問題更為突顯。教育方法、教育內容、教育制度逐漸受到禁錮。教育與功名深度結合,教育目的被嚴重曲解,大部分舉子并無法通過科舉成為理想中的“士”。
如何切實合理設置教育目標始終是懸而未決的重要問題。晚清以來,科舉制度下教育的片面化、功利化受到廣泛批評。杜威摒棄教育的外部目的,認為教育是非功利的,應從教育內部尋找目的,且目的“要根據于現存的或現時的活動”,同時須是符合實際的,能夠“轉變成為一定計劃”,是一種可預見的結果。[2]提出“教育即生長”,要讓活動全面自由地進行下去,使個人得到連續不斷的成長,批評教育脫離實際的現象,進一步關注教育本身,避免教育陷入功利主義的泥沼,促進近代課程、教材、教學方法等的變革。
傳統教育目的中對道德目的較為重視。道德時常被視為與物質利益對立,因此多推崇道德而貶低物質。近代以來,造就實用人才的需要尤為緊迫,以建設民主社會為最終目標的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受到歡迎。杜威的德育觀同樣在中國產生較大影響,江恒源在《倫理學概論》中對杜威德育觀表示認同:“美國學者杜威所說:‘道德就是學,就是生長’。這就是說人類精神生活,本是生長不絕的,道德也是生長不絕的。”[3]杜威認為道德即生長,強調“所謂社會的目的便是道德的目的。例如,單講社會的目的,其意就是要養成一種人品,能對社會有益,能做社會有用的一分子,這個目的自然就是道德的目的了。”[4]同時,提出教育即生活,而非生活的預備,強調學校與社會生活相聯系,對培養適應社會發展的實用人才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此,陶行知進一步構建了生活教育理論體系,主張打破生活與教育的壁壘,在實際生活中進行成長和體驗。陳鶴琴提出了“活教育”思想,指出“教育的目的在培養做人的態度,養成優良的習慣,發現內在的興趣,獲得求知的方法,訓練人生的基本技能。”[5]基于本國國情進行了具有豐富科學性和實踐性的新教育改革。
(二)個人目的與社會目的之間的互利
教育目的存在著眼于個體發展或國家社會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抑或是個體個性化與個體社會化之間的選擇。一方面,傳統教育存在如王鳳喈所論的“個人主義”:“教育的主旨在把個人變成社會上所規定的標準人……標準人的規定雖多是以社會為本位。而如何去做到那種標準人,則純以個人為本位”,古代教育家 “主張以個人修養為本,以改良社會為用”。[6]指出傳統教育關注的根本點在于培養個人的優秀品質,個人學習同時關乎國家發展,須努力修為自身乃至“行為世范”。李弘祺同樣認為古代中國教育是“為己之學”,教育的意義“來自于個人自身的進取”,同時注重“個人與社會的和諧融合”。[7]傳統教育多偏重于個人的修為,并從私德延伸至公德。
可以看到,傳統社會另一方面也始終強調社會責任。中國古代具有政教合一的傳統,《管子·牧民》提出“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認為使民眾具備社會公德乃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漢書·賈誼傳》有“國而忘家,公而忘私”之語,強調士人要以公共利益為先。《禮記·大學》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成長模式,認為承擔社會責任是士人的最終目標。但在實際中,封建統治者易將社會目的與個人目的進行對立,突出社會目的,對個人的個性發展不甚關注,致使二者之間時常發生沖突。
近代以來,挽救危機成為當務之急,教育中的社會目的被著重強調。1904 年,張之洞等人在《重訂學堂章程折》中提出的教育宗旨為:“無論何等學堂,均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8]1906年,清廷將“尚公、尚武、尚實、忠君、尊孔”定為教育宗旨,申明應承擔的外部責任,但忽視和束縛了個人的發展需要。“中華民國”成立后,臨時政府教育總長蔡元培于1912 年9 月公布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9]教育宗旨重新兼及個人與社會。
杜威同樣注意到這一對重要關系:“社會生活的知識使我們可以定教育的目的,這是遠的一端。那近的一端就是兒童。”[4]其教育目的論首先是基于平民主義的,強調兒童本位的教育:“兒童天賦的本能、才量等乃是教育之基本”,教育者要“就兒童固有的經驗加以相當的指導。”[2]圍繞兒童的個性與興趣展開教育。杜威不認同犧牲個人以達成社會目的的二元論觀點,認為社會效率的獲得應積極調動個人的天賦能力:“平民主義教育之目的,在發展社會上個人之才力與精神為最大之宗旨,非若貴族之限制人民。”[4]在此基礎上,杜威同樣重視教育與社會的聯系,強調“教育之目的,即在加增這種適應或適合之能力,庶幾各個人能以維持生活,并能利用四圍的物件,使成為更有效用的個人。”[2]王鳳喈也認同這一觀點:“教育的目的不僅是造就個人成為思想家、科學家、文學家,并須使個人成為社會的個人……這種主義,美國杜威一派學者提倡最力。”[6]強調培養參與共同生活的能力,使個人能力在社會中充分發揮作用,實現個人價值與社會發展需要的有效結合。通過達到個人目的與社會目的的平衡性與一致性,杜威認為能夠培養出“配做社會的良好分子的公民”,使個人“不但被動地吸收,還須每人同時做一個發射的中心,使他所承受的及發射的都貢獻到別的公民的心里去。”[4]社會由此形成真正的聯合體。
對于杜威教育目的論,常道直強調其中需將社會目的擴展至世界范圍的觀點:“目前世界各國的教育還是以國家為單位,未能為全人類的大社會統籌合算。”[10]這是在殘酷的一戰后,其對“聯合生活”進行的一種再思考。此外,常道直也強調發展“平民主義的教育”:“須要同時發展個人的創發能力和適應能力:個人的能力發展到無微不至;服務社會的能力也發展到最高限度,乃是社會的教育之最后的目的。”[10]蔣夢麟在回國后與黃炎培、陶行知等人創辦《新教育》月刊,將辦刊目標定為“養成健全之個人,創造進化的社會”,《新教育》“在教學法上主張自發自動,強調兒童的需要,擁護杜威教授在他的《民主與教育》中所提出的主張”。[11]胡適在留美期間便認為 “教育之宗旨在發展人身所固有之材性。”[12]回國后,他繼續強調教育要注意培養個人的創造性和自主性,訓練參與社會生活的能力,提倡培養具有獨立自由人格的公民。在杜威的影響下,民國教育界逐漸倡導以兒童為中心的教育觀,在課程、教材教法上對兒童的發展予以了更多關注,出現諸多新式中小學和教育實驗,“造就公民”成為一種教育共識,推動了教育民主化和科學化的進程。
(三)知與行的協調
教育目的對教育行動具有導向作用。知與行的關系同樣是古今一直討論的問題。程頤認為:“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致知……怎生得行? 勉強行者,安能持久?”,強調思想的預知性。朱熹也認為知先行后,同時知與行不能分開:“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王陽明綜合前人觀點,提出知行合一的觀點。在普遍認識中,往往認為“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孫中山鑒于因辛亥革命后多次失敗而出現的畏難情緒,提出“知難行易”論。杜威來華后對孫中山的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適杜威博士至滬,予特以此質證之。博士曰:“吾歐美之人,只知‘ 知之為難’ 耳,未聞‘行之為難’ 也。”[13]孫中山自此更加堅定其“知難行易”的觀點。
杜威認為目的就是一種預見終點的能力,強調目的應為動態的,要基于實踐活動不斷反思調整,使實踐活動開展得更為靈活且容易控制,知與行因此得以相互協調、相互促進。周谷城指出,杜威“講思想講得最清楚。他說思想就是一副工具,是指揮行動的,是解決困難的,是引導行動向前的”,同時也認為其對于“思想之本身究為何物”“思想解放行動及指導行動之方法”“思想與自我及生活之區別”等并未說明,因此進一步反思延伸,指出“思想乃是生活之一段”,要努力達到行與思的和諧統一,形成科學人生觀,成為其“生活系統”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14]陶行知對知行關系進行了深刻探索,倡導“教學做合一”“知情意行合一”等教育方法,提倡實驗精神,開展了基于本土實際的教育教學改革。
三、杜威教育目的論與中國教育實踐
杜威教育目的論與傳統教育理想有一定的契合之處,同時帶來新的視角和取向,在諸多兩難問題中取得了某種平衡。在杜威教育目的論的影響下,民國學人對教育本身予以更多的關注和本土探索,引起民國學人對教育目的的定位、取向、性質的討論和思考,同時推動了教育政策的改革。
1919 年10 月,杜威出席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第五次會議并進行演講,重點論述了其“教育之外無目的”的觀點。在杜威的影響下,會議通過《呈教育部請廢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義案》,認為“蓋無論如何宗旨、如何主義,終難免為教育之鑄型”,主張廢止教育宗旨,以“養成健全人格,發展共和精神”為教育本義。[15]教育部雖未采用這一提案,但在1922年公布的新學制中取消使用“宗旨”一詞,規定七條學制標準,包括:適應社會進化之需要;發揮平民教育精神;謀個性之發展;注意國民經濟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縮余地。學制標準充分反映了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及教育目的論的影響。
隨著杜威教育目的論影響的擴大,也有學人對其提出異議。如有論者指出其存在兩處錯誤,一為“分析目的性質之錯誤”,認為其將生長作為目的,實際是將教育意義與教育目的混為一談;二為“假定目的標準之錯誤”,杜威認為目的“可改變之彈性”實際上是“囿與眼前之目標,而昧于遠大之目的者也”,認為教育目的實由這二者組成,并強調應將“平民主義的理想”作為遠大目標。[16]
除學術討論外,杜威教育目的論在中國的境遇也因時勢發生變化。五卅運動爆發后,西方文化受到大范圍質疑,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傳播熱潮開始回落,國家主義教育思潮更據上風。陳啟天認為“今人所謂平民主義實在就是個人主義,只知發展個性而忘卻培養群性”,強調“一個國家或是一種社會要他能夠長久維持必須各個分子均有共同信仰共同了解和共同習慣才行”,平民主義“在中國行起來實在容易偏向于個人方面。”[17]認為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國無法得到真正實現。陳啟天強調教育中國家利益的重要性,一定程度反映了其時教育界的趨向。1926 年,中華教育改進社也在年會上通過決議,認為教育宗旨應為“養成以國家為前提之愛國國民”,將“注重本國之文化,以啟迪發揮國性之獨立思想”視為教育重點。[18]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大學院于1928 年召開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通過以“三民主義的教育”作為新的教育宗旨,教育失去其獨立性,成為灌輸黨義的工具。時至抗戰時期,“教育救國”成為社會主流思想,拯救民族危機成為戰時教育的首要目標。“教育之外無目的”在教育政策上的影響逐漸旁落。
四、結語
杜威教育目的論回應了中國本土長期關切的教育問題,適應了五四運動后國內教育改革與社會變革的需要,推動了民國學人對教育目的的重新審視和探索,加深對其中諸多二元問題的認識。同時,民國學人對杜威教育目的論進行了吸收和創造性轉化,促進中國教育目的觀的近代轉型,進而開展新教育實踐和教育制度的改革。作為杜威教育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杜威教育目的論的廣泛傳播也推動了實用主義、平民主義教育思潮的形成及發展。在這一過程中,能夠看到民國教育界和知識界為建設新社會、塑造新國民作出的多種嘗試和努力。
在引薦與運用杜威教育思想的同時,也伴隨著眾多解讀方式與爭議,一方面是由于譯法的不同,另一方面也是因學人基于自身立場,會對其持有不同態度,其中以“教育無目的論”最為典型。在民國具體教育實踐中,教育宗旨實際不斷因時勢發生變化,外部目的依然存在,杜威教育目的論在中國也相應擁有不同境遇。可以看到,教育仍需在其獨立性和工具性之間尋找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