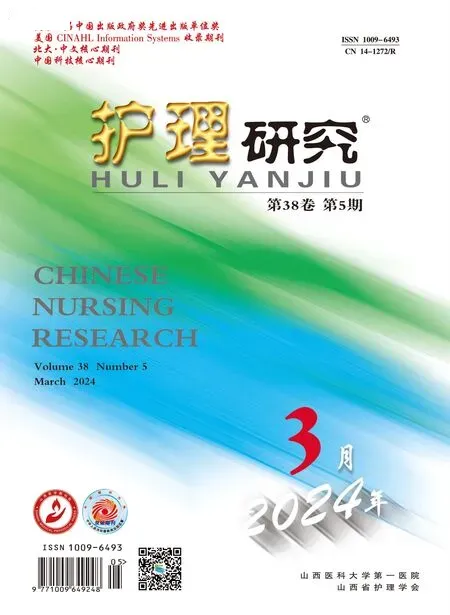預立醫療照護計劃準備度研究進展
楊雪梅,梁 湘,陳思芮,陳海林,吳莉莉,陳 英*
1.廣西醫科大學附屬腫瘤醫院,廣西 530021;2.廣西醫科大學
臨終期的過度治療并不能改變病人死亡結局,并且會給家庭造成更大經濟壓力,同時給醫療系統帶來沉重負擔[1]。預立醫療照護計劃(advance care planning,ACP)是指病人在清醒狀態下,根據個人偏好、價值觀表明自己將來在臨終狀態時想要接受的治療及護理意愿及溝通病人偏好的過程[2]。ACP 準備度是指病人在治療決策中對ACP 的認可和接受的行為傾向,是預測病人未來是否參與ACP 的重要因素。相關研究顯示,ACP 能提升臨終期病人生活質量、減少醫療資源浪費、減輕經濟負擔,而ACP 準備度是病人是否參與ACP 的預測因素,因此研究ACP 準備度有重要的意義[3]。現對ACP 準備度評估工具、準備度現狀、影響因素進行綜述,以期為提高國內病人ACP 準備度及未來ACP 推廣提供參考。
1 ACP 準備度評估工具
1.1 一般人群ACP 準備度評估工具
1.1.1 ACP 準備度量表(Readiness of Advance Care Planning,RACP)
RACP 由日本學者Sakai 等[4]于2022 年以文獻綜述和專家小組討論形式,基于跨理論模型編制的符合亞洲文化特征的RACP。該量表包含認識到說和寫的重要性、打算說、打算寫、行為準備、練習說和寫5 個維度,共28 個條目,采用Likert 6 級評分法進行計分,“非常不同意”計1 分,“非常同意”計6 分,得分越高表明ACP 準備度越好。該量表Cronbach's α 系數為0.95。該量表可以評估不同年齡人群在不同的健康階段對ACP 的準備度,但量表條目數較多且文字較長,不適合有嚴重疾病的病人填寫,后續可編制一個簡短的量表。且該量表僅經橫斷面研究驗證,未來需要進一步開展多中心、大樣本研究來評估量表的敏感性。
1.1.2 ACP 的認知和態度問卷
Lai 等[5]通過編制ACP 的認知和態度問卷,評估馬來西亞老年人對ACP 的意識和態度。問卷包含“對ACP 的 感 受”“參 與ACP 的 理 由”“不 參 與ACP 的 理由:命運與宗教”“不參與ACP 的理由:逃避對死亡的思考”4 個維度。量表各維度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637~0.915。該量表填寫難度小,即使只有小學水平的閱讀能力也可完成填寫。
1.1.3 ACP 行為變化量表
該量表由Sudore 等[6]編制,用于評估舊金山老人參與ACP 的行為改變過程,A 量表從行為改變理論中已知的影響行為因素的“過程測量”和“行動測量”組成,“過程測量”由知識、意向、自我效能和準備4 個維度組成,使用Likert 5 分評分法;“行動測量”包括醫療決策代理人、價值觀和生活質量、代理決策的靈活性以及知情決策相關的多種行為。該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總體Cronbach's α 系數為0.94,知識、意向、自我效能、準備度分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分別為0.84,0.86,0.83,0.92。該量表具有較好的信效度,但條目較多,填寫時間較長,可能會影響其實用性。
1.2 患病人群ACP 準備度評估工具
1.2.1 慢性病病人ACP 準備度問卷
該問卷由王心茹[7]編制,用來評價慢性病病人ACP 準備度水平。該問卷共包含態度、信念、動機3 個維度、22 個條目,采用Likert 5 級評分法計分,態度維度為反向計分,“非常不同意”計1 分,“非常同意”計5分。根據得分將ACP 準備度及各維度分別劃分為ACP 準備度、對ACP 的態度、參與ACP 的信心和參與的動機4個水平,問卷總分越高,代表ACP 準備度越好。問 卷 總 體Cronbach's α 系 數 為0.923,3 個 維 度 的Cronbach's α 系數分別為0.900,0.880,0.835。該問卷基于我國文化背景編制,具有較好的文化適用性,已廣泛應用于我國慢性病病人ACP 準備度的研究[8-9]。
1.2.2 ACP 準備度量表
該量表由Brown 等[10]編制,用于評估婦科惡性腫瘤病人參與ACP 討論的意愿與準備情況。量表包含愿意討論臨終話題與接受ACP 2 個維度和8 個條目,其中參與ACP 的意愿(5 個條目)、討論臨終治療護理措施的接受度(3 個條目),采用Likert 7 級評分法,“非常不同意”計1 分,“非常同意”計7 分,得分越高表示病人更愿意討論ACP 及準備度越好,其信效度良好,Cronbach's α 系數為0.81。但是,此量表并未得到廣泛應用,且該量表初期僅在美國白人婦科惡性腫瘤病人中進行了應用,導致其受試人群有限,使得該量表的推廣存在局限性。
1.2.3 ACP 準備度測評工具(Advance Care Planning Readiness Instrument,ACPRI)
由美國德克薩斯大學Calvin 等[11]基于“個人保護理論”編制,主要用于評估腎衰竭病人ACP 的準備度。該量表貼近臨床實際,條目偏向于臨終醫療情境,對ACP 準備度的測量主要側重于個人對家庭、生活、醫療環境各方面的權衡。量表包括30 個條目,采用Likert 7級評分法,“非常不同意”計1 分,“非常同意”計7 分,問卷總得分越低表示個人參與ACP 討論的準備越好,而得分越高則表明個人尚未準備好。量表總Cronbach's α系數為0.88。該量表主要通過個人保護理論從病人對臨終偏好的角度來判定其參與ACP 的意愿及準備程度,護理團隊可以使用該量表來確定透析病人對ACP的準備情況。但目前此量表僅被研發團隊小樣本使用,還需進行大樣本研究,以測試其在預測ACP 準備情況方面的敏感性。
2 ACP 準備度現狀
2.1 國外ACP 準備度現狀
國外ACP 發展起步早,較早頒布相關法律法規。在McIlfatrick 等[12]對北愛爾蘭1 201 名成年人的研究中,雖然78.7% 參與者承認ACP 帶來的好處,但是63.3%受訪者認為自己健康狀況良好并不考慮ACP或者不打算了解更多,提示ACP 準備度不高。Fleuren等[13]對荷蘭1 585 名年齡57 歲及以上荷蘭人的研究顯示,約78%的研究對象參與ACP 但并沒有與他們的醫生討論,也并沒有將這些話題記錄下來,意味著他們沒有準備好與醫生討論這些話題。美國一項對等待肝移植的終末期肝病病人的研究結果顯示,僅有9%的病人完成了ACP,但大部分病人認為已準備好指定決策代理人,對參與ACP 的準備和信心水平較高[14]。而美國另一項針對年輕人的研究結果顯示,雖然年輕人對ACP 有積極看法,約一半的人也與家人討論了臨終相關話題,但大多數年輕人仍沒有簽訂生前預囑或簽署醫療委托書等預立醫療措施[15]。國外人群對ACP態度整體較積極且ACP 接受度較高,ACP 的準備度整體水平較高,部分國家或地區已從意識層面落實到行為層面。
2.2 國內ACP 準備度現狀
香港、臺灣地區ACP 發展較早,在過去的20 年里已對ACP 進行了深入研究,且得到政府的支持。臺灣的一項質性研究顯示,老年晚期癌癥病人缺乏基本ACP 意識,ACP 準備度低,處于預思考階段,可能與被研究人群處偏遠山區、獲取信息有限有關[16]。在一項對238 名香港居民和87 名臺灣居民的調查研究中,46%的臺灣居民參與者表示他們會考慮在未來完成預先指示,而香港居民參與者的比例為20%,臺灣居民參與者ACP 準備度較香港居民參與者高[17]。這可能與2 個地區之間預立醫療指示和臨終護理的法律地位、政策和保險范圍的差異影響他們的預立醫療偏好有關。臺灣地區對ACP 接受度及準備度較高,而香港地區因公眾尚不能廣泛接受醫療預立指示而以非立法形式開展ACP,表明香港公眾對ACP 接受程度較低且ACP 準備度不高。
我國大陸(內地)地區公眾缺乏ACP 意識且多數人未聽說過ACP,部分病人雖對ACP 態度積極,甚少與家人及醫務人員討論ACP 相關話題,ACP 準備度水平在不同人群中存在差異。張娟[8]對355 例癌癥晚期病人的調查顯示,癌癥晚期病人準備度水平處于中等偏上水平,對ACP 持積極態度,參與ACP 的信念及動機較強,對ACP 較為認可。張麗等[18]對150 例缺血性腦卒中病人的調查顯示,缺血性腦卒中病人ACP 得分處于中等偏下水平,提示缺血性腦卒中病人并未做好實施ACP 的準備。屈小伶等[19]對終末期肺癌病人的質性研究顯示,病人不僅缺乏ACP 相關知識,還將ACP 概念與立遺囑、放棄治療混淆。丁多姿等[20]研究發現,醫學生對概念類條目了解較多,而對ACP 的實施了解甚少,說明醫學生對ACP 在臨床中的實施開展知識儲備不足。我國非醫務人員ACP 準備度水平較低,而醫務人員對ACP 準備度稍高,這可能與醫務人員目睹病人病痛、使其對ACP 較易于接受從而準備度較高有關。
3 ACP 準備度的影響因素
3.1 文化因素
文化與一個人價值觀、生死觀的形成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它影響了人們對死亡的理解以及臨終的態度,包含了生死觀、孝道文化、醫生權威、家庭觀念等。張娟[8]研究顯示,我國傳統文化信仰接受程度越高的晚期癌癥病人ACP 準備度越低。傳統孝道觀念根深蒂固,在生命末期,即使積極治療已經徒勞,但是不少病人親屬仍會選擇延長生命的醫療措施,不然會被認為“不孝”而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何虹燕[9]對194 例慢性心力衰竭病人的研究顯示,受我國傳統孝道文化影響,即使病人向親屬表明自己的治療護理偏好,病人仍擔心在終末期親屬未按照其意愿給予符合其意愿的治療護理措施。我國有醫生權威觀念,國人對挑戰權威、從群體中冒尖持負面看法,認為這樣是無禮的行為[7]。有這樣觀念的人可能在文化上可能更容易服從于社會權威。在家庭觀念的影響下,在重大決策中人們傾向于家庭主導及照顧家庭成員,人們發起ACP 的主要原因大多是為了讓家人知道他們的愿望、減輕家庭決策負擔[15]。談論死亡是禁忌的話題,甚至認為討論死亡是不吉利的,一項對美籍華裔的研究顯示,研究對象認為談論死亡會帶來厄運甚至加速死亡[21]。因此,我國在推廣ACP 的過程中,應充分考慮文化因素的影響,構建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ACP 推廣模式。
3.2 社會人口學因素
社會人口學因素包括年齡、教育水平、宗教信仰等。張娟[8]研究結果顯示,在晚期癌癥病人中,年齡越大的病人ACP 準備度水平得分越低。但何虹燕[9]研究顯示,年齡越大的病人,其對ACP 準備越充分,相反,年齡越小的病人,對ACP 準備越差。Gallagher 等[22]研究顯示,病人雖然希望表達自己的臨終偏好,但因受教育水平低的影響可能缺乏相關的知識來討論臨終時的治療及護理偏好。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晚期癌癥病人ACP 準備度越高[8]。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不太可能討論自己的臨終愿望[22]。尹曉彤等[23]的研究結果與此相似,有宗教信仰的中青年癌癥病人ACP 接受度高于無宗教信仰者。這也與吳麗娜等[24]的研究結果相同,這可能與參加宗教組織后所接受的理念傳遞有關,豁達的生死觀讓他們更容易面對死亡。但董丹妹等[25]的研究結果與此相反,該研究顯示,有宗教信仰者均不能接受ACP,這可能與所信奉宗教的信仰與理念的不同,從而使宗教信奉者對死亡及臨終有不同的理解。未來可根據不同年齡病人、不同教育程度的病人制定相應的ACP 準備度干預措施,同時應根據不同宗教信仰制定個性化干預策略,以期提高病人ACP 準備度。
3.3 疾病因素
疾病因素對病人ACP 準備度有重要的影響,其中包括病情知曉程度、病程時長、病種、診斷個數等。對自身疾病了解程度越高的病人ACP 準備度水平越高,確診疾病后病程越長的晚期癌癥病人,其ACP 準備度、態度、信念、動機水平越高[8]。王心茹[7]在慢性病病人的研究中同樣發現病程持續時間越長的病人,其ACP 準備度越高。病程較長的病人相比病程短的病人經歷了更多的疾病反復和治療,有更多的機會考慮疾病的發展及預后,因而參與規劃未來危重期醫療措施的準備度相對更高。在各類疾病中,癌癥病人更傾向于制定ACP,癌癥病人往往會與家庭成員及醫護人員就自身病情及未來醫療照護愿望進行溝通,以確保失去決策能力時的醫療照護方案與自身期望相一致,其中癌癥Ⅳ期的病人比癌癥Ⅰ期的病人及預后越差的病人更容易接受ACP[26-28]。有研究發現,疾病診斷多的病人更愿意接受和討論ACP,表明疾病診斷個數影響病人對ACP 的理解[7]。
3.4 認知因素
Chan 等[29]研究顯示,接受過ACP 相關培訓的醫療工作者對開展ACP 的信心和意愿會更高,同時ACP準備度水平更高。美國一項關于大學生的ACP 研究[15]得到了與此相似的結果,該研究指出大學生對ACP 相關知識了解越多,對ACP 積極評價越高。Lum等[30]在老年病人的研究中,圍繞以人的價值觀為中心的ACP 工作坊進行討論增加了病人ACP 相關文件的記錄以及一些行動步驟的準備。信息對決策很重要,在對我國臺灣偏遠地區老年癌癥晚期病人的研究中[16],盡管病人樂于討論有關臨終話題,但由于缺乏相關知識及醫療資源,他們沒有機會參與ACP,這對該人群的ACP 準備度產生了負面影響。因此,應加強醫務人員ACP 培訓及從社會層面對ACP 進行宣傳推廣,提高公眾ACP 認知,從而提高其ACP 準備度。
3.5 心理社會因素
心理社會因素對病人ACP 準備度有重要影響,其中包括家庭情感支持、應對方式、心理疾病、社交孤立等。Miyashita 等[31]研究指出,來自家庭情感支持可以促進病人與家庭成員的討論,為ACP 討論提供機會,這種討論成為一個催化劑,從而引發ACP 的討論。但大多數人發現很難向親屬或者醫務人員提出臨終護理及治療偏好的討論,因為他們擔心談論自己死亡相關話題會讓家屬感到不安或痛苦[12]。不同的應對方式對ACP 準備度有不同影響,趨向于以回避、自我安慰等負向的態度處理外界應激事件的病人,其ACP 準備度越低[7]。Kelly 等[26]的研究結果表明,患有抑郁癥的病人更容易接受ACP,從而簽署預立醫療相關文件。McMahan 等[32]對986 名老年人的研究結果與此相似,存在抑郁及焦慮情緒的老年人可能不重視延長生命,對ACP 的參與及準備程度較高。相似的是,社交少或社交網絡有限的老年人不太可能與親朋好友討論ACP,其更少參與ACP 過程,不善社交及獲取相關ACP 信息較少,因此較難發起ACP 討論[33]。未來在構建ACP 準備度干預方案時應重視家庭的影響,提高家庭的支持度,根據不同人群制定相應的干預方案。
3.6 其他因素
一項對長沙社區204 名老年人的調查顯示,有近期住院經歷的老年人對ACP 行為更有信心和準備[34]。而缺乏親屬死亡經歷的人談論死亡相關話題會引起不適,不太可能發起ACP 談話[22]。Fleuren 等[13]研究顯示,主觀剩余壽命短的病人參與ACP 的概率更高,他們認為生命即將終結,由此更傾向于啟動ACP。因此,應根據不同住院經歷、是否有死亡經歷、不同主觀剩余壽命構建相應干預模式,提高ACP 準備度。
4 干預策略
隨著我國《“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及《安寧療護中心基本標準(試行)》等一系列文件的發布,在國內安寧療得到了蓬勃發展的同時,ACP 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在ACP 探索中應注意ACP 準備度是病人是否參與ACP 的重要因素。提高ACP 準備度需要進一步借鑒國外ACP 實踐經驗,結合我國文化背景,制定有效干預措施,提高公眾ACP 準備度。開展符合我國國情的ACP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筆者認為以下幾個方面應引起關注。
4.1 提高ACP 認知
我國ACP 發展較晚,ACP 研究和發展尚處于探索及概念推廣階段。作為ACP 主要發起者及決策主導者,醫護人員在ACP 的實施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醫務人員對ACP 的認知影響他們是否接受并積極開展ACP 工作。提高醫務人員對ACP 的認知水平及ACP 知識、技能水平可以借鑒安寧療護推廣模式,如設立ACP 工作坊、研討會、專科護士培訓等。針對病人可研制適合本土文化背景的ACP 視頻教育工具,以需求為導向的同時尊重病人家屬意愿制定個性化ACP 視頻教育工具。面向社會的宣傳可設立ACP 科普專欄,通過宣傳小冊子對ACP 概念進行宣傳推廣;同時可以利用網絡的便利,開通微博、微信、抖音等ACP 公眾號推送精彩的ACP 科普文章、短視頻傳播ACP 內容使ACP 更深入人心。建立相關ACP 網站,如羅點點創辦的倡導“尊嚴死”的公益網站“選擇與尊嚴”,推出生前預囑文本《我的五個愿望》,有效地幫助公眾了解并推進ACP 的開展。應大力開展針對性及有效的ACP 教育,采取多種干預方式和多途徑宣傳方式,以提高公眾的ACP 準備度。
4.2 開展符合本土文化的死亡教育
應加強公眾死亡教育,可參照我國臺灣地區開展死亡教育的生命教育體系的形式,也可參考我國香港地區將死亡及生命相關課程納入通識教育的方式,同時結合我國大陸(內地)地區不同特點制定相關生命教育課程并納入教育體系。醫護人員作為ACP 對話發起者,應培訓醫護ACP 溝通技巧,以期能在ACP 對話中采取合適的溝通技巧,激發病人對嚴重疾病討論以及引導病人表達其臨終護理及治療偏好,從而了解病人的臨終關懷目標。同時,衛生管理部門及相關醫療機構可通過不同形式進行生命教育宣傳,如短視頻、講座、小冊子、公益廣告等,給公眾樹立正確的生死觀,使其能正確看待死亡,緩解對死亡的焦慮和恐懼。
4.3 推廣以家庭為中心的ACP 溝通決策
我國傳統文化中個人利益服從家庭利益,病人自主意識薄弱,這種極強的家庭觀念影響著病人在重大決策時優先考慮家庭,往往不愿自己做主而將決定權交予家屬。因此,在ACP 溝通過程中家屬的參與是ACP 的關鍵,應鼓勵病人家屬參與并強調病人自主權,在文化、價值觀背景下平衡病人的臨終治療護理需求,更好地了解病人的臨終治療偏好及心理需求。
4.4 制定ACP 相關政策及法律法規
2022 年,深圳第七屆人大通過了《深圳經濟特區醫療條例》在臨終期應當尊重病人生前預囑,首次將“尊嚴死”納入法律體系,這一規定迅速登上熱搜,引起熱烈討論,不少網友認為該規定應在全國推廣,說明我國已初步具備ACP 立法的法律環境。但缺乏政策支持阻礙了ACP 本土化推廣,要有效地開展ACP 還需國家制定相關法律法規使ACP 有法可依。同時,政府及醫保應提供相應的資助,制定ACP 收費標準并納入醫保支付范疇,減輕病人ACP 支付壓力,使其更容易接納ACP。醫院是ACP 對話發起及實施的重要場所,醫院管理者應給從事ACP 相關工作的醫護人員相應的鼓勵和支持。
5 小結
我國病人對ACP 認知缺乏,ACP 準備度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研究內容多為現狀調查及影響因素研究,相關干預研究較少。提高病人ACP 準備度對ACP 發展有重要意義,應探索個性化ACP 準備度干預模式,提高病人對ACP 的認知及準備度,改善終末期病人生存質量。針對不同人群ACP 準備度的權威評估工具較少,可根據我國文化背景制定符合我國國情的不同人群的準備度評估工具。總結國外ACP 實踐的經驗構建符合本土文化背景的ACP 推廣模式,促進ACP 在我國的發展還需要國家層面制定相關法律,推廣符合我國文化特色的ACP 家庭決策模式,從家庭角度出發提高病人ACP 準備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