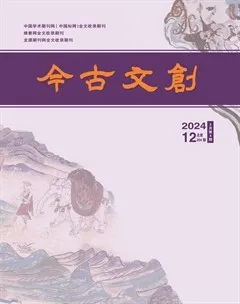論動畫《鵝鵝鵝》對傳統“吞吐” 類故事的繼承與創新
吳寅妍
【摘要】動畫短片《鵝鵝鵝》改編自魏晉志怪故事《陽羨書生》,在繼承原作“吞吐”人物情節的同時亦做出時代創新。其創新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對主角在劇情中身份的改編;二、對原文中“情欲”的思考作進一步深化擴充。本文將《鵝鵝鵝》與《陽羨書生》以及“吞吐”類故事的源頭《梵志吐壺》加以對照,嘗試探討時代背景更迭下同類作品的不同文化內核,對當下傳統文化如何實現有效的現代化傳播母題有著現實意義。
【關鍵詞】《梵志吐壺》;《陽羨書生》;文化創新;動畫改編
【中圖分類號】J954?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12-008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12.025
《中國奇譚》是由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與嗶哩嗶哩視頻網站聯合出品的原創網絡動畫短篇合集,該片由八個獨立的動畫短篇組成,于2023年1月1日起在嗶哩嗶哩播出。全篇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意在展現中式美學的獨特魅力,其中的第二集動畫短篇《鵝鵝鵝》改編自南朝梁吳均所撰寫的《續齊諧記》中的《陽羨書生》,動畫不僅沿襲六朝志怪小說中詭異玄幻的氛圍,還對故事加以改編、擴充,使故事在保留原作內核的同時更貼近當代審美。本文將對《陽羨書生》和《鵝鵝鵝》以及它們的淵源《梵志吐壺》作深層對照,以此剖析作品背后魏晉志怪小說中獨有的哲學內涵。
一、主角在劇中身份的改變
(一)人稱的改變
首先是作品中敘述人稱的改變。《陽羨書生》以第三人稱的視角,敘述了陽羨的許彥在綏安山遇到一書生,書生以腿疼為由進入他的鵝籠,兩人在樹下擺酒席設宴相談,許彥眼看書生口中吐出銅奩子、佳肴、女子,女子又從口中吐出一男子,男子隨即又從口中吐出另一女子,最終書生蘇醒,幾人又相繼把吐出的人與物吞回肚子的奇遇。原文采用第三人稱,以許彥的視角向讀者展現他的所聞所見。通篇下來,許彥在故事中更多是被動地配合其他人的行動(例如在被吐出的男女相繼請出自己的心上人,請求許彥保密時簡單地說出“善”字),作為事件的見證者,他更多是作為旁觀者,亦故事的轉述者,帶著讀者平靜地注視著事情的發生,從始至終并未主動參與其中,與其他人物有過親近互動。
不同于原作,《鵝鵝鵝》一改原先的第三人稱視角,將故事的敘事改為少見的第二人稱,將劇中對主角的稱呼從“許彥”變成了第二人稱的“你”。這種敘述人稱并不常見,但也在一些傳統說書中出現過,例如在《水滸傳》中智取生辰綱一章末尾,作者便跳出傳統敘事直接與讀者對話:“我且問你:這七人端的是誰?不是別人,原來正是晁蓋、吳用、公孫勝、劉唐、三阮這七個……”這里雖然采用第二人稱,但也只是敘事人所假定的一種虛構存在,為的是引出下文,將其敘述的事件加以補全,而并非真正存在“你”這一人物。與之類似的還有嚴歌苓的《扶桑》,也是在第三人稱敘事的基礎上用第二人稱對故事背景、人物心理加以補充說明。
真正將第二人稱敘事貫徹使用的經典之作,是米歇爾·布托爾的《變》與《度》。在《變》的開頭,他寫道:“你把左腳踩在門檻的銅凹槽上,用右肩頂開滑動門,試圖再推開一些,但無濟于事。” ①這一人稱上的改變讓觀眾不再以觀看者的身份旁觀他人的故事,而是作為故事的親歷者置身其中,進一步拉近了觀眾與故事的距離,張閎在《論第二人稱敘事》一文中提出:“第二人稱敘事乃是一種召喚,一次吁請,迎接讀者進入事件的現場,成為與人物同在的角色,甚至,他就是作品中的人物本身。” ②回到《鵝鵝鵝》,不同于小說的文字敘述,動畫作為一種視覺媒介更注重畫面上的信息傳達。為此,導演在篇中采用類似默劇形式,全篇無一句臺詞,只以“這里是鵝山,是你失蹤的地方。”“他要你背他去那山頂。”等文字旁白簡要說明故事的發生背景以及角色的對話內容,襯之以背景音烘托氣氛。默劇重畫面、不喧鬧的特性,搭配上旁白以“你”為開頭直接與觀眾對話的特性,使觀眾可以迅速代入角色,置身于故事現場,全身心專注于故事發展。
(二)與其他角色的互動
此外,不同于原文中許彥作為“旁觀者”被動觀賞事件的描述,《鵝鵝鵝》細化并擴充了原作內容,將故事發展的主動權交在了主角“你”的手中,通過讓主角和事件的其他角色產生互動的形式,使主角從轉述者搖身一變成為事件的主動參與者。動畫中將書生及幾個被吐出的男女角色外觀改為更卡通化的狐貍、兔子、野豬、鵝妖怪造型,即貼合原作志怪小說詭譎奇幻的氛圍,又便于加深觀眾對角色的印象。動畫名為《鵝鵝鵝》,除去鵝籠中被書生吞入的兩只鵝,那第三只鵝便是最后由野豬妖吐出的女鵝妖。在前面三妖陸續睡去后,動畫新增了主角“你”與女鵝妖的對話互動,明示兩人已然互生情愫。鵝妖想讓“你”帶她走出鵝山,“你”望著鵝妖朱紅的唇和漆黑的口,想起先前自己失去的兩只鵝,還有接連被吐出的妖怪,生怕眼前這鵝妖口中又會吐出新的情人,“鵝”又生“鵝”。就在“你”猶豫當口,狐貍書生蘇醒,幾個妖怪陸續把自己的情人吞入口中,“你”失去了第三只鵝,永遠迷失在了鵝山當中。這種讓主角與其他角色互動的方式,也讓角色從先前冷漠的轉述者變得有血有肉,在立體形象的塑造上功不可沒。作為觀眾視角的切入點,比起動輒呼風喚雨的妖魔鬼怪,“你”作為一個處事尚淺的年輕貨郎,想要抓住眼前機遇卻又患得患失,最終滿盤皆輸的經歷顯然更能給予觀眾共鳴,極大程度上加強了觀眾的代入感,使觀眾為“你”這樣的小人物的失敗經歷感到惋惜,并思考故事背后的內涵哲理。
二、從“壺”到“籠” ——對欲望的探討
要探討《鵝鵝鵝》的內涵哲理,需要從它的源頭開始講起。《鵝鵝鵝》改編自《陽羨書生》,而《陽羨書生》的源頭則是域外與佛教密切相關的譬喻故事《梵志吐壺》。唐代段成式在《酉陽雜俎》續集卷四《販誤》引錄《陽羨書生》時,曾在末尾提及該文:
釋氏《譬喻經》云:“昔梵志作術,吐出一壺,中有女與屏處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復作術,吐出一壺,中有男子,復與共臥。梵志覺,次第互吞之,拄杖而去。” ③
這其中人物吞吐的橋段顯然與《陽羨書生》中一致,不同于書生的直接吞吐,《梵志吐壺》中多了“壺”這一召喚媒介。為何要專門提及“壺”呢?在印度佛教中,壺常常與祭祀、宗教相聯系。丁敏提出,“壺”在佛教典故中,一為一種被清凈的梵行禁止的“投壺”的競技游戲;二則為吐痰之唾壺,兩者都有嬉戲放逸的象征,意指秘密情欲的污垢。④《梵志吐壺》以“壺”為喻,顯然帶有一定佛教步道目的。《梵志吐壺》借壺中女子與他人偷情之舉,批判不潔男女為滿足私欲暗相茍且的齷齪之行,有較強告誡之意,是承載印度佛教義理的譬喻故事。而在這類“吞吐”故事的本土化發展中,《陽羨書生》保留了原先人物吞吐和男女私情的橋段,但去除了“壺”這一帶有濃厚宗教色彩的媒介,敘述重心變為對詭異情境的刻畫上,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原先的道德教化意味。《鵝鵝鵝》則將重心放在對主角與其他角色的交互上,著重刻畫了“你”這一平凡小人物形象。為何故事的主旨會不斷發生變化?究其原因,則與各自不同的時代背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如宗白華所說:“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 ⑤魏晉時期王朝更替頻繁,到處充斥著數不盡的戰爭和皇族血淋淋的殘殺,無數的紛爭也讓世間民不聊生,平民士大夫階層難以自保,飽受肉體和精神上的雙重苦痛。這種社會背景給宣揚“現世報”“輪回轉世”“忍受苦痛得以苦修成佛”的佛教思想提供了適宜的生存土壤,民眾悲苦的內心從此得到慰藉,例如《梵志吐壺》這樣旨在告誡信徒遠離情欲,靜心修行的譬喻故事也得以傳入中國,在中原得到了可觀傳播。
除去佛教的傳播,在這種混亂的大背景下,《陽羨書生》主旨的本土化改進則與魏晉朝精神世界的解放有著緊密關聯。政權的頻繁更迭,讓統治者的思想難以形成自上而下的統一,這直接導致了兩漢經學的崩塌與道教的復興。文人志士將思考中心從對階級秩序的維護變為對自我價值的探討,開始思考本身存在的意義。自此,人的自我意識開始覺醒,加之混亂的政局也讓世人敢于表達自我,精神世界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出現如《古詩十九首》這種感嘆性命短促、人生無常,何不及時行樂的詩篇:“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這些詩句干脆坦率,直抒胸臆,表達的是人對自己生命的重新發現與探索。相比于《梵志吐壺》中純粹的敘述事實,《陽羨書生》多了許彥與被吐出男女之間的對話:“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彥曰:‘善。女子于口中吐出一男子……” ⑥隨后面對被吐出男女們同樣的請求,許彥亦只是回答“善”。這簡單的一個“善”,說明許彥并不認為男女私情是件有損風化的齷齪之事,僅僅是作為一個看客旁觀這些因變故無法與真愛長相守,只能趁機私會的男女互道真情。這顯然符合魏晉追求真摯情欲,及時行樂的社會風尚。即已是亂世,何不趁此機會與真愛共享佳肴,共同享樂?
那么,《鵝鵝鵝》繼承的又是兩者中的哪一思想呢?筆者認為,二者皆有之。首先從片中“你”對男女私會的默認態度上看,動畫應該是繼承了《陽羨書生》中對情欲的肯定態度。不僅如此,片中還讓身為凡人的“你”與其中的鵝妖跨越身份和種族的差別互生情愫,可見導演在創作動畫時并沒有選擇先前的道德教化目的,站在道德層面譴責這些男女的不潔。但在另一方面,動畫在開頭就點出結局“這里是鵝山,是你失蹤的地方”,說明“你”在最后并沒能成功走出鵝山,這悲劇結尾的背后則又是對《梵志吐壺》內涵的繼承。除嬉戲放逸的象征外,“壺”作為私藏男女的空間載體,在佛教中也是諸多狹小物體內部空間被無限放大,“別有洞天”的典范。這在中國神魔小說中亦有記載,例如《神仙傳》中的“壺公”,也是依靠自己的法寶壺劫富濟貧。與之相對應,葫蘆在中國民間亦被認為是天地的微縮,內部寄宿著靈氣,作為善神寶器而存在,既能驅邪除惡,又可擒妖捉怪。《西游記》中的金、銀角二妖擁有的紫金紅葫蘆寶器,就有可以將人吸入其中,將其化為濃水的神力。這些看似狹小,內部卻別有洞天的空間載體以不同形式具象化,在《梵志吐壺》中它是私藏男女的“壺”,在《鵝鵝鵝》中,則是裝載著鵝的“鵝籠”。
如果說《梵志吐壺》中的“壺”象征的是見不得光卻永不知足的男女私欲,筆者認為,《鵝鵝鵝》則是將其中特指男女情欲的“欲”字進一步作了延伸,擴展至更大范圍的“欲望”范疇,意在警醒世人時刻注意自身無限膨脹的欲望。魏晉時期盛行玄學,追求道法自然,以自然本身為美的黃老之術,故事中的“你”作為普通貨郎,只因貪圖捷徑走上鵝山這道險路,才在途中遇到書生,被卷入到這一系列風波當中。動畫中斷腿書生的形象借鑒了《天書奇譚》中狐妖的設定,能施展妖術,吞吐活人的狐貍書生的出現對于貨郎而言,就像是一道新世界的大門,又像是潘多拉的魔盒,讓他既恐慌,又好奇,于是在半推半就的情境下同意帶書生前往山頭,在到達山頭后,原本可以就此一走了之的貨郎又被書生的誘惑迷住,與他共享佳肴美酒。故事發展到這里,原本無欲無求的貨郎已然在狐妖書生的一步步誘惑下點燃了內心的欲望之種,從最開始的不愿參與其中的態度漸漸轉變為對未知世界的新奇,而之后鵝妖的出現更是進一步激發了他對美好事物的占有欲望。又有幾人能夠拒絕與美麗的女子互訴衷腸呢?如旁白所說,眺望鵝山美麗的風景,“你”不禁“想讓她片刻停留”。此刻的貨郎早已沒了對欲望的戒備,對美的欲望讓他忘卻了對神魔鬼怪的畏懼,想要獨自占有眼前的“美”。鵝妖懇求“你”帶她出山,想要變成一只鵝住在鵝籠,“你”想要答應,注意力卻停在了鵝妖那張黑漆漆的嘴上。這里的每個妖都有自己的心上人,卻都與自己的心上人同床異夢,“你”又該如何確保眼前的鵝妖不會在自己睡著時再吐出新的心上人呢?“你”對此猶豫不決,生怕鵝再有鵝。在這一刻,貨郎心中對“美”的追求和對男女忠貞思想的堅守到達矛盾的頂峰,對愛情的欲望讓他愿意帶眼前的美人離開,可傳統道德觀中的忠貞思想又讓他望而退步,生怕自己會重蹈前面幾妖的覆轍,幫別人做了嫁衣。隨后,就在“你”選擇遵于自身欲望,接納眼前這位心上人的當中,書生蘇醒,被吐出的幾妖又陸續被吞了回去,“你”失去了自己的愛人,再次變回了那個一無所有的貨郎,連同原先鵝籠中被書生所吞的兩只鵝一起失去了三只鵝。由此,動畫點名標題:《鵝鵝鵝》。前兩只是貨運時丟失的鵝,第三只則是失去的心上人。
不難發現,動畫中貨郎的欲望并非一開始便有,而是伴隨情節的發展慢慢被點燃。狐貍書生在劇中的作用就像是未知世界的領路人,一步步引領貨郎走向欲望的無盡深淵。《梵志吐壺》里的壺是愛欲的具象化,而《鵝鵝鵝》中的鵝籠,即是關押鵝的竹籠,亦是故事中每個人心中的那扇欲望的鵝籠,是一把隱形的枷鎖。《鵝鵝鵝》中的貨郎看似自由,卻在書生的引誘下,從對事態的旁觀一步步變為事件的參與者,完成了從對鵝籠的觀看到成為籠中一員的蛻變。當書生離場,一切回歸正常,品嘗過愛情,亦是欲望滋味的貨郎卻再也無法回到先前無欲無求的平靜,只能帶著對昔日愛人的眷戀與一念之間失去愛人的苦痛淪陷在欲望的黑洞,在“鵝籠”的籠罩下無力自拔,可謂“人生何處不鵝籠”。《鵝鵝鵝》的主旨即有《陽羨書生》中對男女真情的肯定,又有《梵志吐壺》中對過分情欲的否定,與前二者全面肯定或批判的態度相比,它更像是對內容的折中融合,意在表達人需要欲望,但也需時刻警惕欲望的哲理內涵,令人回味無窮。
注釋:
①(法)米歇爾·布托爾著,桂裕芳譯:《變》,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3頁。
②張閎:《論第二人稱敘事》,《當代文壇》2022年第5期,第7頁。
③(唐)段成式撰,許逸民校箋:《酉陽雜俎校箋》,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1673頁。
④丁敏:《中國佛教的古典與現代:主題與敘事》,岳麓書社2007年版,第126頁。
⑤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7頁。
⑥陳文新:《六朝小說》,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年版,第314頁。
參考文獻:
[1]麻國慶,朱偉.文化人類學與非物質文化遺產[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
[2]米歇爾·布托爾.變[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5.
[3]張閎.論第二人稱敘事[J].當代文壇,2022,(5).
[4]段成式撰,許逸民校箋.酉陽雜俎校箋[M].北京:中華書局,2016.
[5]丁敏.中國佛教的古典與現代:主題與敘事[M].長沙:岳麓書社,2007.
[6]宗白華.美學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7]陳文新.六朝小說[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