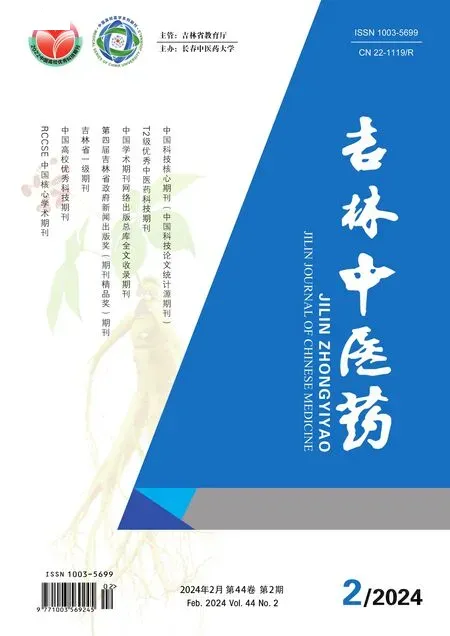基于“三焦氣化”探析原發性肝癌的中醫動態病機觀
寧天宇,劉松江
(1.黑龍江中醫藥大學,哈爾濱 150040;2.黑龍江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哈爾濱 150040)
原發性肝癌是我國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1],其腫瘤致死性居于第二位,對于患者的身體和心理有著雙重打擊,臨床所見肝臟惡性腫瘤類型可分為肝細胞癌(HCC)、肝內膽管癌(ICC)及其混合型,其中HCC 所見較多,達75%~85%[2]。現代醫學對于肝癌病因機制的認識尚未完全統一,其誘發因素大多歸于乙/丙型肝炎病毒感染、過量酗酒、各種原因導致的肝硬化、家族史等,目前治療手段仍是在具備手術切除的條件下首選外科切除,同時通過MDT的診療模式,按照不同的分期選擇療效最大化的方案[3]。由于患者在診斷本病時的身體狀態(即PS評分、Child-Pugh分級)是具有一定的變化性的,這種可予以調節的身體狀態對于繼續下一步的治療具有明顯的等級劃分,所以,把患者的身體狀態盡可能恢復到最佳狀態來進行治療可以最大地發揮臨床療效。
隨著近年來中醫藥的發展,在祖國醫學指導下的病證辨證-中西結合模式對于患者的圍手術期、術后輔助治療期、隨訪康復期等不同時期,中醫藥起到了重要作用,為患者爭取到了更高的生存時間及質量。肝癌在祖國醫學中記載為“肝著” “臌脹”“痃癖”“癥瘕”等病名[4],多由于飲食勞倦所上,或情志不遂等因素,致使臟腑功能失調,肝氣郁結,痰瘀內生,濁毒萌生,發為本病。其實,肝癌的本質就是癌毒的形成與擴散的過程[5],即肝藏血主調達,以疏泄為用,若患者正氣不足或氣機紊亂,造成人體五臟六腑氣機失暢,肝氣郁結于脅下,疏泄無權,久而化瘀,蘊結為癌毒,若癌毒擴散,則病情危矣。現代中醫臨床中大多醫家將本病辨證分型,或歸于肝、腸、脾、腎等臟腑經絡之損毀,或歸于氣、血、痰、瘀等運行失常,并根據證候分類,按證索方[6-8]。而本篇結合臨床所見,癌毒既是人體臟腑陰陽失衡的病理產物,又是進一步損傷機體功能的致病因素,如外感諸邪或七情內傷導致臟腑經絡氣血失和,氣滯血瘀久滯肝絡,發為本病,且隨著病勢進展,癌毒進一步阻滯氣機,瘀郁熱濕內壅互結,損毀壽數,形成“氣郁-邪實-癌毒熾盛-陰陽離決”的病機動態。所以,肝癌并非一臟一腑之病變,而應歸屬周身三焦之變化,遣方用藥也不可妄自攻伐,應遵行氣散滯、柔肝調肝之法。
1 三焦的釋義及發展
三焦的提出,首見于《黃帝內經》[9],“三焦者,中瀆之府……是孤之腑也”,同時《素問》詳細的記載了三焦的位置,如“上焦出于胃口……中焦亦并胃中……下焦者,別回腸”,其功能屬“決瀆之官,水道出焉”。需要指出的是,《內經》中并未詳細地描述三焦的具體形態,只是根據其功能分為了上中下三焦,“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這一情況使得后世醫家對于三焦的認識不斷發揮,擺脫開機體結構來探求中醫理論下的三焦生理功能[10]。所以,三焦的理論基礎并非是按照解剖學的實體發現來確定的,而是根據其功能由“有形之三焦”發展為“無形之三焦”,同時為溫病學說奠定了一定基礎。如唐·孫思邈在《備急千金要方》言:“夫三焦者,一名三關也……有名無形,至五臟六腑,往返神道,周身貫體,可聞不可見”;明·趙獻可《醫貫》言:“三焦者……有名無形,主持諸氣,以象三才”,認為三焦有名無形;近代張錫純提出“人體之氣化以三焦為總綱”,通過三焦可內滋臟腑竅穴,外濡關節經絡肌膚;現代醫家結合臨床醫學認為三焦與人體內微循環、內分泌、免疫系統等有關[11],從而更加擴大了三焦的意義和理解。因此,中醫對于三焦的認識經歷了一個從有形到無形的發展階段,雖然歷代醫家對此或有爭論,但正是這一爭論反映了中醫的本質,即整體觀念,重視局部與系統的聯系,把握各個臟腑的生克關系,從而更加促進了中醫發展。
2 三焦氣化的作用
氣化,即氣在機體中升降出入的一切變化,氣化的存在,是人體進行生命活動的基礎。中醫“氣化”一詞首見于《素問·氣交變大論》[12]:“其應奈何?各從其氣化也”,認為人體氣機通過正常運行,從而應對外感邪氣的變化。至明代趙獻可首次提出“三焦氣化” 的理論,認為體內津液及水谷精微物質的輸布代謝與肺脾腎三臟相關,膀胱氣化尿液,較為完善地詮釋了三焦對于精氣代謝的作用機制[13]。上焦氣化與肺:肺,主宣發肅降,將自然界中的清氣吸納入體,與營衛之氣合為宗氣,聚于上焦,隨著肺的呼吸,上充毛竅,宣發氣機,又可下行歸腎,滋養元氣。中焦氣化與脾:脾,主運化水谷精微,《靈樞》曰:“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中焦的氣化功能體現在脾之運化轉輸營衛津血,維持正常機體能量,參與宗氣的生成。下焦氣化與腎:下焦所主之元氣不僅取決于先天稟賦,同時也依賴于后天滋養,下焦的氣化使得中上二焦所化之宗氣與自身元氣相結合,以滋五臟六腑,才能使得陰平陽秘,生生不息。三焦連貫,上下相通,才是氣化之本,三焦氣化的正常運行,體現了體內陽氣對精血津液的生成與運行輸布的重要作用,體內痰飲、水濕、瘀血等病理產物得以產生,均與三焦氣化的功能運行失司密切相關,因此,本篇以三焦氣化為綱,整合臟腑經絡與癌毒的病機關系,探究肝癌發生與發展的中醫動態病機觀。
3 肝癌患者的病機特性
3.1 氣機郁滯為標,陽氣不足為本 肝,為風木之臟,喜調達,主升發,是機體正常氣血活動的積極動力。《林氏活人錄匯編》言:“肝之積為肥氣,蓋由郁怒傷肝,肝氣不能條達,使生陽之氣,抑而不升,郁滯于左右兩脅之間,形如覆杯,積成肥厚之氣。”大部分肝癌早期患者并沒有明顯癥狀,只是伴隨“起居不時,憂忿過度,飲食失節”的生活狀態[14],致使氣機運轉失常,肝氣郁結于脅下,逐漸出現乏力、消瘦、脅肋隱痛等癥狀。另外,肝的另一生理功能是“體陰用陽”,陽氣衰弱不足,正不勝邪,則是癌毒發生的根本原因[15]。張景岳言:“脾腎不足及虛弱失調之人多有積聚之病”,若先天之本腎陽受損,則氣化失司,三焦不暢,手足不溫,水濕泛濫,一派臃腫;若后天之本脾陽受損,則中焦不運,水飲停聚,運化失常,清濁難分,腹脹腹滿,飲食難消。
3.2 邪盛正衰是病情進展的重要因素 肝癌的關鍵,在于癌毒的形成與擴散。《靈樞》:“若內傷于憂怒,則氣上逆,氣上逆則六輸不通,溫氣不行,凝氣蘊裹而不散,津液澀滲,著而不去,而積皆成矣”,由于氣機閉塞,痰濁內阻,濕熱化毒,久而不消,肝臟失去正常運轉的能力,同時伴隨正氣虛損,則癌毒形成。國醫大師周仲瑛指出:“肝癌的形成雖以正虛為基礎,但癌毒侵襲為其必然條件,所以重視癌毒的形成與進展,尤為重要,因為癌毒不僅是病理產物,更是進一步阻塞氣機,化火化毒的致病因素”[16]。癌毒一旦形成,則膠著難醫,初期雖癥狀不顯,極其隱匿,可一旦發病,則必然影響氣機失調,津血運行不暢,痰濁阻塞,擴散轉移他處,成烈火燎原之勢。
3.3 癌毒易化火、易蓄水、易傷陰、易動血 所謂“久郁化火”,癌毒的產生由痰濕邪穢積聚體內日久所致,在正氣驅逐病理產物的過程中則會化毒化火,患者可表現為口干口苦、眼睛干澀、小便色黃等火氣內蘊的表現,此為化火。癌毒進展后常表現出腹水,與蛋白失衡、癌細胞刺激、淋巴系統有關,中醫認為,肝主疏泄,體陰而用陽,腹水的發生與肝的疏泄失常有關,或因氣滯血瘀,或因濕熱困阻,或因陰陽寒熱不調等,均可發生蓄水;肝為“剛臟”,體陰而用陽,即肝以機體陰液津血為根本,以宣展陽氣溫煦推動為目的,在癌毒的影響下,患者長期消耗陰液,則易出現肌膚甲錯、口干便秘、夜間潮熱,此為傷陰。癌毒晚期,尤其是合并肝硬化,患者體內氣機橫逆,引動血分,可出現腹脹納呆,脅肋疼痛,面色黧黑,嘔血便血等消化道出血,此為動血。總之,在人體正氣強盛的條件下,癌毒若能積聚內斂,尚能用藥治之,但若癌毒擴散,病情進展,則壽數難言。
4 三焦氣化對肝癌患者的病機動態辨治
4.1 氣郁-邪實:清毒排毒,三焦分治 肝癌患者在最初階段并沒有明顯的癥狀及體征,部分患者出現體重下降、飲食油膩則腹脹、右脅處偶有隱痛、重體力勞動易疲乏勞累等情況,故很難受到重視[17]。從疾病診斷到發病階段,應積極重視患者身體狀態及肝功能情況,才能為進一步的手術、介入、靶向藥治療等做好準備。《素問》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此時患者處于“氣郁-邪實”的階段,正氣尚足,邪氣逐漸匯聚,積為痰濕瘀毒,治療既要清毒排毒,又要三焦分治。
若上焦肺氣宣降不暢,可伴有咽中異物感,咯痰難出,咳嗽氣悶,情緒焦慮等,兼有痰氣郁結,正氣尚足者,用藿香、佩蘭、紫蘇宣透化濕,合以茯苓、澤瀉利濕去濁,選方如半夏厚樸湯,上焦宣痹湯等;兼有痰濁伏肺,頑痰難消者,用蘇子、貝母、白芥子豁痰利竅,合以半夏、細辛蠲飲降逆,選方如蠲哮湯、三子養親湯等;兼有正氣不足,咳痰乏力者,治當扶正化痰,少用黃芪、人參、西洋參補氣益肺,加用茯苓、白術建中補脾,配以石菖蒲、郁金化痰開竅,選方如四君子湯、三香湯等;兼有氣滯不暢,情緒焦躁者,用柴胡、芍藥、枳實疏肝理氣,陳皮、茯苓健脾和中,選方如柴胡疏肝散,逍遙散等。若中焦脾胃痰瘀阻滯,運化失常,可伴有胃脘脹悶,飲食不易消化,形體消瘦,面色萎黃,二便不調等,兼有氣虛乏力,脾胃虛損者,用黨參、茯苓、山藥健脾益中,雞內金、白術助其運化,選方如補中益氣湯、歸脾湯等;兼有濕熱內生,痰濁中阻者,用黃芩、黃連、茵陳燥濕化濁,蒼術、厚樸行氣暢中,選方如三黃湯、平胃散等;兼有瘀濁阻滯,飲食積滯者,用蒲黃、五靈脂、山楂、神曲消積導滯,桃仁、三七活血散瘀,選方如膈下逐瘀湯、失笑散等;兼有腹脹納呆,寒濕困脾者,用干姜、草豆蔻、木香溫中散寒,陳皮、當歸養血和胃,選方如溫中湯、理中湯等。若下焦肝腎陰陽失調,陰虛火旺者可伴有面色顴紅,手足心熱,眼干眼澀,肌膚干燥等,選方如六味地黃丸、左歸丸等;肝腎精氣不足,陽氣虧虛者可伴有手足不溫,喜溫畏寒,夜尿頻多,精神不佳等,選方如腎氣丸、右歸丸等。
4.2 邪實-癌毒熾盛:中焦為主,上下兼顧 當癌毒發病期進一步出現癌毒影響的身體狀況時,患者可伴有脅肋疼痛,黃疸,腹脹腹滿,納差乏力,大便異常等,此為癌毒由最初的病理產物逐漸成為了致病因素,臨床應以增強患者的身體素質為目標,在具備外科切除的條件下,首選手術、介入等治療[18]。部分患者在經受精神打擊之下,或接受介入(TACE)、消融術或新輔助化療后,出現明顯肝郁脾虛,中焦不運,濕熱困阻,瘀血阻滯的情況,此時應顧護中焦,上下兼顧,益氣扶正與攻邪逐邪并治。《金匱要略》云:“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中焦脾胃的強健對于肝癌的治療非常重要,因為肝以氣血為養,若癌毒阻滯合并中焦氣血生化無源,肝體無以所養,必然導致病情快速進展,即使能夠支持手術,也必定影響后續治療。
故發病期患者首當辨清虛實之輕重,若正氣尚足,并發癥較少或可耐受, 臨證可予以排毒除濕、攻毒消癥、化痰軟堅之法。如患者心煩口苦,小便短赤,腹脹腹滿,情緒煩躁,予以龍膽瀉肝湯加芍藥、茵陳等;如腹脹腹滿,脅肋疼痛,胸悶不暢,發熱,黃疸,予以清熱解毒藥與活血化瘀藥,如白花蛇舌草、莪術、半邊蓮、虎杖等;如脅痛如刺,腹脹不饑,舌質晦暗有瘀斑,予以柴胡疏肝散加海藻、昆布、瓦楞子等。若正氣漸虧,伴有上腹部腫塊,疼痛易乏,飲食欠佳等,臨證可予理氣化痰、養血益氣之法,如患者出現腹腫脹悶,食少消瘦,倦怠神疲,舌淡邊有齒痕等,可予逍遙散和香砂六君子湯加減;如患者出現脾虛泄瀉,氣血虧虛,形體消瘦,食欲不振等,可予參苓白術散加減。同時,在癌毒的中焦固護過程中,應同時兼顧上焦心肺與下焦肝腎,上焦者多用黃芪、防風、白術以固護肺衛,下焦者多用一貫煎疏肝養陰。
4.3 癌毒熾盛-陰陽離決:下焦為主,平調陰陽 《景岳全書》言:“五臟之傷, 窮極必腎”,癌毒損傷機體致人死亡的便是這一階段。患者大多手術或介入治療之后,正氣已虧,癌毒肆虐,同時在痰濁瘀阻、易感外邪、臟腑精氣虛損、藥物不良反應等諸多因素影響之下,使病情隨之加重,癥見肝區滿痛,體倦乏力,面色枯槁,腹滿腹脹,食少納呆,肢體浮腫等。《重訂通俗傷寒論》言:“陽虛者陰必盛, 陰盛者氣必弱”,此時的治療當以顧護下焦肝腎、平調陰陽為要。
《素問·生氣通天篇》言:“陽氣者, 若天與日,失其所, 則折壽而不彰。”在疾病發展的最終階段,中醫認為,“存一分陽氣,便有一分生機”,若患者陽虛體寒,四肢不溫,浮腫,面色蒼白,小便不利,此為陽氣不足,可用四逆湯、潛陽封髓丹等,使下焦陽氣充盛,則有助于各個臟腑功能恢復,同時注意用藥防止辛溫燥烈損傷正氣[19],如《素問》言:“大積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過則死”,不可用藥過猛,應徐徐調之。若患者潮熱盜汗,形體消瘦,皮膚干糙,舌紅少苔,此為陰液虧損,虛火內擾,可用增液湯、大定風珠等,滋補肝腎,固護陰液。《溫病條辨》言:“熱邪久羈,吸爍真陰”,癌毒最易化火傷陰,故治療采用柔肝潤肝之法,即所謂“養其肝體,則其用自柔”。
5 基于三焦氣化用藥特色
5.1 行氣散滯,不忘護陰 基于三焦氣化,在肝癌的各個治療階段,均應以氣機通暢為主,臨床多用行氣散滯之藥,如柴胡、枳實、陳皮、青皮、香附等,也常用利濕利水藥,如茯苓、薏苡仁、澤瀉、茵陳、玉米須、冬瓜皮等,由于行氣藥偏于溫燥,祛濕藥易于傷陰,所以在臨證遣方時稍加芍藥、地黃、玄參、女貞子、枸杞子等涼潤甘緩之藥,防止陰液損傷。閆慧文等通過益氣養陰解毒之法改善患者身體疲乏、情緒低落,重視用藥不可一味攻伐,所謂“陽常有余,陰常不足”,故后期常以益氣養陰,肝脾腎三臟同治,解毒化瘀等延緩癌毒的進展[20]。
5.2 散瘀通滯,慎用活血之藥 在肝癌的“邪實-癌毒熾盛”階段,若患者伴有面色黧黑、舌質紫暗等癥狀,屬于瘀毒阻滯,或癌毒積聚腫瘤較大,單純用軟堅散結藥效力不夠,為了更好的通行氣血,常配伍活血化瘀藥如三棱、莪術、水蛭等。彭艷等采用活血化瘀法治療惡性腫瘤,意在氣血調和,脈絡通暢,認為久病多瘀,故在諸多治法中加以活血之品,辨證施治[21]。但是,臨床中肝癌患者應注意凝血功能的異常,因為腫瘤的存在會改變纖維蛋白原、血小板黏附性、血漿黏度等,故慎用活血藥[22],可改用活血止血藥如三七、蒲黃、當歸等,并時刻注意患者出血傾向。
5.3 滋肝補腎,尤重調理脾胃 患者在“癌毒熾盛-陰陽離決”階段,應重視調整陰陽虛實,此時大多久病及腎,耗傷真陰,故臨證用藥如北沙參、麥冬、熟地黃等滋膩礙胃之品,可適當加用配伍陳皮、砂仁、木香、焦三仙等醒脾開胃藥,健脾和中,使補而不滯。5.4 癌性疼痛 癌性疼痛是患者臨床遭受的極大痛苦之一,在臨床治療中,中藥治療配合癌痛三階梯方案能夠發揮積極作用,減少西藥帶來的神經功能紊亂等不良反應,通過中醫辨證的方式,判斷誘發癌痛的主要因素,針對不同體質辨證用藥,如熱毒較重用延胡索、夏枯草、重樓、蒲公英等;氣滯較重用細辛、乳香、沒藥、川楝子等;瘀毒較重用穿山甲、蜂房、三七、水蛭等。
6 討論
《中藏經·論三焦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脈證之法》言:“三焦總領五臟六腑、營衛、經絡、內外、左右、上下之氣也。”三焦通暢,正氣周流全身,調和陰陽,是人體強健的根本。本文基于三焦氣化論治肝癌的發病與進展,因為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而且診療指南也會隨著個體的差異選擇不同的措施,所以三焦氣化的貫穿性分析相比于單純的辨證分型要更加清晰且具備臨床實踐性。如在癌毒的最初階段重視三焦分治,兼以清毒排毒,行氣化痰散滯活血;隨著病情進展需要顧護中焦,上下兼顧,益氣扶正與攻邪逐邪相結合;到了疾病的終末期,應予平調陰陽,延遲壽命,防止陰陽離散。總之,基于三焦氣化辨治肝癌的思維診療方式,是集合了病位-病性-病勢的多重思路,更加有益于臨床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