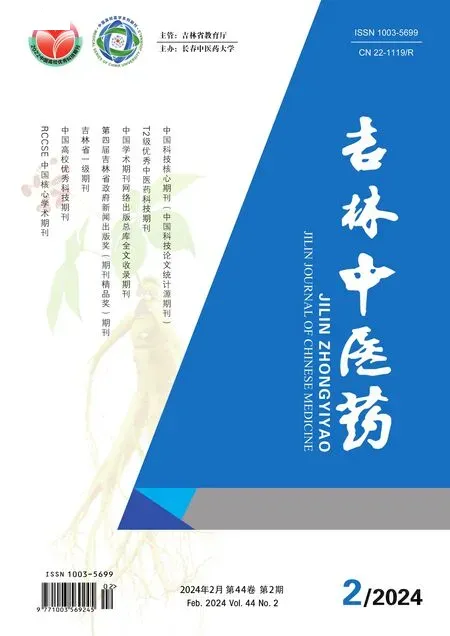國醫大師劉柏齡運用補腎祛瘀法治療膝骨性關節炎經驗
張憲帥,石明鵬,劉世林,周國徽,馬 悅,趙長偉,李紹軍,孫鳳玲,李振華*
(1.長春中醫藥大學,長春 130117;2.長春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骨科中心,長春 130021)
膝骨性關節炎是以關節軟骨破壞,關節骨質增生引起的慢性退行性疾病,臨床主要表現為膝關節疼痛及活動障礙。中醫學將膝骨性關節炎歸為“痹病”“骨痹”等范疇,多見于中老年人,病程常遷延難愈,有一定致殘率,嚴重影響患者的生存質量。流行病學顯示: 我國骨性關節炎的患病率約為15%,隨著年齡的增長患病率逐漸增加,70 歲以上年齡者高達80%[1]。常與性別、年齡、肥胖、膝關節外傷史等因素有聯系[2]。臨床上常采用膝關節鏡以及全膝關節置換術來治療,給患者造成了嚴重的精神經濟負擔[3],近年來,中醫藥治療膝骨性關節炎顯示了明顯優勢,并且獨具特色。
國醫大師劉柏齡行醫70 余年,治療本病有著獨到的經驗。劉柏齡認為本病的發生是在肝腎虧虛的基礎上,加之風寒濕侵襲以及痰濁瘀血痹阻經脈發而為病,補腎壯骨、祛瘀除痹是本病的基本治法,即補腎祛瘀是重要環節。本人有幸跟隨劉柏齡教授侍診,現將劉柏齡治療膝骨性關節炎的臨證經驗介紹如下。
1 肝腎虧虛為本,瘀血痹阻為標
1.1 腎與骨的關系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治病必求于本。”劉柏齡指出膝骨性關節炎的發生與肝腎虧虛有密切的聯系。膝為筋之府,膝關節周圍由肌腱韌帶包繞,連接骨骼關節起到主束骨而利關節的作用。“肝主筋……為罷極之本”,是人體生命活動調控的樞紐[4]。肝血充盈,則筋脈勁強,肝血虧虛,則筋束骨的能力減弱,導致膝關節屈伸不利。“腎主骨生髓”“骨者,髓之府”,骨髓來源于腎中精氣的充盈,也依賴于腎陽的推動和氣化。腎精與腎陽對于骨的生長發育至關重要,在20 世紀70 年代,劉柏齡基于現代醫學骨骼運動體系的認識,并結合“腎主骨生髓,髓充則能健骨”的再認識,提出“治腎亦即治骨”的學術思想[5]。在此基礎上,劉柏齡指出肝腎不足,筋骨關節失其濡養而空虛是本病發生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治療上以補腎壯骨為基礎,即“治腎亦即治骨”。
1.2 瘀血既是病因,亦為病理產物 瘀血是指體內氣血推動無力,凝滯不通形成的病理產物,瘀血既是膝骨性關節炎的致病因素,也是膝骨性關節炎發生發展和加重的原因。《素問·舉痛論》云:“寒氣客則脈不通。”劉柏齡指出外感六淫中風寒濕邪侵襲是膝骨性關節炎的外因,其中寒濕影響最大。寒為陰邪,易傷陽氣。膝骨性關節炎初起多因腎陽不足,寒邪凝滯筋骨關節,陰寒內生,若遇外寒,則內外合邪,發而為病。如若遇到跌打損傷,外傷導致脈絡破損血溢脈外而成離經之血,則進一步痹阻經脈,即因實致瘀;《素問·上古天真論》云:“女子七七,任脈虛,太沖脈衰少……男子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八八,天癸竭,精少,腎臟衰”,腎主氣依賴腎中精氣的蒸騰氣化作用,隨著年齡增長,腎虛臟腑功能氣化減弱,精血同源,肝不藏血,腎精不足與血液難以互生互化,氣血推動無力,終致血瘀,即因虛致瘀。《素問·痹論》曰:“病久入深,榮衛之行澀,經絡時疏,故不通”,膝骨性關節炎是退行性病變,隨著患者年齡的增長,久病入絡,營衛之氣循行異常,氣血運化無力,瘀血留滯于經脈筋骨,即久病致瘀[6]。基于以上因實、因虛、久病致瘀的論述,劉柏齡指出瘀血痹阻是膝骨性關節炎病理的關鍵所在。
2 辨治特色
2.1 補腎祛瘀法貫穿始終 劉柏齡指出膝骨性關節炎病位在于肝腎,與筋骨關系密切,根據本病多為老年人,患病率高,且病程較長,臨床常表現為膝關節隱隱疼痛,屈伸不利,局部僵硬,活動受限,畏寒肢冷,腰膝酸軟疼痛,可出現頭暈耳鳴,舌紅,苔薄白,脈沉細無力。劉柏齡認為膝骨性關節炎病機為本虛標實,腎氣不足是本病的內因,標實雖有因實、因虛、久病致瘀之分,但血瘀是其致病的主要病理因素。基于以上病因病機及病理變化過程的認識,劉柏齡將補腎祛瘀法貫穿于治療全程,擬膝痛1 號方,處方:伸筋草15 g,蒼術15 g,澤瀉15 g,澤蘭15 g,五加皮15 g,赤芍15 g,丹參15 g,骨碎補20 g,豨薟草15 g,續斷15 g,防風10 g,陳皮15 g,薏苡仁15 g,蜈蚣2 條。方中骨碎補為君藥,具有補腎壯骨,活血止痛之功,現代藥理學研究[7]表明骨碎補可以促進軟骨細胞的增殖,對軟骨細胞的損傷具有保護作用。薏苡仁、蒼術、澤瀉、澤蘭、防風清利水濕,赤芍、丹參、蜈蚣活血祛瘀,五加皮、續斷補益肝腎,伸筋草、豨薟草舒筋通絡,諸藥合用,共奏補腎壯骨、祛瘀除痹、扶正祛邪之功。
2.2 辨證加減 劉柏齡臨證使用本方,執簡馭繁,據證加減,臨床強調在補腎祛瘀的基礎上應辨風、寒、濕、痰、瘀之偏勝,寒凝者溫而通之,血瘀者逐而通之,痰濕者化而通之,氣虛者補而通之,在補腎祛瘀的基礎上隨癥加減變化。關節冷痛、畏寒喜溫、四肢發涼、關節拘攣者,加仙茅、狗脊、桑寄生補肝腎、強筋骨,祛風除濕;關節腫脹、灼熱、濕熱下注者加黃柏、徐長卿清熱除濕、通利關節;關節慢性腫大,關節周圍結節者加白芥子、白僵蠶化痰通絡;關節刺痛,四肢麻痛者加土鱉蟲、地龍活血祛瘀;腰膝酸軟、頭暈耳鳴者加熟地黃、制附子、肉桂補腎陽、益精血;骨蒸潮熱,自汗盜汗者加知母、黃柏滋陰退熱除蒸;氣虛乏力者加當歸、黨參補氣養血;脾虛便溏者加白術、砂仁健脾益氣;老年便秘患者加肉蓯蓉、火麻仁潤腸通便。
2.3 用藥特色 劉柏齡臨床用藥特色鮮明,善用重用海螵蛸。海螵蛸,味咸、澀,性微溫,《本草求真》言其“服此咸能走血,溫能除寒逐濕,則血脈通達,故直入厥陰肝經血分活血”。劉柏齡指出海螵蛸一方面具有祛寒除濕活血通經的作用,另一方面還具有收澀之性,因大部分患者年老體衰,而大劑量的破血通經之品走竄之力較強,猶恐傷血動血,為防止太過而用本品起到反制的作用,劉柏齡一般臨床治療用量為20 ~30 g。現代藥理研究[8]表明海螵蛸對軟骨損傷的修復具有一定療效,可以提高成骨細胞的分化、促進骨誘導,對軟骨的損傷修復具有愈合的作用。
劉柏齡善用藤類藥和蟲類藥。《本草便讀》云:“凡藤類之屬,皆可通經入絡。”根據取類比象的原則,藤類藥之屬多攀枝纏繞,走竄多變,因其本性大多數藤類藥具有通絡的作用[9],尤其是對于經絡痹阻的患者,常用補血活血的雞血藤、雞矢藤,祛風除濕的絡石藤、海風藤,祛痰通絡的青風藤、威靈仙。另外,劉柏齡還善用蟲類藥搜剔經絡中的頑痰瘀血。葉天士曰:“久則邪正混處其間,草木不能見效,當以蟲蟻疏逐,以搜剔絡中混處之邪”。該病久病入絡,寒瘀血阻滯經絡,其化為敗瘀凝痰,非草木通經之品所能企及,而蟲類藥因其蠕動及飛靈走竄之性,能搜剔絡中瘀血,具有推陳致新之功[10]。臨證常用蜈蚣、地龍、烏梢蛇、土鱉蟲、全蝎、僵蠶、桑螵蛸等蟲類藥,臨床用量多為9 ~15 g。
2.4 內外同治 《理瀹駢文》云:“外治之理,即內治之理;外治之藥,即內治之藥。所異者法耳。”內外治法是針對同一疾病的不同治療手段,劉柏齡常采用內外結合的方式治療,在服用中藥的同時,重視病變局部用藥。中醫學認為,人體是以五臟為中心的整體,外在四肢百骸,內在五臟六腑,經脈則是聯絡兩者的通道,若人體受到損傷,氣血運行失常,經脈痹阻不通則痛[11],中藥熏洗是將中藥煎煮后在皮膚或指定位置進行熏蒸或者淋洗的治療方法,經脈喜溫而惡寒,熏洗可以加快氣血循行,筋脈暢通則人即安和,達祛邪扶正之效[12]。對于膝骨性關節炎,劉柏齡每次臨證均囑患者外用院內制劑熏洗Ⅱ號方進行患部熏洗以達到舒筋活絡、祛瘀除痹的目的,熏洗Ⅱ號方的組成為透骨草、威靈仙、急性子、烏梅、生山楂、伸筋草、防風、三棱、骨碎補、紅花、莪術、白芷、白芥子、皂角、麻黃、馬錢子等。
3 病案舉例
王某,女,62 歲,2019 年11 月28 日一診。主訴:雙膝關節疼痛1 年,加重2 周。現病史:1 年前因勞累后出現雙膝關節酸軟疼痛,活動不利,行膝關節封閉治療。2 周前雙膝無明顯誘因疼痛加重,服用非甾體抗炎藥“西樂葆”疼痛稍減輕,現癥:雙膝關節疼痛,右側重,左側輕,右側膝眼自覺刺痛腫脹,夜間疼痛尤為明顯,小腿痙攣,腰膝酸軟無力,雙下肢怕涼,晨僵明顯,舌暗苔白,脈沉細。西醫體格檢查:雙膝關節壓痛(+),右膝屈伸不利,右側膝眼飽滿,活動明顯受限,右側麥氏征(+)、右側浮髕試驗(+)。輔助檢查:自帶MRI(2019 年7 月23 日)示雙膝關節存在脛骨平臺增生改變、髕骨增生。西醫診斷:雙膝退行性骨關節炎;中醫診斷:膝痹病(肝腎虧虛、瘀血痹阻證)。治法:補腎壯骨,祛瘀除痹。藥用:熟地黃15 g,伸筋草15 g,蒼術15 g,澤瀉15 g,澤蘭15 g,五加皮15 g,赤芍15 g,丹參15 g,骨碎補20 g,豨薟草15 g,續斷15 g,薏苡仁20 g,蜈蚣2 條,制附子15 g(先煎),肉桂10 g,淫羊藿30 g,巴戟天20 g,雞血藤30 g,乳香15 g,沒藥15 g,木瓜15 g,吳茱萸9 g。7 劑水煎服,日1 劑,早晚各服1 次。另加熏洗Ⅱ號(院內制劑)7 袋外敷。
2019 年12 月4 日二診:服上方7 劑及外用藥后,小腿已無痙攣,雙膝關節疼痛緩解,腰膝酸軟減輕,腫脹明顯減輕,行走有力,下肢怕涼癥狀緩解,但夜間疼痛時有發生,爬樓梯仍受限。在上方的基礎上去木瓜、吳茱萸加土鱉蟲9 g,地龍9 g,海螵蛸30 g(先煎)以活血祛瘀,7 劑水煎服。另加熏洗Ⅱ號(院內制劑)7 袋外敷。
2019 年12 月28 日三診:服二診方14 劑后,膝關節腫脹消失,腰膝酸軟明顯減輕,膝蓋疼痛明顯減輕,行走正常,雙下肢已不怕涼,囑患者繼服二診方7 劑,煎服法不變,以鞏固療效,并囑其避風寒, 注意保暖,適當進行功能鍛煉。
1 個月后患者就診,訴上述癥狀基本消失,囑服院內制劑“骨痹止痛丸”以善后,3 個月后隨訪,病情未再復發。
按:本例患者因年老體衰,腎虛髓空無以養骨,肝血虛不能濡養經筋而致膝骨性關節炎,遂用制附子、肉桂、淫羊藿、巴戟天增補命門之火,熟地黃、骨碎補益精填髓,赤芍、丹參、蜈蚣搜刮絡中瘀血,乳香、沒藥行氣止痛,雞血藤、伸筋草、豨薟草疏通經絡、通利關節,蒼術、澤蘭、澤瀉、薏苡仁清利水濕、消腫止痛,木瓜、吳茱萸舒筋活絡,諸藥合用共奏補腎壯骨,舒筋祛瘀之功效,并囑患者外敷熏洗Ⅱ號解凝除痹,一診效果顯著。二診患者膝關節夜間疼痛無明顯緩解,瘀象明顯,故在一診的基礎上加用土鱉蟲、地龍增強活血祛瘀之力,邪去正自安,并重用海螵蛸修復退變的關節軟骨。三診患者癥狀基本消失,繼服二診方7 劑鞏固療效并善其后。縱觀整個治療過程,劉柏齡以補腎壯骨治其本,活血祛瘀治其標,攻補兼施,治療后病情穩定,療效顯著。
4 小結
國醫大師劉柏齡認為,風、寒、濕等外邪侵襲雖為膝骨性關節炎發病的誘因,但正氣不足實為本病發病的主要內因,而肝腎虧虛尤為重要,本病病位在肝腎,多為本虛標實之證。本病病程較長,纏綿難愈,瘀血是本病的病理關鍵。在治療上,劉柏齡著重補肝腎、溫腎陽,并輔以祛瘀除痹,補腎祛瘀法貫穿整個療程的始終,臨證時辨證加減用藥,善用重用海螵蛸以及蟲類藥、藤類藥祛瘀除痹,在內服中藥的同時兼用外治法,同時強調應配合功能鍛煉,減少膝關節負重,避免對膝關節過度勞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