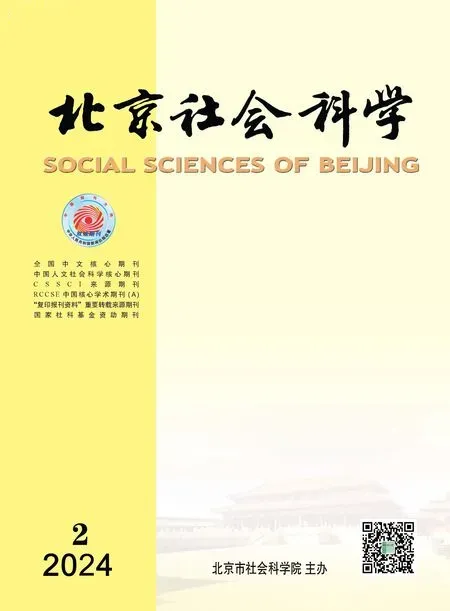單位犯罪教義學的兩個問題
時延安
一、引言
目前,刑法教義學體系中并沒有單位犯罪的獨立位置。在不承認法人犯罪的國家,如德國,其刑法理論體系并無法人犯罪的地位。而我國雖然規定有單位犯罪,在刑法理論體系中并沒有強調單位犯罪的特殊性,只是與自然人主體一樣在犯罪主體①或者行為主體②中加以討論。這主要是因為,研究者多數仍然是從自然人的角度理解單位犯罪的行為和罪責問題,認為單位的犯罪行為不可能脫離自然人的行為,單位決策者即自然人的意志就可以理解為單位的意志,相應地,也就為單位確立了罪責的基礎。這樣簡單化的理論體系“處理”,實際上抹殺了單位犯罪及單位承擔刑事責任的特殊性,也忽視了規定單位犯罪的刑事政策意義。同時,刑事司法實踐中處理的單位刑事案件主要涉及民營企業,而這類企業的經營管理多由企業負責人或者實際控制人“做主”,這也就使得對單位的刑事責任追究與對自然人的刑事責任追究結合起來考量。相應地,現行刑事訴訟法也將單位刑事案件的處理與單位中自然人刑事案件的處理“捆綁”起來,在程序設計上對前者的處理從屬于后者。
這就產生了一個需要迫切回答的問題:在刑法理論體系中應否將單位犯罪作為一個相對于自然人犯罪獨立的范疇進行分析和研究?進言之,應否構建相對獨立的單位犯罪教義學?顯然,無論從刑法學理論體系自我完善的角度,還是從適用刑事實踐的角度,乃至從完善刑事訴訟制度的角度,都有必要認真考慮這個問題,并給予確切的回答。
二、對法人進行刑事制裁的正當性
一般情況下,當某一主體應受到刑事制裁時,會被認為其實施了刑法所規定的危害行為,且應當受到譴責。那么,對于法人而言,如果認為其應當受到刑事制裁,也就需要考慮三點:一是法人是否具有人格,即是否具有獨立的法律地位、能夠以自己的名義開展活動且自己承擔行為后果的資格?二是法人是否具有刑事責任能力?三是法人是否具有獨立承擔刑事譴責的可能性?只有對這三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才可以認為對法人進行刑事制裁具有正當性。本文從以下三個角度進行分析。
(一)從民法角度思考法人的人格
我國民法理論通說認為,法人和自然人同為獨立的民事主體,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即基本上采取“實在說”的立場[1],而在商法學中討論的大多數法律問題都是圍繞著法人展開的。由是可見,在民商法理論中,法人有其特有的人格及法律所規定的各項權利和義務,并能夠以自己的名義從事相應的民商事活動,且根據法律規定以其財產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民商法中確定法人具有獨立的人格和獨立的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并不能當然地推導出法人的刑事責任根據。不過,民商法對法人人格的確立,對法人刑事責任能力的證成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它為對法人進行評價和譴責提供了基礎;另一方面也為使其獨立承擔刑事責任提供了條件。更為重要的是,當學說上一般認為法人的人格獨立于自然人時,也就為法人獨立承擔刑事責任提供了一個“前置法”上的前提。在民法上承認法人的獨立人格,在刑法上自然要接受這個結論,因為刑法并沒有確認某一主體人格的功能。因此,在民法上承認法人具有人格,在刑法上也就不能否認法人不具有人格。
(二)從民事行為能力推論法人的刑事責任能力
民商法學中并沒有“民事責任能力”這一術語,這可能是因為,對民事責任概念的界定強調的它是一種不利后果,而民事行為能力本身則涵蓋了民事主體承擔不利后果的能力。比較而言,刑法中所說的刑事責任能力,實際上也是一種行為能力或者犯罪能力。我國刑法通說認為,刑事責任能力,是行為人構成犯罪和承擔刑事責任所必需的,是行為人具備的刑法意義上的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從這一定義中可能看出,刑事責任能力的本質就是一種行為能力或者說是一種犯罪能力。不過,刑法通說中所說的刑事責任能力帶有明顯的“自然人視角”。如果借用民事行為能力的視角來分析,對行為能力的性質界定,重點在于強調行為主體的自我決定及其法律意義。那么,對刑事責任能力概念的內涵界定,也應當強調行為主體自我決定其行為的能力及在刑法上的意義。從這一內涵界定展開,法人并不具有等同于自然人的刑事責任能力,但卻具有自我決定如何行為的能力,而這種自我決定以及由此做出的行為,會在刑法上產生評價乃至給予譴責的意義,因而也就可以認為法人具有刑事責任能力。
(三)對法人實施嚴重危害行為的譴責問題
刑事制裁本身是一種不利的法律后果,其內容表現為對犯罪人基本權利的限制和剝奪,而刑事制裁的前提則是對犯罪人人格的否定性評價及譴責。這一前提,在我國刑法理論中就是刑事責任的范疇。對于刑事責任的實質,高銘暄教授指出,它是統治階級通過國家司法機關對基于個人自由意志實施違反統治階級利益的行為的人所做的一種否定性評價。[2]以這一界定為學理根據,對犯罪人的刑事制裁一方面是其實施了一定的危害行為,另一方面則是其應受到否定性評價。由此展開,對犯罪人人格的否定性評價及譴責,是對犯罪人進行刑事制裁的根據。那么,否定性評價及譴責的內容又是什么呢?同樣,從上述界定出發,其內容應當是犯罪人人格中表現出反社會的人格傾向,即對現行統治秩序的反對態度。刑事責任范疇的核心功能就是判斷犯罪人是否具有這種傾向及程度。如此,也可以大致厘清,行政制裁與刑事制裁的差異所在,即前者并不強調對違法行為人反社會人格傾向的判斷。
在承認單位具有人格的前提下,犯罪單位承擔刑事責任,也應對其人格進行否定性評價。不過,對于犯罪單位人格的反社會傾向如何理解,卻是一個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我國刑事責任理論的哲學基礎認為,行為人具有相對的意志自由,只有當行為人有選擇合法行為的可能卻選擇違法行為時,才有對其譴責的合理性,而只有當行為人選擇犯罪行為時,才有對其人格中的反社會傾向進行否定的合理性。單位作為組織體,并沒有等同于自然人的意志自由;單位如何選擇行為,是其決策機構中自然人的合意或者代表人的意志所決定的。對于單位而言,決策機構中自然人的意志決定從效果上也就是單位的意思表示,從而看起來好像對單位犯罪的譴責與自然人的譴責不可分離。不過,當我們將單位看成一個獨立的存在時,單位意思表示的形成機制更為重要,即多數自然人的合意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為什么在單位做出違法乃至犯罪的決定時,該單位內部沒有有效的機制進行糾正并促進其合法經營。由是以觀,單位人格的反社會傾向在于其內部治理結構存在著重大問題,以至于單位不能做出合法的意思表示、實施合法的行為。
總之,單位人格的特殊性實質上決定了對單位承擔刑事責任的哲學根據不是其具有相對的意志自由,而是其內部治理結構存在著弊端,因而對犯罪單位的譴責不是聚焦在其內部的自然人,而是聚焦在其內部的治理結構。
三、組織體責任論的內涵應從“單位是規則組織體”來認識
川崎教授提到了三種學說,即企業組織體責任論、單位行為責任說(即等同路徑)和組織模式說。企業組織體責任說,是將單位等企業組織的自然人行為視為企業組織體的活動;單位行為責任說,是將單位代表的意思和行為視為單位的意思和行為。這兩種理論,實際上都是將特定自然人的行為視為或者等同于單位的行為,進而為單位追究刑事責任提供立論基礎。川崎教授將這兩種學說稱之為個人模式,這與英美刑法有關替代責任(vicarious liability)和同一視原則(identification principle)具有相通之處。組織模式說,則嘗試將單位中自然人的刑事責任與單位的刑事責任區分開來,以單位的法律義務為著眼點,認為這類義務的負擔才是單位所具有的,當單位違反義務而形成法益侵害時,就為追究其刑事責任奠定了基礎,由此也將合規計劃及其實施納入承擔刑事責任的考量。在主張組織模式說的同時,他也不否定個人模式,即采取并用的觀點。采取并用的觀點,確實是一個比較折中但又務實的路徑:采取個人模式,可以較好地解決中小規模企業的刑事責任根據問題;采取組織模式,則可以較好地解決大規模企業的刑事責任根據問題。不過,從現實及發展的眼光看,單位犯罪采取組織模式說更為妥當,在我國刑法學語境中對應著組織體責任論。
(一)我國刑法對單位犯罪的規定及司法實踐實質上對組織體責任論的貫徹
我國規定單位犯罪最早可追溯到1987年的《海關法》。將單位規定為犯罪主體,是有很強的集體主義色彩的,因為當自然人為了單位利益且基于單位集體決策的情況下實施犯罪時,讓自然人為集體承擔刑事責任是不公平的,而單位作為一個集體有其特殊的“人格”,因而可以也應當規定為犯罪的主體。也因為如此,在一些犯罪(如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單位行賄罪)中,對單位中自然人(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的法定刑要低于自然人犯罪的法定刑。在定罪量刑標準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通過司法解釋對自然人犯罪和單位犯罪也確定了不同的數額、數量標準。
在學理上,源自英美的替代責任理論和同一視作為學說被引進,但一般認為,這兩種理論無法解釋我國刑法有關單位犯罪的規定;如果考慮到單位犯罪立法背景所具有的集體主義考量,那么,我國單位犯罪的立論基礎應更接近于組織體模式。對單位犯罪成立要件的判斷,強調三個特征:單位名義;單位意志;單位利益。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由于大量的犯罪單位是中小規模的民營企業,而這類企業通常都是負責人決策(即便其采取公司化的方式),因此,對單位犯罪成立的判斷就轉變為“單位名義+單位利益”,在一些極端的情況下,一些法院甚至只考慮將“單位是否從犯罪中獲益”作為最重要的判斷根據。司法實務中之所以有意無意地忽視“單位意志”的判斷,筆者認為,在很多情況下是因為難以區分是單位中自然人的意志還是單位的意志,所謂單位的意志往往是模糊和不確定的。
在合規話題引入中國刑法學視野之前的十年多時間里,對單位犯罪的研究乏善可陳,而恰恰是在合規理論引入之后,中國刑法學界開始重新思考單位犯罪的責任根據問題。例如,黎宏教授系統而深入地論證組織體責任論。[3]與黎老師觀點相似,劉艷紅教授提出合規責任論[4],王志遠教授提出,要超越行為責任,提升單位犯罪采取歸咎的刑事責任說[5],兩位教授提出觀點的基礎仍是組織體責任論。學說上確立組織體責任論的地位,相應地也就會在單位犯罪解釋論上形成一系列應然的結論,甚至也為刑事訴訟法中設立相對獨立的單位刑事案件處理程序提供了實體法上的理論根據。[6]從以上關于法人人格、刑事責任能力和刑事可譴責性的分析,就會得出單位刑事責任應采取組織體責任論,也就是說,無論將民法理論作為論述的前提,還是從對單位進行刑事譴責的必要性及根據來看,都會將單位區別于自然人來看待,并脫離自然人的意志自由來討論單位的刑事責任根據問題。
對單位類型的理解和觀察,對研究者在單位犯罪刑事責任問題上采取何種立場產生了一定影響。以企業為例,我們觀察不同規模的企業會有不同的認識,如果將眼光放在中小規模企業,尤其是靠家族創業、經營的企業,會很容易將企業與自然人結合起來,在理論上也會傾向于選擇從自然人的角度觀察、理解企業的刑事責任問題;反之,如果將眼光聚焦在已經實現現代企業治理要求的企業時,則很容易將企業理解為一個脫離于自然人的獨立主體來看待,在理解其刑事責任時會更多地從一個獨立的組織體來看待。對待企業犯罪,采取一種向前看的思路更好,就是從現代企業制度來理解企業活動和其承擔法律責任的根據。
(二)組織體責任論的“內核”應采取規則組織體的觀念
黎宏教授認為:“單位是由人和物復雜結合而成的法律實體,具有自己獨特的制度特征、文化氣質和環境氛圍,這些要素能夠對單位中的自然人的思想和行為產生影響。”單位犯罪的刑事責任根據應采納組織體責任論,根據這一認識,組織體責任論的“內核”包括三個方面,即制度、文化和環境。據此推論,這三方面的共同作用會影響單位中自然人的行為,而“單位的制度、氛圍或者說氣質,若容許或默認犯罪的發生,或者在防止犯罪方面措施不力,便可將其作為引致該單位成員犯罪的條件或者原因,此種場合下的單位成員個人犯罪可以被視為單位自身的犯罪”[3]。這一帶有擬人化的觀點,對于理解單位犯罪中自然人行為如何能視為單位行為具有積極意義。不過,諸如文化、氣質、環境等在實踐中難以判斷,例如,如何基于企業文化來判斷是企業文化促成了單位中自然人實施了犯罪行為?在我看來,包括企業在內的單位可能是一個帶有特殊文化或者氣質的組織體,但更是按照各種規則構建起來的一個規則組織體。既然如此,我們在理解單位的刑事責任時就要考慮其作為規則組織體的意義。
單位作為一個組織體,實質上是一個依靠規則構建的組織體。對此,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一是,單位的人格是從依法設立時開始的,從《民法典》第58條有關法人的規定即可略見一斑。進言之,單位的成立條件、程序均由法律、行政法規確定,其成立需要得到有權機關的批準。二是,單位享有的權利和義務均源自法律,其享有的權利類型和義務類型明顯區別于自然人。三是,單位內部人員之間及單位機構的職權等依照法律和其章程確立,其內部是依靠規則運行的;單位對內、對外的意思表示,都是根據這套規則而產生的。實踐中常說的“家族企業”,其內部也是依靠規則,只不過這種規則并非法律所認可的規則。認識到單位是一個規則組織體,認識到其是依靠一套規則運轉的,那么,在認識其人格、意思表示及行為時就會認識到規則對于單位內部管理、外部行為的意義。當我們對一個實施犯罪的單位進行譴責時,不是因為它是個“壞”單位、沒有“良知”的單位,而是支持它內部運轉、運營的規則以及由此建立機制是易生成違法行為的、是具有明顯的危險性的。所以,對單位刑事責任的理解,不能類比自然人、從人的意志自由來進行分析,而是應當考慮其作為一個由人組成的組織體、一個規則的組織體,從其內部治理結構及運行機制的違法傾向以及社會危險性來進行理解。
(三)從合規的視角理解單位犯罪
川崎教授在演講結束部分提到,“不將合規體制的建立視為法人固有的注意義務,而僅將其視為刑事政策視角下作為激勵措施的免責事由,這也是一種可行的選擇。”從這句話來分析,合規體制的建立對法人犯罪是否成立的影響,存在著兩條可供選擇的路徑,即從是否履行注意義務的角度切入和將其作為法人犯罪的責任阻卻事由看待。就第二條路徑來講,單位既然是一個規則組織體,當其已經建立合法合規的內部治理結構和運營機制即已經建成合規體制的話,該單位也就不再具有應譴責性的可能,因而有效的合規體制可以作為單位的責任阻卻事由。這條路徑是可行的。不過,在罪責部分討論合規問題,在單位犯罪成立的判斷流程設計上可能過于滯后了,更為妥當的思路還是在構成要件的適格性階段進行判斷。
我國刑法中的單位犯罪(除合同詐騙罪)幾乎都是法定犯,其行為構成犯罪的第一個要件就是,單位是否違反了行政法或者民商法所規定的強制性義務,個別情況下也包括合同義務。當單位沒有違反義務或者屬于行使權利,或者具有民商法上的免責事由時,就不成立犯罪。[7]既然有效合規建設本意首先就包含了守法的意思,當單位已經建立有效合規后,就認為其已經履行了法律義務,這種情形導致危害后果發生的自然人行為,就只可能構成自然人犯罪。例如,涉案企業已經建立有效的環境合規體制,其工作人員違背企業規定擅自非法處理污染物的,就只應追究該自然人的刑事責任。
四、結論
本文僅僅討論了單位犯罪教義學的兩個基本問題:其一,結合我國單位犯罪理論與司法實踐,論證法人刑事制裁的正當性,肯定其在刑法上的獨立人格,進而指出單位人格的特殊性決定了對單位承擔刑事責任的哲學根據不是其具有相對的意志自由,而是其內部治理結構存在著弊端。其二,對單位刑事責任的歸責采取組織體責任論,其“內核”應采取規則組織體的觀念,從合規角度理解單位犯罪。對于單位犯罪的完整理論體系構建,還有很多工作要完成,本文期冀能夠將以上兩個問題解釋清楚,為單位犯罪教義學打下最為重要的基礎,循此實現單位犯罪的理論與實踐完善。
注釋:
① 采犯罪構成理論的教材,都是在犯罪主體中予以討論。例如,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第八版)[M].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102.
② 采犯罪階層理論的教材,則在構成要件中行為主體部分討論。例如,張明楷著.刑法學(上)(第五版)[M].法律出版社,2016: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