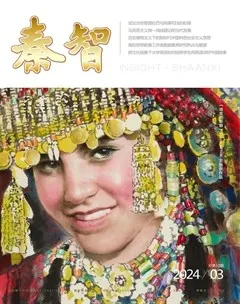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適用實證研究
[摘要]當前犯罪形式日新月異,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在打擊新型疑難犯罪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但是,司法實踐表明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的司法適用存在難題。本文通過分析2021-2023年60篇與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措施有關的裁判文書得出,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在適用過程中存在證據(jù)適用標準不統(tǒng)一、證據(jù)出示不規(guī)范、非法證據(jù)排除困難等問題。為了使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更好的發(fā)揮作用,有必要對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的適用加以規(guī)范,具體而言包括明確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的適用范圍、出示程序,完善非法證據(jù)排除規(guī)則等。
[關鍵詞]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非法證據(jù)排除;程序控制
[中圖分類號]D915.2? ? ? [文獻標識碼]A
[DOI]:10.20122/j.cnki.2097-0536.2024.03.009
一、研究背景
2012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刑事訴訟法》)在第152條首次對技術偵查證據(jù)的法律地位和效力作出了認定。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頒布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對技術調查、偵查證據(jù)的審查與認定作了進一步規(guī)定。然而,受“偵查秘密主義”、技術偵查證據(jù)本身特性等因素的影響,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在移送、出示、質證、非法證據(jù)排除等方面的適用效果并不理想。
本文通過分析2021—2023年與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有關的裁判文書,揭示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的適用現(xiàn)狀,探尋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措施在實踐中出現(xiàn)的問題,進而提出對策建議,為我國技術偵查制度的完善添磚加瓦。
二、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適用現(xiàn)狀分析
為了明確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在司法適用中出現(xiàn)的問題,進而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筆者通過“中國裁判文書網”對2021年—2023年與本文研究相關的裁判文書進行了篩選。排除掉96篇屬于隱匿身份偵查與控制下交付的案件、沒有將技術偵查材料作為證據(jù)使用的案件以及類似的案件,最后得到與本文研究相關的裁判文書共60篇。
(一)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總體適用情況
1.大多適用于毒品犯罪案件
該60篇裁判文書共涉及8類犯罪,包括:毒品犯罪、走私犯罪、貨幣犯罪、賭博犯罪、財產犯罪、人身犯罪、電信網絡犯罪和妨害司法犯罪。其中毒品犯罪37件,占比61.7%。因此,毒品犯罪是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的主要適用類型。
2.大多適用于重罪案件
從案件數(shù)量上看,有10件案件對被告人判處了不滿3年有期徒刑,有42件對被告人判處了3年以上有期徒刑,有8件根據(jù)罪行輕重對共犯判處了不同程度的刑罰。從刑罰人數(shù)上看,對52人判處了不滿3年有期徒刑,對65人判處了3年以上不滿10年有期徒刑,對51人判處了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由此可見,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大多適用于重罪案件。
3.大多適用通信監(jiān)控和行蹤監(jiān)控措施
在60份裁判文書中,提及通信監(jiān)控措施的案件有28件,提及行蹤監(jiān)控的案件有7件,提及記錄監(jiān)控和場所監(jiān)控的案件各1件,其余案件由于裁判文書中沒有提及,故無法得知采取了何種監(jiān)控措施。由此可見,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的取得大多來自通信監(jiān)控和行蹤監(jiān)控。
(二)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適用具體情況
1.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的出示
根據(jù)出示形式的不同可將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的出示分為出示原始證據(jù)、翻音材料和情況說明。翻音材料是對原始證據(jù)進行整理得到的文字材料。情況說明是對原始證據(jù)主要信息的描述。[1]在60個案件中,明確指出出示原始證據(jù)的案件有7件,如:陳某等走私販賣毒品案中,通過出示音頻光盤證明被告人通過手機通話販賣毒品的事實。出示翻音材料的案件有17件,出示情況說明的案件有25件。由此可見,出示原始證據(jù)的案件較少,出示情況說明的案件較多。
2.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的質證
首先,在辯方是否提出質證意見方面,有10個案件辯護方提出了質證意見。其次,在辯方提出質證意見的內容方面,大多是對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的合法性提出異議,對證據(jù)的關聯(lián)性和客觀性提出異議的較少。如:在廖某華、王某走私販賣毒品案中,辯護方認為技術偵查措施的適用沒有事先獲得批準,因此通過該方式獲取的技術偵查證據(jù)屬于非法證據(jù),應當予以排除。
3.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的采信
根據(jù)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技術偵查證據(jù)的調查核實方式有三種,當庭核實、采取保護性措施后的核實以及庭外核實。[2]在收集的60個案件中,大部分都是采用當庭核實的方式采信技術偵查證據(jù),只有1個案件明確說明通過庭外核實的方法核實證據(jù)。在技偵證據(jù)是否采信方面,法院一般會采信技術偵查證據(jù)。在收集的60個案例中只有1例法院沒有采信技術偵查證據(jù)。如在王某利販賣毒品一案中,法院認為本案中偵查機關沒有隨案移送技術偵查的法律文書,且文字材料缺乏對應的音頻資料,無法確定技術偵查資料的真實性,故對該技術偵查證據(jù)不予采信。
三、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適用存在的問題
通過分析60個案例可以看出,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措施在適用中存在適用標準不統(tǒng)一,證據(jù)出示不規(guī)范,非法證據(jù)排除困難、權利救濟機制缺失等問題。
(一)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適用標準不統(tǒng)一
根據(jù)相關法律規(guī)定,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措施只適用于嚴重危害社會的重大犯罪。然而司法實踐中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措施已經成為了偵查機關常用的辦案手段。[3]在駱某軍盜竊案中,被告人凌晨進入被害人的出租房,盜走受害人價值4031.67元的手機和2000元現(xiàn)金。隨后公安機關通過技術偵查手段對被盜手機進行定位并以此抓獲了犯罪嫌疑人。駱某軍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4000元。但是該犯罪并不屬于法律規(guī)定的嚴重危害社會的重大犯罪。
(二)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出示不規(guī)范
相較于出示翻音資料或情況說明,出示原始資料更具有真實性、客觀性,因此應當以出示原始證據(jù)為主。然而在60個案件中明確出示原始資料的案件僅有7件。大多數(shù)案件中控方只出具了情況說明、辦案說明等文字性材料。雖然出示概括性的文字材料可以提高庭審的效率,但是也造成了技術偵查證據(jù)后續(xù)的形式化,給庭審的程序正義帶來了困擾。[4]
(三)質證過程非法證據(jù)排除困難
通過分析上述案件可以得出,在質證過程中很少有辯護律師申請排除非法證據(jù)。在上述60個案件中僅有10件案件辯護律師對技術偵查證據(jù)的合法性提出了異議,其中只有3個案子的辯護律師請求排除非法證據(jù),占比僅為5%。此外,法院在面對非法證據(jù)排除申請時對爭議證據(jù)的合法性難以進行有效的審查。如在廖某勇、王某走私販賣運輸毒品一案中,法院僅以廖某華實施的是重大毒品犯罪,偵查時機稍縱即逝,采取技術偵查手段具有正當性為由對辯護方的意見不予支持,顯然說服力不足。
(四)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權利救濟機制缺失
技術偵查措施在實施過程中極易侵犯相關人員的權利,但法律對侵犯有關人員權利時如何救濟并沒有作出明確的規(guī)制,這無疑不利于當事人的權利保障。
四、完善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適用對策建議
為了規(guī)范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的適用,發(fā)揮技術偵查制度的效用,應當針對上述問題提出行之有效的對策建議。
(一)明確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的適用范圍
適用技術偵查措施時應遵循最后使用原則,即,只有當其他偵查手段不足以懲治犯罪時,才能啟動技術偵查措施。[5]此外,法律規(guī)定技術偵查措施只適用于重大犯罪,但是對于何種程度才算重大犯罪并沒有作出規(guī)定。法律應當明確規(guī)定以何種法定刑為節(jié)點,當犯罪程度達到法律規(guī)定時,方可適用技術偵查措施,以此規(guī)范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的適用。
(二)規(guī)范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的出示程序
首先,應當明確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的出示內容。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不同于通過常規(guī)偵查方式獲取的證據(jù),該種證據(jù)的取得往往涉及國家保密技術,具有秘密性。[6]因此,應該把握好出示的內容。一方面,為了保證程序正義應當讓更多的證據(jù)以原始形式接受控辯雙方的當庭質證;另一方面,技術偵查證據(jù)的出示不能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即,除了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和泄露特殊技術手段的證據(jù)都應當當庭出示。
其次,應當盡量出示原始材料。原始證據(jù)不宜被篡改、扭曲,更能保證證據(jù)的真實性、客觀性和合法性。去掉敏感信息后可以當庭出示的原始材料應當當庭出示,如果出示原始證據(jù)有泄露技術手段的風險,則可以通過翻音材料出示,但是法官應當核實原始材料的真實性。
(三)規(guī)范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非法排除規(guī)則
技術偵查證據(jù)的特殊性決定了偵查部門在很多情況下會以保密的理由拒絕公開技偵證據(jù),一般是通過情況說明將技術偵查證據(jù)提交給法庭,在此種情況下,即使技偵證據(jù)在收集過程中有違法行為,也很難被發(fā)現(xiàn)。一方面,法院是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的非法排除主體,應當對技術偵查證據(jù)進行詳細審查。技術偵查證據(jù)的核實方式有常規(guī)方式、保護性措施和庭外核實。此三種方式在適用時應當存在順位,常規(guī)方式優(yōu)先,必要時采取保護性措施核實,情況特殊時才可進行庭外核實。[7]另一方面,技術偵查措施適用不當會給相關人員的權利帶來嚴重的侵犯,因此不同于普通偵查措施的排非規(guī)則,對技術偵查證據(jù)的排非程序應當更加嚴格,對于違反技術偵查審批程序、案件適用范圍、技偵使用期限等規(guī)定的,均應排除。
(四)完善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權利救濟機制
當前我國法律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違法行使職權或者存在過錯給當事人的權利造成損害如何救濟作出了規(guī)制,如國家賠償、復議、申訴等,但是相關法律并沒有對技術偵查領域侵權如何救濟做出規(guī)制。[8]技術偵查措施的司法適用現(xiàn)狀急需法律對此作出回應。首先,在立法層面,應當細化法律規(guī)定,將技術偵查明確規(guī)定到國家賠償、復議等的救濟范圍中。在司法層面,應當完善當事人權益受侵害時的控告和申訴機制,國家有關機關應當為此提供便利。
五、結語
隨著科技的發(fā)展,犯罪形式愈加復雜化、科技化和智能化,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在打擊此類犯罪中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技術偵查是一把雙刃劍,使用不當便會給當事人的權利造成重大損害,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在司法適用中出現(xiàn)了一系列問題,這對公民的權利保障造成了威脅。因此有必要對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的適用予以規(guī)制,使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更好的發(fā)揮作用。
參考文獻:
[1]程雷.技術偵查證據(jù)使用問題研究[J].法學研究,2018,40(5):153-170.
[2]董坤.論技術偵查證據(jù)的使用[J].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3):151-160.
[3]田芳.技術偵查中個人信息保護的法理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
[4]劉梅湘,李真.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運用問題研究[J].證據(jù)科學,2022,30(1):83-96.
[5]李東春.淺析在職務犯罪偵查中采取技術偵查措施[J].湖南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0,22(5):136-138.
[6]朱孝清.試論技術偵查在職務犯罪偵查中的適用[J].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4(1):111-116.
[7]艾明.論技術偵查證據(jù)庭外核實的性質調整與程序完善——以2021年《刑訴法解釋》為中心的考察[J].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6):130-143.
[8]蔡藝生,楊帆.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措施適用實證研究——以2019-2021年425份判決書為主要分析樣本[J].山東警察學院學報,2022,34(3):65-71.
基金項目:青海民族大學研究生創(chuàng)新項目,項目名稱:監(jiān)控類技術偵查證據(jù)適用實證研究(項目編號:04M2023089)
作者簡介:汪龍貞(1998.6-),女,漢族,山東臨沂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刑事訴訟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