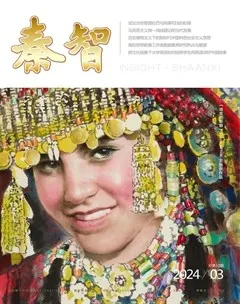中學課程中“兩門歷史科”的特點與差異

[摘要]香港在中學課程設置中設有兩門名稱類似、課程目標卻截然不同的歷史課程,“歷史”和“中國歷史”展現了完全不同的歷史觀、教學目標和評估方式。基于香港文憑試的試卷分析,本文探討了香港兩門歷史科目的差異,剖析在試題中所呈現的諸多問題,提出針對課程教學問題的改善意見。
[關鍵詞]中學歷史科;香港中學教育;中學文憑考試;試卷評析
[中圖分類號]G633.51 ?????[文獻標識碼]A
[DOI]:10.20122/j.cnki.2097-0536.2024.03.049
引言
在香港的中學課程中,存在兩門名稱相似的歷史課程——“歷史”與“中國歷史”,然而其課程內容與課程目標卻截然不同。在同一個國家,歷史課程的課程內容、歷史取向應該是保持一定的,但在香港的這兩門課程中不僅課程內容明顯不同,還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歷史觀、教學目的以及評核方法。
對于香港歷史課程的兩種歷史觀,學者維克斯(Vickers)曾通過他的文章做了相關分析,然而在其中卻缺失了對于試卷內容的分析。一門科目的考核方式會影響教師的教學方式,從而影響到課程發展和課程設計,最后反饋到學生學到的知識內容,這便是所謂的回流效應(Backwash effect)。由于回流效應的存在,試卷及考題分析會間接但更直觀地反映課程的現狀,因此在考察學科知識時關注“考什么”會比“教什么”更重要。在維克斯及回流效應視角下,本文研究將重點放在香港的文憑試考試,試圖從試卷分析出發,探索兩種歷史課程的不同命題取向。
一、有關香港歷史科的研究基礎
維克斯認為“中國歷史”偏重于用中文授課,更強調中國古代史以及中國傳統的文化價值觀、道德教育觀,價值觀多推崇“中國特色”的價值體系,為國家歷史觀服務;在講述歷史事件時多強調英雄人物,主要集中于對政治史的考察,而在考核模式方面更偏重于數據記憶。反觀“歷史”,作為英國歷史課程的舶來品,其主要授課語言通常為英語,接受英國的歷史教學模式以及歷史觀,其價值觀服務于香港地區;關注世界文明、國際文化、宏觀歷史,考察學生的思維能力。雖然對于“一國兩制”下的教育體系,有學者認為可以依據“全球—國家—地方”的分析框架進行解構和分析,但兩門歷史科目的設置卻混淆了全球、國家和地方的觀念,尤其“歷史”既缺失了本應固守的國家視角,又過分強調了西方的歷史邏輯。因此,在維克斯的分析基礎之上,本文重點關注香港兩門歷史課程的試卷,剖析其中的不同之處。
二、香港中學文憑試概述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簡稱文憑試)是為配合新高中學制而由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簡稱香港考評局)舉辦并設立的全港性公開考試,其成績可以用來報考并學習4年制大學學士學位課程或兩年制副學位課程,因此已成為香港教育考試的代表。
文憑試的甲類科目共有24科,包括4門核心科目(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及通識教育)和20門選修科目,選修科目歸類為多個學習領域,包括“語文教育”“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科學教育”“科技教育”“藝術教育”及“體育”;甲類科目不同于乙類的應用學習科目,需要設立公開考試。在本文中,筆者欲關注甲類科目中屬于選修科目的“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領域的“歷史”和“中國歷史”科。
三、文憑試中的考生表現與試卷設計差異
文憑試中屬于中四及中六(高中)考察范圍的“中國歷史”和“歷史”均屬于選修科目,從2012年文憑試的首屆考試開始,這兩門科目大體保持著報考人數較低的趨勢;其中,每一年的“中國歷史”報考人數均高于“歷史”報考人數。,。
從兩門科目的內容側重、試卷的資料運用與學生在答題時所表現出的能力差異來看,“歷史”較為關注中國與世界史的比較與關系分析,而“中國歷史”則僅關注本國史;在“中國歷史”試卷中,每份資料下方都寫明了確切的作者與專著,而在“歷史”試卷中其資料出處則非常模糊;此外,選修“中國歷史”的學生,在讀圖能力方面稍遜于選修“歷史”的學生。
(一)內容側重
在“中國歷史”試卷中,由于教師在教授中國歷史學生學習知識時,將中國史和全球史相剝離,因此考生在涉及到最基本的外國史知識時,犯了一些非必要的錯誤。例如2016年試卷的試卷一第六題,頗多考生不熟知資料所指的“美利堅合眾國”是美國,寫成了“美利堅”“合眾國”“國聯”或“聯合國”等,其反映了“中國歷史”考生對于國外基本歷史知識的缺失以及對全球史的忽視。
(二)試卷的資料引用
通過對“中國歷史”和“歷史”試卷的比較,其最明顯的區別表現在對試卷中史料來源的標注,在“歷史”試卷的材料上方,常會出現“某、取材自、選自、發表于”等詞;而不是如“中國歷史”試卷一樣,在材料下方寫明具體圖書名稱及作者。
雖然“歷史”要求學生具備辨別或解釋,或恰當選用及組織史料的能力,但在選取史料的過程中,試卷本身沒有對史料做系統地甄選與基本信息的呈現。參考劍橋IGCSE歷史考試中關于學生要“說明對資料來源的解釋和評價”的評價目標,其提到在學生解釋和評價資料時,要“確定該史料在多大程度上有用”“它有多可靠”“它的限制是什么”“它是什么類型的來源”“內容創建者的重要性”等等;但如果在出題時未提供史料類型與引用信息,學生就無法繼續判斷其“可靠性”。因此,在資料的引用方面,“歷史”試卷的資料引用格式略顯特別。
(三)學生讀圖能力的差異
在學生的答題表現中,選修“中國歷史”的考生表現出了較薄弱的讀圖能力;而反觀“歷史”考生,他們在讀圖方面的表現總體上良好。不同于“中國歷史”考題中對獨立圖片的解讀考察,“歷史”試題中雖然有些題目也會考察讀圖能力,但其主要以文字為主、文字下方的圖片為輔;其不以解釋圖片為主,而圖片僅作為對文字的具象化表現。
“中國歷史”考生在審題時會忽略題目設問中的關鍵詞,有時在閱讀圖像時無法做到圖像中的“圖片與文字的結合”。2016年試卷一第一題中b(iii)的題目為“資料四的兩張海報分別反映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哪兩項發展重點?試援引史實,闡述與兩張海報相關措施的內容。”在這一題中,很多考生只對海報中重工業的發展略有認識,而沒有抓住題目中所列明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關鍵詞以至于誤答;還有考生多把焦點放于海報圖像,沒有注意海報的文字描述,因此忽略了重要訊息,同樣導致誤答。
對于造成“中國歷史”考生讀圖能力薄弱的原因,可歸結于如下幾個方面:一是由于歷史知識積累不足,因此在面對圖片時知識與插圖出現斷層,不能夠有效地從圖片中提取信息;二是圖文結合能力薄弱,無法做到圖片與圖片中文字的雙向結合,因此無法閱讀出其中的關鍵信息;三是讀圖能力的不足,在面對圖片時無法把握圖片的全局并分析出圖片中的有用信息,因此觀點有失偏頗;四是審閱和理解試卷設問的能力不足,導致答題時的分析未涵蓋題目所示的內容與知識范圍。
結合比較“中國歷史”和“歷史”考生的歷年科目合格率發現,“歷史”的合格率均高于“中國歷史”合格率。究其原因,除上述提到的考生讀圖能力薄弱的原因外,還有考生知識基礎較為薄弱以至于無法在讀題時做好關鍵詞抓取、由于基本課程知識的不足導致聯結相關知識的能力也較低。
四、結語
綜上,香港考生在選擇選修科目的過程中,對歷史相關科目表現出較低的興趣。即便如此,就“歷史”和“中國歷史”兩門科目而言,“歷史”的合格率比“中國歷史”較高,每年均在90%以上。
但兩門歷史課程本身也存在問題,具體而言(見表1)為:由于“歷史”試卷中的所引資料不明確,因此是否能夠做到“史料實證”值得思考,另外一小部分提問方式不符合培養和考察歷史核心素養的要求、在出題時略欠妥當;從“中國歷史”的試卷來看,考生有關中國當代史的知識基礎相對薄弱,另外可能是由于課程目標中未能重視培養學生的讀圖能力(閱讀圖片、照片、地圖能力)導致考生在考試中的讀圖能力表現欠佳。
就目前的考試來看,仍有以下不足亟待完善和補充:其一,“歷史”試卷的史料出處問題需要借鑒“中國歷史”試卷出題方式列出并標明參考資料,幫助學生掌握“史料實證”素養;其二,考生的身份認同考察,首先需要在教學中充分教授身份認同的概念和內容之后,再從適當的角度考察身份認同,而不是將其脫離情境,只為了考察思辨能力而去模糊甚至誤導考生對身份認同的理解;其三,要加強教師和學生的當代史知識掌握程度,這不僅有助于學生正確認識中國,更有助于對學生國民身份認同的培養;其四,要加強學生的讀圖能力,特別是對圖片和圖片中文字的圖文結合能力,讀圖能力不僅作為歷史科評核所需,其作為語言閱讀能力的基礎也需盡早認知并掌握。
基于整體史觀、全球史觀的學科發展路徑,首先需要在目前的歷史課程標準基礎之上,竭力擺脫兩種歷史的教育模式,整合課程目標與評價目標,結合歷史與現實情境,在知識層面貫穿中國史與世界史知識,以增強學生對國內外歷史知識的了解;其次在技能層面要加強對于史料的理解、辨識與運用,培養學生的讀圖能力等學科能力和思維能力以及培養全球視野、人文情懷、國家認同感和中華民族認同感,構建相對統一穩定的歷史課程體系。基于我國歷史核心素養的要求,結合澳門歷史教育的經驗,未來課程應力求培養出具備核心史觀、歷史解釋、時空觀念、史料實證、家國情懷,同時指向“中國文明未來建構”的國家人才。
參考文獻:
[1]簡麗芳,Edward Vickers.香港中學課程中的“歷史科”與“中國歷史科”[J].歷史教學(中學版),2010(4):41-49.
[2]趙敏,張紹清,黃明亮.粵港澳城市群基礎教育區域協同的推進策略研究[J].現代教育管理,2023(3):29-37.
[3趙宏勃.對外漢語教學中文化課程測試的理念與形式[J].教育與考試,2012(2):37-40.
[4]劉暉,張艷芳.香港特區區域教育樞紐建設:戰略與成效[J].中國遠程教育,2023,43(11):60-71.
沈陽師范大學博士、引進人才科研項目啟動基金,項目名稱:中國近代中學經濟科目史(項目編號:BS202333)
樸匯燕(1995.9-),女,朝鮮族,遼寧沈陽人,博士,講師,研究方向:課程與教學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