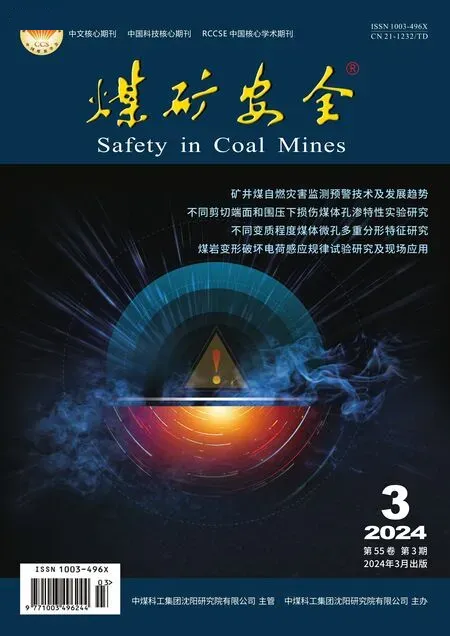火成巖侵蝕對煤自燃特性及其結構的影響
胡海峰 ,楊英兵 ,2 ,張運增 ,2 ,陳明浩 ,郭佳策
(1.國能神東煤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內蒙古 鄂爾多斯 017200;2.國家能源集團 礦井通風安全與職業健康防護研究中心,內蒙古 鄂爾多斯 017209;3.中煤科工集團沈陽研究院有限公司,遼寧 撫順 113122;4.煤礦安全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遼寧 撫順 113122)
火成巖侵蝕作為煤礦井下常見的地質構造之一,在世界主要煤炭生產國家均有分布[1-4]。據已有資料顯示,我國已發現存在火成巖侵蝕現象的煤田礦區數量超過30 個[5-6]。火成巖侵蝕對煤層的穩定性、煤體成分和孔隙結構特征均會造成影響[7-8]。在煤礦采掘火成巖侵蝕煤層過程中,常伴有發生瓦斯突出、煤炭自燃等災害事故的風險[9]。例如徐州張集煤礦在1995 年和1998 年先后發生3 次煤與瓦斯動力現象;淮北楊柳煤礦在2011 年發生采空區自燃事故[10];鐵法大興礦在采掘火成巖侵蝕煤層過程中常受到煤自燃威脅[11-13]。
目前國內外學者圍繞火成巖侵蝕煤體的組成和結構特征,開展了一系列關于火成巖侵蝕煤層致災原理的研究。SUSILAWATI 等[14]、劉福勝等[15]通過分析煤樣的地球化學和礦物學特征,發現火成巖侵蝕會提高煤的變質程度;蔣靜宇等[16]、代世峰等[17]、LIU 等[18]分析通過煤中無機成分的含量特征,發現火成巖侵蝕煤中水分、揮發分含量降低,黃鐵礦、方解石和鐵白云石含量增加;王亮等[10]、MASTALERZ 等[7]、JIANG 等[19]對比分析了原生煤與火成巖侵蝕煤體的孔隙結構特征,發現火成巖侵蝕增大煤的比表面積,煤中微孔數量和比表面積降低,宏觀孔數量增加,瓦斯賦存量增加;SHI 等[13]研究發現火成巖侵蝕后煤中直徑>20 nm 的孔隙比表面積增多。然而目前鮮有針對火成巖侵蝕影響煤自燃特征的相關報道,因此關于揭示火成巖侵蝕對煤自燃極限參數和煤結構特征差異的工作中還需要進一步開展系統性的深入研究。為此,以陜西、遼寧區域兩煤礦同工作面原生煤及火成巖侵蝕煤為對象,對煤的氧化特性、自燃極限參數、活性官能團含量以及孔隙結構特征進行分析,以期從宏觀和微觀層面揭示火成巖侵蝕對煤層自燃特性的影響規律。
1 樣本制備及試驗方法
1.1 樣本信息
在兩煤礦同工作面中靠近火成巖處采集火成巖侵蝕煤樣,在遠離火成巖處采集原生煤樣,將陜西區域煤礦煤樣編號為TS,將遼寧區域煤礦煤樣編號為XN。原生煤及火成巖侵蝕煤樣具體編號為TS-1、TS-2、XN-1 和XN-2,煤樣的制備方法遵照GB474—2008 標準。為減少外在水分對測試結果的干擾,測試前將試驗煤樣置于40 ℃恒溫干燥箱內干燥48 h。試驗煤樣的工業分析結果見表1。火成巖侵蝕煤樣相較于原生煤,其水分和空氣干燥基揮發分含量更低,空氣干燥基灰分和空氣干燥基固定碳含量更高。

表1 實驗煤樣的工業分析結果Table 1 Results of industrial analysis of experimental coal samples
1.2 測試方法
1)程序升溫試驗。為探究火成巖侵蝕對煤氧化特性和自燃極限參數的影響。采用煤自燃程序升溫檢測裝置,該裝置由金屬煤樣罐、程序控溫箱、供氣管路和氣相色譜儀構成。煤樣罐為內徑和高均為5 cm 的鋼制圓柱罐體。將裝有測試樣品的煤樣罐置于程序控溫箱內,設置恒溫箱升溫速率為0.5 ℃/min;接通供氣管路,提供流量為100 mL/min、體積分數為21%的O2-N2混合氣體。本次程序升溫測試的煤溫范圍為30~180 ℃,煤溫每升高5 ℃對排氣端進行1 次采氣分析,分別檢測氣體中的O2、CO 和CO2體積分數,用以分析煤樣的氧化特性和自燃極限參數。
2)物理吸附測試。為探究火成巖侵蝕對煤孔隙結構特征造成的影響。采用美國康塔Autosorb 的比表面積和孔徑分析儀,檢測孔徑范圍小于50 nm 的微孔和介孔,分別使用BET、HK 和BJH 理論模型計算煤的比表面積、平均孔徑及孔隙體積;選用美國麥克默瑞提克的AutoPore V9600 高性能全自動壓汞儀進行煤樣的壓汞測試,試驗的壓力范圍在0~420 MPa,檢測孔徑范圍為3×10-9~1 100×10-6m。
3)紅外光譜檢測。為探究火成巖侵蝕對煤中活性基團含量的影響。采用德國布魯克TENSOR27型傅里葉變換紅外光譜儀,在30℃條件下對煤樣進行紅外檢測(FT-IR),在分辨率為4 cm-1,光譜范圍為4 000~400 cm-1內記錄煤的FTIR 光譜。通過分析各煤樣的FT-IR 曲線,統計煤的主要官能團含量。
2 試驗結果
2.1 氣體變化速率與自燃參數
2.1.1 氣體變化速率
煤氧化自燃過程涉及復雜的物理、化學吸附和化學反應。氧氣作為重要的反應物質,參與到煤自燃的全部過程。煤的耗氧速度作為評價煤自燃特性的重要參數之一,被廣泛應用于煤自燃特性的研究當中。耗氧速率計算公式為:
式中:v1為煤樣耗氧速率,mol/(m3·s);Q為試驗過程中氣體流量,m3/s;c0為標準O2的體積分數,20.10%;c1為煤樣罐進氣口處的氧氣物質的量濃度,mol/m3;c2為煤樣罐排氣口處的氧氣物質的量濃度,mol/m3;S為煤樣罐截面積,m2;L為煤樣的堆積高度,m。
CO 釋放速率的計算公式為:
式中:v2為煤樣在氧氣物質的量濃度為c1時的CO 釋放速率,mol/(m3·s);c3為煤樣罐排氣口處的CO 物質的量濃度,mol/m3;V為煤樣罐內煤樣的體積,m3。
同理,CO2釋放速度v3的計算公式為:
式中:c4為煤樣罐排氣口處的CO2物質的量濃度,mol/m3。
將煤樣程序升溫試驗結果與式(1)~式(3)相結合,計算獲得的煤氧化過程中的氣體變化速率如圖1。

圖1 氣體變化速度分布曲線圖Fig.1 Distribution curves of gases speed changes
由圖1 可知:相同溫度下同工作面火成巖侵蝕煤相較于原生煤具有更高的耗氧、CO 釋放和CO2釋放速度。由圖1(a)可知:相同溫度下4 組煤樣的耗氧速度排序為XN-2>TS-2>XN-1>TS-1,進一步分析,受火成巖侵蝕的影響,在30~180 ℃范圍內,TS 煤樣耗氧速度的增幅百分比為25.98%~125.69%,XN 煤樣耗氧速度的增幅百分比為25.96%~159.37%;由圖1(b)可知:TS 煤樣CO 釋放速度的增幅百分比為20.52%~363.49%,XN 煤樣CO 釋放速度的增幅百分比為9.53%~235.20%;由圖1(c)可知:TS 煤樣CO2釋放速度的增幅百分比為0.55%~45.90%,XN 煤樣CO2釋放速度的增幅百分比為2.12%~70.97%。火成巖侵蝕改變了煤的氧化特性,增強了煤的耗氧、CO 釋放和CO2釋放能力。
2.1.2 自燃參數
煤自燃極限參數包括最小浮煤厚度、下限氧氣體積分數和上限漏風強度。當松散煤體同時滿足厚度不低于最小浮煤厚度,煤體接觸到的氧氣體積分數不低于下限氧氣體積分數,且煤體所處環境的漏風強度不大于上限漏風強度時,松散煤體內部產熱速率大于散熱速率,極易造成熱量在煤體內積聚,進而引發煤炭自燃。
最小浮煤厚度的計算公式為[20]:
式中:hmin為最小浮煤厚度,m;ρg為空氣密度,kg/m3;Cg為空氣比熱容,J/(kg·K);T為煤體溫度,℃;Ty為巖體溫度,取巖體溫度為30 ℃;λe為煤導熱系數,J/(m·s·℃);q(T) 為煤在溫度為T時的氧化放熱強度,kJ/(m3·s)。
下限氧氣體積分數的計算公式為[21]:
式中:cmin為下限氧氣體積分數,%;h為松散煤體厚度,m。
上限漏風強度的計算公式為[21]:
式中:Qmax為上限漏風強度,m/s。
煤氧化放熱強度的計算公式為[21]:
式中:qa為煤體對氧氣的化學吸附熱,kJ/mol;Δh1為CO 的生成焓,kJ/mol;Δh2為CO2的生成焓, kJ/mol。
將計算獲得的煤耗氧、CO 釋放速度和CO2釋放速度與式(4)~式(7)相結合,計算獲得的煤氧化自燃過程中的自燃極限參數如圖2。

圖2 氣體變化速度分布曲線圖Fig.2 Distribution curves of coal spontaneous combustion limit parameters
由圖2 可知:隨著溫度的升高,測試煤氧的最小浮煤厚度和下限氧氣體積分數的分布趨勢相近,均呈現出先增大后減小的趨勢;煤樣的上限漏風強度則隨著溫度的升高而增大。相同溫度條件下,同工作面火成巖侵蝕煤相較于原生煤具有更低的最小浮煤厚度、下限氧氣體積分數和更高的上限漏風強度。由圖2(a)可知:相同溫度下4組煤樣的最小浮煤厚度排序為XN-2 煤樣的微孔和介孔孔徑分布結果如圖3,通過N2吸附獲得的煤樣孔隙結構參數見表2。 圖3 煤樣孔徑分布特征Fig.3 Pore siz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oal 表2 通過N2 吸附獲得的煤樣孔隙結構參數Table 2 Pore structure parameters of coal samples obtained by N2 adsorption 由圖3 可知:火成巖侵蝕煤和原生煤樣的微孔和介孔孔徑分布曲線呈相同的分布趨勢。由圖3(a)、圖3(b)可發現:同工作面原生煤與火成巖侵蝕煤的孔徑曲線呈多峰分布狀態,且火成巖侵蝕煤的孔徑分布曲線始終大于原生煤的孔徑分布曲線;由圖3(c)、圖3(d)可知:當孔徑小于18 nm時,同工作面火成巖侵蝕煤的介孔孔徑分布曲線小于原生煤,當孔徑大于18 nm 時,火成巖侵蝕煤的介孔孔徑分布曲線大于原生煤。 由表2 可知:受斷火成巖侵蝕的影響,TS 煤的比表面積由14.605 m2/g 降至4.416 m2/g,降幅百分比為69.76%;XN 煤的比表面積由17.784 m2/g降至9.060 m2/g,降幅百分比為49.06%;TS 煤的平均孔徑由5.739 nm 增至7.968 nm,增幅百分比為27.97%;XN 煤的平均孔徑由5.461 nm 增至10.471 nm,增幅百分比為47.85%;TS 煤樣和XN 煤樣的微孔孔容降幅分別為63.64%和56.74%;TS 煤和XN 煤的介孔孔容降幅為29.35%和35.56%。火成巖侵蝕導致煤中微孔和介孔的比表面積及孔容降低,比表面積增大,改變煤體原本的微孔和介孔孔隙結構特征。 為探究火成巖侵蝕對煤體宏觀孔隙結構特征的影響,采用壓汞儀對煤樣進行孔隙結構測試。煤樣孔徑分布與階段進汞量關系如圖4,煤樣介孔、宏觀孔的比表面積及孔容分布結果見表3。 圖4 煤樣孔徑分布與階段進汞量關系曲線Fig.4 Relation curves between pore size distribution and stage mercury intake of coal 表3 介孔、宏觀孔的比表面積及孔容分布結果Table 3 Distribution results of specific surface area and pore volume distribution of mesoporous and macroscopic pores 由圖4 可知:火成巖侵蝕煤和原生煤樣的階段進汞量分布曲線隨孔徑的增大整體呈降低趨勢,且當孔徑大于20 nm 時火成巖侵蝕煤的階段進汞量曲線明顯高于原生煤,這與文獻[13]的檢測結果相符合。 由表3 壓汞實驗結果可知:受火成巖侵蝕的影響,TS 煤介孔的比表面積由22.373 6 m2/g 減小至16.875 4 m2/g,降幅百分比為24.57%,宏觀孔的比表面積由0.281 4 m2/g 增至1.004 6 m2/g,增幅百分比為71.99%;XN 煤的介孔比表面積由18.384 6 m2/g 降至13.726 1 m2/g,降幅百分比為25.34%,宏觀孔的比表面積由0.243 0 m2/g 增至0.5439 m2/g,增幅百分比為55.32%;TS 煤介孔孔容由0.061 3 cm3/g 降至0.056 5 cm3/g,降幅百分比 為7.83%,宏 觀 孔 孔 容 由0.011 0 cm3/g 增 至0.031 6 cm3/g,增幅百分比為65.19%;XN 煤介孔孔容由0.051 1 cm3/g 降至0.044 9 cm3/g,降幅百分比為12.13%,宏觀孔孔容由0.007 4 cm3/g 增至0.020 6 cm3/g,增幅百分比為64.08%。 由低溫氮氣吸附實驗和壓汞實驗結果可知,火成巖侵蝕導致煤中孔隙結構特征發生改變,煤中原有微孔和介孔破碎、塌陷、連同形成較大的空隙通路,特別是孔徑大于20 nm 的孔隙結構占比增大,提高煤體內部氣體的流通性,提高了煤的氧化自燃風險。 4 組實驗煤樣的紅外光譜曲線如圖5。 圖5 煤樣紅外光譜圖Fig.5 FTIR spectrum of coal 由圖5 可知:4 組實驗煤樣的FT-IR 曲線具有相似的分布趨勢,按照曲線的吸收峰分布特征,可將煤樣的紅外光譜曲線劃分為4 個階段,即波數范圍700~900 cm-1波段的芳香烴區、1 000~1 800 cm-1波段的含氧官能團區、2 800~3 000 cm-1波段的脂肪烴區和3 000~3 600 cm-1波段的羥基區;其中主要吸收峰包括在710~870 cm-1波段的苯環取代吸收峰,1 160~1 320 cm-1波段附近的-C-O-吸收峰,在1 410 cm-1附近的-CH2彎曲振動吸收峰,在1 600 cm-1附近的C=C 吸收峰,在1 695 cm-1附近的C=O 吸收峰,2 870 cm-1附近的-CH3對稱振動吸收峰,在2 923 cm-1附近的-CH2不對稱伸縮振動吸收峰,在3 427 cm-1附近的OH-OH 伸縮振動吸收峰。 為探究火成巖侵蝕對煤體表面官能團含量的影響,使用分峰擬合軟件Peakfit 分別擬合圖5 中4 組煤樣的FT-IR 曲線,獲取的各煤樣主要官能團區域的吸收峰面積比見表4。 表4 煤樣中各主要官能團譜吸收峰面積占比Table 4 Infrared absorption peak area proportion of main functional groups in coal 由表4 可知:受火成巖侵蝕影響,TS 煤芳香烴區的面積比由0.336%增至0.782%,增幅百分比為132.74%;含氧官能團區面積比由14.900%增至29.818%,增幅百分比為100.12%;脂肪烴區的面積比由0.487% 增至2.116%,增幅百分比為24.57%;羥基區面積比由84.276%降至67.283%,降幅百分比為334.50%;XN 煤的芳香烴區的面積比由0.709%增至4.053%,增幅百分比為471.65%;含氧官能團區面積比由34.791%增至40.647%,增幅百分比為16.83%;脂肪烴區面積比由1.466%增至1.906%,增幅百分比為30.01%;羥基區的面積比由63.034%降至53.393%,降幅百分比為15.29%。 由紅外光譜測試結果可知,火成巖侵入體熱變質作用促進煤中有機物質發生熱解、揮發,導致煤中活性官能團含量發生改變。煤中原有的芳香烴、含氧官能團和脂肪烴含量增大,羥基含量減少。含氧官能團的增多會提高煤的氧化活性[22],促進煤氧化反應的發生。脂肪烴在煤氧化過程中可與氧發生反應產生羥基,而羥基的活性較強,極易發生氧化消耗[20]。并且脂肪烴氧化生成羥基的速率小于羥基的氧化消耗速率[23],因此表現為火成巖侵蝕煤樣的羥基含量低于原生煤。 煤氧化自燃受內部和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內部影響因素包括煤化程度、水分、煤巖成分、含硫量、粒度與孔隙結構和瓦斯含量等,外部影響因素包括地質條件、開采技術、漏風強度和溫度等。研究涉及的4 組煤樣是采用統一的制備流程且在相同的測試環境下進行,拉近了各測試煤樣間的粒度及外部因素的差異,測試結果必然突顯出內部影響因素對煤自燃的影響,火成巖侵蝕煤的自燃差異性被突顯放大。具體表現為:受火成巖的機械擠壓與熱蝕影響,煤體孔隙結構遭到破壞,煤中水分散失、有機質揮發,導致煤中微孔和介孔破碎、塌陷、連通形成較大的空隙通路,特別是增大了孔徑20 nm 以上的孔隙結構占比,利于氧氣進入煤體與活性基團發生氧化反應;火成巖的高溫高壓作用促進煤中有機物質發生熱解、揮發,導致煤中芳香烴、含氧官能團和脂肪烴的相對含量均出現不同程度的增大,煤體的化學活性基團結構發生改變,氧化活性增強。 經火成巖侵蝕后,煤的物理孔隙結構和化學活性基團結構均發生變化,更有利于氧氣在煤體內部輸送、運移,促進氧氣與煤表面高活性官能團的結合,提高煤的氧化能力,進而提升煤的氧化放熱能力,降低煤自燃的最小浮煤厚度和下限氧氣體積分數,提高煤自燃的上限漏風強度,增大煤的自燃風險。 礦井實際采掘過程中,同工作面火成巖附近更易出現煤炭自燃現象。除了火成巖侵蝕提高煤體自身的氧化活性之外,也與外部影響因素中的地質條件、開采技術和漏風強度有很大關系。火成巖侵蝕增加煤炭的開采難度,減緩工作面的推進速度,增大火成巖附近煤體的氧氣接觸時間;火成巖侵蝕煤體的強度減弱易在采掘過程中破碎垮落,增大采空區內遺煤量,為煤的氧化自燃提供了必要的反應物;火成巖的硬度較高,在采空區內不易垮落,降低采空區的壓實程度,增大采空區的空隙率,有利于工作面風流向采空區深部滲透;受火成巖侵蝕的煤層瓦斯含量普遍高于普通煤層[21-22],當火成巖侵蝕煤體破碎后,煤體賦存的瓦斯氣體與氧氣發生置換,利于煤體與氧氣接觸發生氧化反應。并且在采掘火成巖侵蝕煤層過程中,為了降低瓦斯災害風險,通常采用打抽采鉆孔、設置抽采巷道、提高工作面供風量等手段降低瓦斯體積分數,但同時也會造成大量空氣滲入采空區內部,增大采空區“氧化升溫帶”的覆蓋范圍,進一步加大采空區發生遺煤自燃的風險。 1)火成巖侵蝕提升煤的氧化能力,降低煤自燃的最小浮煤厚度和下限氧氣體積分數,提高煤的上限漏風強度,增大煤的自燃風險。 2)火成巖侵蝕改變煤的孔隙結構特征,促進煤體內部氧化反應的發生,提高煤體內部的氣體流通性。 3)火成巖侵蝕導致煤中芳香烴、含氧官能團和脂肪烴含量增大,羥基含量減少,提高煤的氧化活性。火成巖侵蝕煤體具有更高的氧化活性。 4)火成巖侵蝕改變煤層賦存條件,增大煤層開采難度,提高采空區內漏風強度,延長采空區“氧化升溫帶”遺煤的氧化時間,從外部因素層面提升煤炭的自燃風險。火成巖侵蝕活動增加煤炭開采難度,增大采空區內遺煤量,降低采空區內壓實程度,提升采空區的滲透率;火成巖侵蝕煤層采掘過程中,為了降低瓦斯體積分數而采取的抽放手段也會增大采空區的漏風量,增大煤自燃風險。2.2 煤比表面積及孔隙分布




2.3 煤體化學活性基團含量


3 火成巖侵蝕煤自燃差異性分析
4 結 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