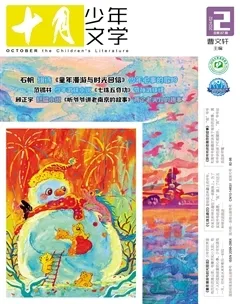[評(píng)論]在時(shí)間中漫游:少年石帆
有時(shí),進(jìn)入一首童詩(shī),就是進(jìn)入另一個(gè)自己。比如,石帆的童詩(shī)會(huì)給我這樣的感覺(jué),不是他在寫(xiě)詩(shī),而是詩(shī)在寫(xiě)他,以萬(wàn)物的情感。時(shí)間的流逝在慢慢完成他語(yǔ)言中的變化和細(xì)節(jié),從而喚醒了我們少年般的情感。于是,我們收到了這樣的來(lái)信:“等了那么久/時(shí)光/終于寄來(lái)了回信。”(《時(shí)光的回信》)
毫無(wú)疑問(wèn),每一首童詩(shī)都試圖與時(shí)間對(duì)抗,從而獲得留存的愿望。石帆或許就是他詩(shī)中那個(gè)“看不見(jiàn)世界的孩子”——小桑吉。他在想象中行動(dòng)起來(lái),萬(wàn)物成了他的向?qū)В骸八苓^(guò)的地方/萬(wàn)物叫他太陽(yáng)。”這里,“太陽(yáng)”的出現(xiàn)意味著白晝的開(kāi)始,而星圖的出現(xiàn)加深了時(shí)間與萬(wàn)物翅膀共振的可能:“世間的生靈與萬(wàn)物/注視著相似的你我/一樣閃亮,一樣的昏暗、隱沒(méi)/一如我們分辨不出群星。”(《你和我》)
如果以詩(shī)歌的眼睛和耳朵去看、去傾聽(tīng),用詩(shī)歌的心靈去感知,那么“群星”則暗示著我們又進(jìn)入了語(yǔ)言的黑夜,星球在石帆的詩(shī)意中完成了一次秘密運(yùn)行。這其中發(fā)生了什么呢?也許思想家?jiàn)W古斯丁會(huì)給我們答案:“時(shí)間是什么?你們不問(wèn)我我是知道的,如果你們問(wèn)我,我就不知道了。”時(shí)間的不確定性讓石帆不斷試探語(yǔ)言的邊界,直到“推開(kāi)窗/就把窗外盛開(kāi)的山桃花照亮/關(guān)上房門(mén)/‘嘀嗒,嘀嗒’/時(shí)間就重新開(kāi)始流淌。”(《四月的房子》)
我們不妨和石帆一起望向窗外,山桃花、氣味、聲音、時(shí)間……都涌了進(jìn)來(lái),將我們淹沒(méi)。沒(méi)錯(cuò),童詩(shī)到達(dá)的地方,就有花朵,它們長(zhǎng)在一個(gè)個(gè)的漢字里,然后花瓣落下來(lái),又生出新的詩(shī)和語(yǔ)言。于是我們和詩(shī)人一起獲得了珍貴的“花的三分鐘”:“花的一分鐘/用來(lái)芬芳……接下來(lái)的一分鐘/用來(lái)眺望遠(yuǎn)方……花的最后一分鐘/用來(lái)讓世界平靜。”詩(shī)人儼然成了一只蜜蜂,它采走了芬芳的時(shí)刻,留給我們語(yǔ)言之蜜,并引領(lǐng)我們重新建立與自然的關(guān)聯(lián),仿佛我們閱讀的不是一首詩(shī),而是“花香的河流”……
“日光下沒(méi)有了聲息/花香是一朵朵漣漪”(《花的三分鐘》)。正如小王子所說(shuō):“最大的問(wèn)題不是長(zhǎng)大,而是遺忘。”石帆寄情于萬(wàn)物,化身其中的一部分,他渴望像彼得·潘一樣來(lái)到永無(wú)島,拒絕長(zhǎng)大:“是啊,少年的手指/經(jīng)過(guò)深藍(lán)的海水/劃出一片銀灘/天邊的曙光正在海岸上緩緩點(diǎn)亮”(《少年的夢(mèng)》),“少年”是一段時(shí)間的匯聚,是生命果實(shí)的一種豐盈。在通往語(yǔ)言的途中,一個(gè)少年略帶情境式的回憶,具有獨(dú)白的神秘,他的手指撫平語(yǔ)言的波浪,這其中包裹著一種來(lái)自時(shí)間的生命力。不難看出,石帆沒(méi)有放低詩(shī)歌的姿態(tài),他詩(shī)歌的音調(diào)和節(jié)奏都在保持最初的自由心性,營(yíng)造出屬于自己的獨(dú)特的少年式的童詩(shī)美學(xué),為童詩(shī)的寫(xi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這是時(shí)間帶來(lái)的珍貴的寶石。因?yàn)槭珗?jiān)信,在詩(shī)意的時(shí)間中,所有的童詩(shī)最終都會(huì)慢慢向自我的童年靠攏,我們都聽(tīng)見(jiàn)了這樣的回音:
“那些錯(cuò)過(guò)的美好/會(huì)在這里歸還給我們。”(《歸還》)
- 十月·少年文學(xué)的其它文章
- 紙船
- 熊熊養(yǎng)育指南
- 春的林間
- 樹(shù)苗
- 風(fēng)過(guò)好運(yùn)
- 我在云彩上玩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