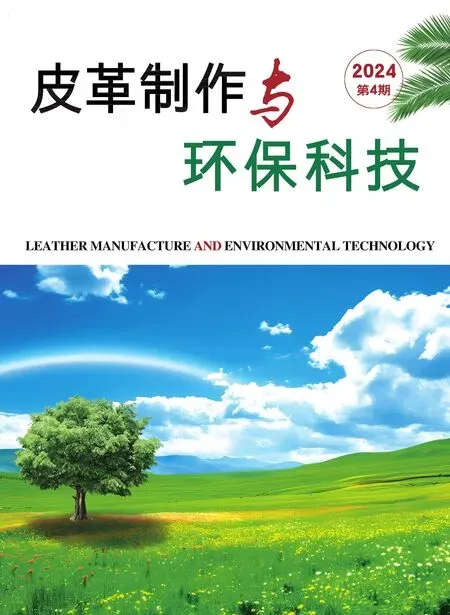土壤環境中新污染物治理的研究進展及展望
宋 帥
(山東公用環保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山東 濟寧 272000)
引言
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土壤環境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特別是新型污染物的出現引發廣泛關注。這些污染物不僅在環境中持久存在,而且對生態系統和人類健康構成嚴重威脅。因此,深入了解這些新型污染物的來源、傳播途徑及其對生態環境和人類健康的影響,成為當前環境科學研究的重要課題。
1 新污染物的種類及危害
1.1 全氟化合物
全氟化合物(PFAS)是一類化學性質穩定、難以降解的新型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廣泛應用于各種工業和生活產品中。這類化合物的最顯著特點是其碳氟鍵的強度,使其在自然環境中具有極高的持久性。全氟辛烷磺酸(PFOS)和全氟辛酸(PFOA)是全氟化合物中最典型的兩種,其結構中含有長鏈碳氟結構,這是導致其環境持久性和生物積累性的主要原因。PFOS和PFOA在環境中不易分解,能在水體、土壤甚至生物體內積累,并通過食物鏈傳播,造成生態環境和人體健康的長期風險[1]。全氟化合物在不粘鍋、防水紡織品、消防泡沫等領域被廣泛使用,導致其在全球分布。研究表明,PFOS和PFOA能干擾內分泌系統,影響生殖和發育功能,甚至與某些癌癥的發生有關。此外,這些化合物在人體內的積累會導致免疫系統功能下降,增加對疾病的敏感性。PFOS和PFOA的結構式如圖1所示。

圖1 全氟辛烷磺酸和全氟辛酸的結構式
1.2 環境內分泌干擾物
環境內分泌干擾物是一類能模仿或干擾生物體內分泌系統正常功能的化學物質。這些物質即便在極低濃度下也能對野生動物和人類的健康產生顯著影響。典型的環境內分泌干擾物包括雙酚類、多溴聯苯醚類、烷基酚類、鄰苯二甲酸酯類和有機磷酸酯類等。這些化合物普遍存在于日常用品如塑料制品、家用電器、化妝品和農藥中。環境內分泌干擾物通過模擬、阻斷或干擾激素的正常生物活動,影響生物體的生殖、發育和行為。如雙酚A(BPA)能模仿雌激素的作用,影響生殖系統和胚胎發育;多溴聯苯醚類在動物實驗中顯示出對甲狀腺激素的干擾作用;烷基酚類會導致雄性生物體的雌性化現象。
1.3 藥品和個人護理品
藥品和個人護理品,包括各類處方藥、非處方藥、獸用藥物和生長劑,以及化妝品、護膚品和香料等,日益成為環境中的新型污染物。這些物質通過多種途徑進入環境,如醫療廢水、家庭排放和農業活動,對生態系統和人類健康構成潛在風險。藥品殘留,特別是抗生素和激素類藥物,會導致環境中抗藥性菌株的出現和擴散。同時,獸用藥物和生長劑的濫用在畜牧業中普遍存在,其殘留會通過食物鏈影響人類健康。個人護理產品中的化學成分,如防腐劑、防曬劑和香料等,雖然在日常使用中安全,但其長期和持續的環境暴露會導致生態毒性,影響水生生物的生存和繁殖。
1.4 微塑料
微塑料,定義為直徑小于5 mm的塑料顆粒,其已成為全球性的環境問題。這些微小的塑料顆粒來源廣泛,包括日用塑料產品的破碎、合成纖維洗滌過程中的脫落,以及化妝品和個人護理產品中故意添加的微珠。海洋是微塑料的主要匯聚區域,也廣泛分布在河流、湖泊、土壤甚至大氣中。微塑料的環境危害不容忽視。由于其表面特性,微塑料容易吸附重金屬和有機污染物,如多環芳烴、多溴聯苯醚等,增加這些有害物質通過食物鏈進入生物體的風險。對于人類而言,盡管目前關于微塑料對人類健康影響的研究還處于初期階段,但是通過食物攝入和呼吸途徑接觸微塑料的可能性已經被科學界確認。這些微小顆粒及其吸附的有害化學物質對人體造成免疫、內分泌和神經系統的干擾[2]。
2 新污染物在不同類型場所的賦存情況
2.1 農田土壤中的新污染物
農田土壤作為新污染物的主要賦存場所之一,其污染主要源于污水和污泥的農用。雖然污水和污泥中富含氮、磷等營養元素,對農作物生長至關重要,但這種做法同時帶來新型污染物的風險。環境內分泌干擾物、藥品和個人護理品等產生的污染物通過污水和污泥進入土壤,影響土壤質量,并潛在地危害作物安全和人類健康。比如,在某些農區,由于長期使用含有抗生素和重金屬的污泥作為肥料,土壤中的抗藥性基因含量顯著上升,這不僅會影響土壤生態系統,還會增加抗藥性菌株通過作物進入人體的風險。
2.2 填埋場土壤中的新污染物
填埋場土壤中的新型污染物問題日益凸顯,這些污染物包括抗生素類藥物、個人護理品和化學添加劑等,通常隨著生活垃圾被送入填埋場。在填埋過程中,這些物質由于生物降解、化學反應或物理作用,會從固態廢物中釋放出來,逐漸滲透到土壤和地下水中,從而對環境造成長期影響。比如,在美國某些城市的研究中發現,填埋場周圍的地下水中含有多種藥物和個人護理產品的殘留物,這不僅暴露了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問題,也引發對公共飲用水安全的擔憂。此外,化學添加劑如塑化劑和阻燃劑的泄漏,會進一步加劇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程度。
2.3 工業場地中的新污染物
工業生產活動在極大提升人類生活質量的同時,也向周邊環境排放大量新型污染物。這些污染物包括但不限于重金屬、有機化合物及其他工業副產品,長時間殘留在工業場地的土壤和水體中。然而,在進行遺留工業場地的污染狀況調查及修復過程中,新污染物并未被充分納入《土壤環境質量 建設用地土壤污染風險管控標準(試行)》(GB 36600—2018)、《土壤環境質量 農用地土壤污染風險管控標準(試行)》(GB 15618—2018)、《建設用地土壤污染狀況調查技術導則》(HJ 25.1—2019)等現行標準和技術導則中。這種疏漏會導致對工業場地中新型污染物的風險評估和治理措施的忽視。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快速發展,一些地區的工業遺留地已經成為新型污染物的重災區。
3 土壤中新污染物的檢測方法
在當前的土壤環境治理中,新污染物的檢測呈現出緊迫性和復雜性。由于全國性的環境調查如污染源普查和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尚未涵蓋新污染物,對于這類污染物的底數和分布情況了解不足。同時,針對新污染物的檢測技術還相對落后,會進一步加劇土壤污染治理的難度。目前,已有一些檢測技術被應用于新污染物的識別和量化,如表1所示。這些技術能夠準確地識別和測量土壤樣品中的新污染物濃度,有助于評估污染程度和潛在風險。然而,由于土壤樣品的復雜性,這些檢測方法在實際應用中仍面臨諸多挑戰,如樣品前處理的復雜性、檢測過程中的干擾物質影響等[3]。

表1 土壤中新污染物的提取及檢測方法
4 土壤中新污染物的治理
4.1 土壤中全氟化合物的降解
全氟化合物的降解研究主要集中在水環境,而針對土壤環境中全氟化合物的研究相對較少,主要關注其在土壤中的污染狀況和分布特征。對于土壤中全氟化合物的治理,目前的研究正在探索有效的降解方法。其中,一種前沿技術是利用改性分子印跡TiO2納米管進行光催化降解全氟辛酸。這種方法通過結合分子印跡技術和TiO2納米管的高效光催化性能,能夠針對性地識別和降解土壤中的全氟辛酸。分子印跡技術通過形成特定污染物的“印跡”腔體,實現對全氟辛酸的高選擇性吸附,而TiO2納米管則利用光能有效促進化學反應,從而實現全氟辛酸的高效降解。結合物理吸附和化學降解的方法顯示出較好的應用前景,尤其在處理土壤中難以生物降解的全氟化合物方面具有重要意義[4]。全氟化合物降解方法概述如表2所示。

表2 環境中全氟化合物降解方法的優缺點
4.2 土壤中抗生素及抗性基因的降解
隨著工農業的快速發展,土壤中的抗生素含量迅速增加,帶來嚴重的生態風險,尤其是對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影響及抗性基因的傳播。目前,在抗生素污染土壤修復方面的研究還處于初期階段,主要采用的修復方法包括生物降解、吸附降解和光降解等。生物降解方法利用微生物降解抗生素,是一種環境友好的修復策略。特定微生物能夠利用抗生素作為碳源和能量源,通過生物代謝過程將其分解。吸附降解方法通過使用各種吸附劑(如活性炭、黏土礦物和生物炭等)將抗生素從土壤中吸附出來,從而減少其在環境中的濃度。光降解是利用紫外光或太陽光照射來分解抗生素的方法,這種方法依賴于抗生素分子對光的吸收特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解土壤中的抗生素污染。
4.3 土壤中微塑料的去除
土壤中微塑料的去除面臨著諸多挑戰,主要是因為微塑料與土壤基質之間存在不同程度的結合。有效的微塑料去除策略關鍵在于實現土壤基質與微塑料的有效分離。目前,一些技術正在被開發和應用于這一目的。比如,密度分離法利用密度差異將微塑料從土壤顆粒中分離出來,這通常涉及使用高密度溶液,如食鹽溶液,以便使微塑料浮到溶液表面。另外,基于篩分技術,可以利用不同大小的篩網分離微塑料和土壤顆粒。此外,浮選法也被應用于微塑料的分離,該方法通過改變浮選介質的性質來實現微塑料的分離[5]。未來,這些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和優化將對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5 展望
為應對土壤環境中新污染物帶來的挑戰,關鍵在于強化提取和檢測技術。鑒于這些污染物通常以低濃度存在,并與土壤介質復雜結合,傳統檢測方法難以準確測定其實際濃度。因此,開發更先進的技術至關重要,以保證對這些污染物的風險評估和治理策略更加精準有效。此外,對新污染物在土壤環境中的風險進行全面評估,并建立相應的環境標準同樣重要。這要求運用多種模型方法評估其對生態系統和人體健康的潛在影響,并確定安全限值。同時,制定的土壤環境基準應全面考慮生態安全、人體健康和農產品安全,以指導實際治理活動。面對新污染物特性,升級和優化傳統治理技術是必要的。在現有技術基礎上,研發針對性更強、效率更高、環保性更好的修復方法,將是有效應對這一挑戰的關鍵所在。
6 結語
土壤環境中新污染物的治理成為環境科學領域的重點關注對象。通過對新污染物的來源、危害進行深入研究,并開發針對性的檢測、評估和降解技術,不斷提高對這些污染物治理的效率和效果。未來,隨著技術的進步和策略的優化,有望實現更為全面和有效的新污染物控制,為保護土壤環境和促進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做出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