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母親
文/任正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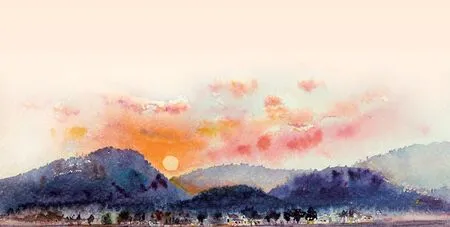
一
父親任摩遜,盡職盡責一生。他在貴州的山區籌建了一所民族中學,一頭扎進去就是幾十年。當時,母親不僅要陪伴父親,還要照顧我們兄妹七人,又要自修文化,完成自己的教學任務。
我親眼看到父母謹小慎微、忘我地拼其全力工作,無暇顧及我們,就如我拼死工作,無暇孝敬他們一樣。
與父母相處的青少年時代,印象最深的就是三年自然災害的困難時期。我們一家九口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資來生活。本來生活就十分困難,我們兄妹七人每人每個學期還要繳2 元~3 元的學費,所以到繳學費時,母親每次都發愁。
其實,直到高中畢業,我都沒有穿過襯衣。我上大學時,母親給了我兩件襯衣,我當時很想哭,因為我有了襯衣就意味著弟妹們在生活上會更難。另外,我家當時是兩三人合用一床被子,而我上大學要拿走一床被子,家里就更困難了。我家也沒有多余的被單,母親就去撿畢業學生丟棄的幾床破被單,縫縫補補后洗干凈給我用,而這條被單在重慶陪伴我度過了大學生活。
1997 年,高等教育制度改革,開始向學生收費,但配套的助學貸款還沒有跟上,于是華為向教育部捐獻了2500 萬元的寒門學子基金。其實,在基金叫什么名字這個問題上爭論很大,甚至有員工來找我,說不要叫寒門。但我認為,出身貧寒并不羞恥,而思想與知識貧寒,即使出身高貴也不光榮。我的青少年時代就是在貧困、饑餓、父母逼著學習中過來的。沒有他們在困難中看見光明,指導并逼迫我們努力,就不會有我的今天。
我一直為老一輩的品德自豪,他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計榮辱、忠于事業的精神值得后代學習。生活中不可能沒有挫折,但為人民奮斗的意志不能動搖。
二
華為是在十分艱難困苦的條件下起步的。那時父母、侄子與我住在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沒有單獨的廚房,只能在陽臺上做飯。他們處處為我擔心,生活也十分節省,攢一些錢說是為了將來“救”我。
當時在廣東,魚蝦死后十分便宜,而父母就專門買死魚、死蝦吃,說還很新鮮。晚上出去買菜,也是買那些賣不掉的菜,便宜一些。彼時的我無暇顧及他們的生活,以致母親糖尿病嚴重了我也不知道,還是鄰居告訴我的。
華為發展得有了規模后,管理轉換的壓力巨大,我不僅照顧不了父母,連自己也照顧不好,我的身體也是那段時間累垮的。我父母這時決定轉去我妹妹昆明的家里定居。我也因此理解了要奮斗就會有犧牲,華為的成功,使我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機會與責任,也銷蝕了自己的健康。
有段時間,媒體對華為有一些報道,內容毀譽參半,母親對“譽”不感興趣,但對一些不了解我們真實情況的文章卻十分憂心。我告訴她,我們不是上市公司,不需要公示社會,主要是對政府負責,對企業的有效運行負責。所以我們不在媒體上去辯論,不要為我們這樣一個小公司,去干擾國家的宣傳重點,我們也承擔不了這么大責任。此時母親才舒了一口氣,理解了我的沉默。
三
1999 年年末的最后一天,我總算在公務結束之后,買了一張從北京去昆明的機票,去看看母親。
買好機票后,我沒有立即給母親打電話,因為若提前跟她說,她會忙碌一下午,會給我做一些我小時候喜歡吃的東西。直到飛機起飛時,我才告訴母親回家的消息,并讓她不要告訴別人,我自己坐出租車回家,目的就是好好陪陪他們。
其實,前幾年我都會回去看望母親,但一下飛機,公司的辦事處就會把我接走,稱:“需要與某個重要客戶見一見、聊一聊……”忙到回家后,只有與母親告別的時間。我知道她一直盼著與我嘮嘮家常,但即使一次又一次落空,她依舊會對我說:“工作重要,先工作。”
我總認為母親身體很好,而我身體不好,以及當我的知識結構、智力跟不上時代時,我就會逐步退出歷史舞臺,總會有時間陪陪她的,沒想到卻飛來橫禍。
2001 年1 月8 日,我圓滿結束對外國一家企業的訪問時,就接到了紀平(華為元老之一)的電話,說母親在上午10 時左右從菜市場出來,被車撞成重傷,孫亞芳(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原董事長)已前往昆明組織搶救。
回到昆明,我發現母親的頭部受傷嚴重,心跳、呼吸全靠藥物和機器維持,同事們在電話里不告訴我,是怕我在旅途中出事。我看見母親安詳地躺在病床上,不用操勞、煩心,好像她一生也沒有這么休息過。
回顧自己走過的路,捫心自問,我無愧于事業與員工、無愧于朋友,唯一有愧的是對不起父母,一直沒有照顧好他們。
我主持華為工作后,我們對待員工,包括辭職的員工都是寬松的(對被管理者少加控制,多給予自由的管理方式),只對高級干部嚴格要求,即我們只選拔有敬業精神、獻身精神,有責任心、使命感的員工進入干部隊伍。這也是親歷親見了父母的過往,而形成了我寬容的品格。
千聲萬聲喚不回,逝者已經逝去,活著的還要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