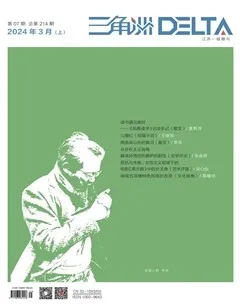小浪底北岸
葛道吉
春上,我再次來到黃河,仍是小浪底北岸櫛比的山梁。
那山梁好長,從遙遠的王屋山蜿蜒下來,直插黃河。山梁與山梁的間距不像攏頭發的梳子那般規整,有的狹窄,有的寬敞。就有4個鄉鎮10萬民眾在溝溝叉叉的土地上耕種。這里滿眼的蒼茫,村莊是很難一眼就看得見的,全隱在1000余平方公里的山坳溝壑里。
道道山梁像極了巨龍探水。浩瀚的水域淹沒了很多散落的村莊、遺址與梯田,讓歷史上光禿禿的山梁變得林木蓊郁。水改變了生態,改變了這里祖祖輩輩人的生活方式。
“老遠看到車就知道你來了。”老人在路旁迎接。我趕忙打招呼:“老劉大伯可好,大娘也在吧!”“在!忙著給你爐紅薯。”大娘總記著我愛吃紅薯。去年冬季,我進到老人居住的土窯洞,看到剛出爐的熱紅薯,忍不住一口氣吃了兩個,不住地說著好吃好吃。大伯大娘只是笑。我已是大伯大娘這個窯院的常客了。在小浪底體驗生活,看到很多山梁、島嶼都成了風景區,都成了開發好了的休閑山莊、游樂場所。唯獨這個交通不便的偏僻角落沒有開發,就因為老劉大伯死守著這個銜著水的山梁。他說這是一圪垯好土,養人!他的話格外引起了我的興趣,我們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去年秋季,我無意間發現了老人深埋心底的一個秘密。那是山頭最為美艷壯麗的時刻,各種果樹紅黃盈枝,有李、杏、山楂、石榴、蟠桃、柿子以及玉米、大豆、花生、紅薯等。果實飄香引來了無數的蜂、蝶、喜鵲以及其他飛鳥。老人說:“鳥們吃不了幾個果,它們也是盼了一年了。”我想目睹老人收獲的場景,留幾張照片,就和老人約定采摘的時間。誰知,老人還有一個自己設置好了的程序。那夜,我隨身帶著帳篷睡在隔壁另一孔破舊的窯洞里,環境的靜謐讓我寫作時忘了時間,早晨就貪睡了一會兒。出門伸一下腰身,突然發現老人面對一炷香,正襟下跪在窯院前邊不遠的一塊臺地上。香在面前長方的石槽里繚繞,裊起一縷青煙,老人深深叩下頭,前額貼著黃土。我悄悄走了過去,生怕驚擾老人。三次叩頭,老人叫了聲“爹——娘——兄弟小毛——”高聲說:“今年又豐收了!”
老人面對古老而嶄新的黃河,一番話在水面上打漂,有波浪涌來,聲音一揚一揚送去遠方:“……咱們家滿山的秋作物和瓜果,你們都回來看看,隨便吃,隨便摘,再不要為沒吃沒穿發愁了。咱牛洼村移民到平原后,全部住樓房,孫兒孫女都在城里工作,也買了房,買了車。爹,娘,早些年咱們做夢都不敢想,自從小浪底大壩建成,咱們這沿河村莊都搬遷了,都過上好日子了。我要叫你們親眼看著,牛洼到山梁那80畝地是咱們家承包的。我身體很好,孩子們整天嚷著叫我去城里住,說冬天有暖氣,夏天有空調。哪有咱這老窯得勁!我一天不見水,心里就不踏實。我就在這兒住,叫你們年年不愁吃,不愁穿……”
老人很動情,嘴角抽了抽,就滾下了老淚。我忍不住叫了聲老劉大伯,老人沒防備,身體震了一下,說:“今天孩子們都要來卸果,你就多拍幾張照片!”我趕忙拉大伯起來,說:“您老這把年紀了,不能傷感,身體要緊。”“沒事,10年前我73歲,孩子們誰也不讓我承包,今年83還沒覺著老。”“這地方是世外桃源,人長壽!”我接話茬剛說完,大娘已站在身后了:“春節孩子們非叫回城里過年,過不到破五就嚷著要來。這地方不知道有啥好!”大娘其實也是很踏實的。又說:“飯成了……”
老劉大伯抬眼看看日頭,急急說:“走,回吃飯!”
沒多大工夫,山腰上來了兩輛車。老劉大伯的兩個兒子都已兒孫滿堂,重孫重孫女像小鳥一樣撲進老爺老奶懷里,四世同堂,幸福無邊。
兒、孫、孫女們紛紛拿出準備好的各種編織袋,有的摘山楂,有的摘石榴,還有的背著鋤頭直接到一邊刨紅薯、刨花生去了。我捕捉到了豐收的喜悅,捕捉到了重孫、重孫女歡快的腳步與小鳥一樣嘹亮的叫聲,著實為這樣的場景興奮。這時,突然不見了老劉大伯。仔細看,那塊高地上放了把椅子,老劉大伯正在椅子上坐著。看到兒孫們大兜小袋往車里裝,心里的踏實和滿足全蕩漾在臉上,笑容里寫滿深沉的皺紋,顯出殷實而低沉的自豪。
車開走了,窯洞里丟下了各種老年人的營養食品。大娘一邊收拾,一邊埋怨:“不讓買非要買,放壞了也沒人吃。”當然,他們明明知道那是孩子們誠誠的心意。
太陽斜到了西山頭,老劉大伯又坐到那把椅子上,面向黃河水愣神。我感覺是個機會,就在老劉大伯身邊一塊石頭上坐了,小心著問:“爹娘都已過世,大伯怎么如此傷感呢?”
老人像觸動了一下,看我一眼,我很小心而真誠。老人急忙把眼光投向水面,銀白里有陽光,水很亮,波浪像地壟一樣一棱一棱涌動著放光。
那是近80年前的事了。老劉大伯慢慢把渾濁的眼神從水里收回來,給我講了他的家與黃河水的恩恩怨怨。當時,老劉大伯7歲,姊妹3個,上有一個姐,下有一個弟。姐16歲就有人張羅提親。弟尚小,剛滿4歲。
1937年的初冬季節,印象最深的就是沒完沒了的挨餓,整天赤腳丫子沒鞋穿。那日掌了燈,河岸河水與岸畔小路全部被夜色包圍。姐姐陪嫁的那床緞子被面與“太平洋”印花大單,是爹拼死拼活在山上割荊條、編籮筐、編荊席,與黃河南岸一個生意人兌換所得。爹的手磨出血泡,裹著厚厚的布條也沒有停下來的時候。20張荊席完成了,就剩10個籮筐就全部編完了交換的180個總數。按當時所定時間沒有任何問題,那天生意人突然出現在窯院門口,說河南一個夯筑工程提前開工,所編的籮筐要趕在開工之前交付,這樣比原定時間提前了半個月。生意人到另一孔窯洞查看了碼著的現貨,問數量齊不齊。老劉大伯說“不差啥,就是時間怕不好保證。”說著晃了晃抱著的傷手:“不能干啊!”
生意人太知道世事的清明與混沌了,二話沒說,在隨身背著的褡褳里取出被面和單子,說:“趕趕吧,都不容易,原來定的時間是人家改的,咱們的一切都是圍著人家轉的啊!”說著把東西遞給了老劉大伯,又說:“也不說最后交換了,先把東西交給你,也算是時間變更對你的補償。你放心,這是貨真價實的好料,在洛陽也不是誰都可以弄到手的。”
“要說對夠整數也不是多大事,關鍵是手磨得嚇人,吃飯連筷子都拿不緊。編制活兒就是個手勁兒,我和孩子們都搭不上手……”大娘在一旁插話,在大伯手中接了被面和單子,左看右看,索性手一揚抖開了單子,色澤鮮艷,花開富貴。“放心吧嫂子,這可是上等的六尺大單,被面也是足尺的綢緞。”生意人拿出了很大的誠意說。
“既然你這般真誠,我也不會說出個二字來。現在主要是缺乏荊條,偌大的山,近處平緩處已找不到了。不過你放心,受再大的苦我也認了,說鐵就是釘!”父親也掏出了心窩。
隨即第二天一大早,父親吃了飯就出門,除了拿上那根鎏光的桑木扁擔外,再就是那張磨得瘋快的“疙瘩頭鐮”。這鐮能當斧子用,接近胳膊粗的山柴也能輕易放倒。割個小拇指粗細的荊條,簡直不在話下。
可是,已是張燈時分了,還沒見人回來。
后坑少說也有七八里遠,關鍵是山路太難走……
第二天拂曉,窯洞里仍然漆黑一片,有微微的暉亮擠進門縫。娘毫不猶豫披衣起床,不能再等山雀的打鳴。這山溝里,這黃河邊,早起的信號就是天麻麻亮時的鳥叫。老娘踏著晨曦微亮的山道,朝著后坑的方向進發,不時有早起的山鼠掠過,有受驚嚇的山雞振翅鳴叫。娘顧不了那么多,滿腦子的焦慮和埋怨:“你能割多少,后坑滿山架嶺的荊條能割完?”想著不自覺就高聲喊了起來:“你在哪唻——天明了也不回來……”
聲音在山梁上起伏,突然滑落到山腳,轟隆隆滾進黃河。娘突然感到后背哇涼,一股寒氣襲來,心里顫抖了一下,扭身朝家的方向返。此時,東邊的山頭已掛上太陽,娘的腳步在霞光里跳躍。
娘沒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伯父家,急匆匆說明情況后,幾乎傾家出動,加上本家的遠近兄弟,七八個小伙子快速朝后坑奔去。所謂后坑,是黃河北岸的一座山頭,山頭往下看2000米的深處是滔滔黃水,這里山勢陡峭,荊棘叢生。人們說窮山惡水,就很貼切。植被繁茂,全不成材,只能做燒材,但是地理環境惡劣,讓人望而生畏。淺山相對安全,已被人們割伐得禿毛精光。當地人都知道,一說在后坑出事,十有八九是喪了命的。
父親的尸體連個蹤影也沒找到。他們分析說:“人滾下山掉進黃河,你去哪找!”
好在,那根光滑的桑木扁擔架在峭壁的一棵崖柏上。后生們發現后想把扁擔打撈上來,用長長的一根繩下去,環扣明明已經套住了扁擔的一端,向上一提,一個滑溜直接掉落,沒影了。年長的人就嚷:“人都沒了,要那扁擔干啥?不要再冒險!”
整整找了一天,能到的地方都到了,能夠目擊的地方全搜尋了,沒有人的任何蛛絲馬跡。老人就說:“你們年輕人都要長點記性,以后就是窮死、餓死,也不要再到這后坑來。”停了停又說,“最起碼死了得有個尸首。”
……
黃河北岸是日軍控制,南岸是國軍把守,把兩岸百姓對峙得生靈涂炭。沒多日,在幾聲叭——叭——的爆竹聲里,姐姐含著淚被一個男人接走了。出嫁那天,姐姐前腳走,母親回到窯洞便嚎啕慟哭,聲音像洪水決了堤,勢不可擋。那是積郁在胸中的悲慟突然發泄。我和弟弟一時無所適從,也跟著母親抹眼淚。后來,娘為了保全我們的性命,在陌生人手里接過3個饅頭,就讓弟弟跟人家走了。
我當時躲在娘的身后,緊盯著弟弟小毛的眼神,有點怕。但是小毛臨走給娘說的一句話,永遠在我耳邊響起:“娘,等我長大了,我一定回來給你種地。”小毛當年4歲呀,他不會忘記自己說的話,他一定會回來的。
我成了娘心中唯一的希望。一連幾年,我跟在娘的屁股后山里山外討飯,為了能夠讓我活下去,娘吃了多少苦、受過多少辱……
老劉大伯已泣不成聲了。我實在不忍老人如此動情,立馬有了負罪之感,忙起來安撫老人說:“好了大伯,咱不說了,這些年的變化老娘會高興的。”
“這我知道。盡管老娘現在仍在水里,有我在這里陪著。我的堅守,除了每年能夠讓爹娘看到豐收外,還要死死守住這個地方,等著我的弟弟回來。我堅信弟弟小毛一定會回來,他當年的眼神告訴我的。”
“這樣很好!”我突然說,“你早幾年沒有把老娘遷走是對的。你想想,小浪底是國家工程,它讓我們多少人改變了生活環境和生活質量,老娘老爹能在水下團聚,對咱們活著的人來說,豈不是莫大的安慰?”
老劉大伯突然抬起了頭,使勁看住我的臉:“爹娘團聚了?”眼里射出驚喜的光芒。
我用勁點了點頭。突然感覺如釋重負,就用欣喜的目光注視著老劉大伯。我清楚地看到,老劉大伯嘴角抽搐了兩下,年邁的臉上放出了光亮,剛剛被眼淚浸濕的臉,在陽光下顯得格外生動。
作者簡介:
葛道吉,中國作協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河南省作協理事、河南省散文詩學會副會長、濟源市作協原主席、濟源市文學藝術創作研究會主席,原《濟源文學》主編,河南省濟源職業技術學院特聘教授。在《人民文學》《人民日報》《莽原》《飛天》《散文選刊》等發表作品400萬字,出版作品集10部,數十篇散文入選全國初高中語文試卷和校本讀物,散文《1300年前的一粒種子》獲第六屆冰心散文獎;散文《沁園春》獲《莽原》2020年度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