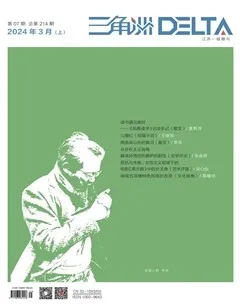特殊語境下的人格自我認同與再生
王晨
嚴歌苓塑造了眾多典型而深刻的女性形象。她們大多在日常生活的運轉中扮演著平凡角色,并于特殊語境下強烈地受到社會風潮和輿論的影響,深入社會所賦予的角色之中,壓抑本我人格的天性。本文以嚴歌苓《白蛇》中兩位女性角色孫麗坤與徐群珊為例,剖析身處特殊語境之中的兩位女性的人生軌跡,代表著社會輿論場牽制中,大眾思想固化、刻板印象禁錮和極高的社會道德要求壓制之下的女性被迫選擇的生存結局。
特殊語境中的三重人格沖突
在孫麗坤的回憶文字中,未受到約束的年輕歲月,其實她的本我人格起著支配作用。還未被社會目光鎖定的自由舞者孫麗坤是舞蹈界的紅人,自編自演的舞劇“白蛇”紅遍大江南北,對舞蹈充滿熱愛的她醉心于藝術,將靈魂賦予藝術,為了學習蛇的舞感與蛇藝人交流,與蛇去貼近距離,她純粹、獨特,滿含著真情,具有強烈的愛與欲望,排練舞蹈時她可以身心投入,忘卻一切,完全陷入角色之中享受愛與欲帶來的快感。孫麗坤的本我是純潔而純粹的,一心跟隨性情的她始終任由本我的操控,沒有約束和控制,這才使其在自我誕生后,深陷于本我、自我與超我的三重沖突中備受煎熬。
孫麗坤這一形象始終是處在壓抑自我的環境之中的。首先是在空間縱向的變換與時間橫向的流變中對個體的禁錮;空間上,孫麗坤前期被關押于歌舞廳的倉庫之中,處于所熱愛和習慣的舞臺環境的反面,后期她被轉移到醫院之中,醫治本就不存在的精神上的疾病,與她在醫院中高漲的愛與欲的熱情形成強烈對比,醫院之醫對于愛之熱而言無疑更是一種壓抑,這是空間強加于孫麗坤的身體的禁錮。時間上,孫麗坤將最好的舞臺留在了過去,而青春卻在被無故關押的日子里白白消磨,外表上的不加修飾和身體發福這些越發明顯的變化,潛移默化地打壓著她的斗志和精神,對過去執念的徒勞使舞者慢慢放棄了自己的舞臺身份,從屬于社會和輿論賦予她的新的社會身份——行為放蕩、有傷風化的美女蛇,這是時間對孫麗坤精神的摧殘和折磨。空間與時間的交織形成了一個看似一直在變化、實際卻始終未變的場域,工人的臆想、女看守的猜忌和妒忌、社會大眾的刻板印象最終成為培養孫麗坤受到壓抑的自我出現的社會的話語場。
社會話語場是孫麗坤三重人格沖突和博弈的場域,是社會與群眾對孫麗坤的猜疑,監視,主觀臆斷和道德約束催生出了孫麗坤充滿矛盾的自我。在特殊時期,孫麗坤的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群眾嫉妒的、猜忌的、羨慕的火焰將孫麗坤的摩登大樓焚毀,她不再是魅力無限的白娘子,而成了淫穢的腐化的美女蛇。處于社會生活中的人們終于可以將自己的艷羨、妒忌和望而不得全部轉化為毀滅的緣由,盡情向落魄的“胖白蛇”施以憎惡的、輕賤的目光。在這種社會的指控、排擠和輕視之中,孫麗坤的本我追求受到了強勢壓制,她越發習慣旁人所給予自己的美女蛇角色,并且在社會的指控中,她的行為和思想越發轉向了社會期待的狀態,迎合著社會話語想要將其踐踏與毀滅的愿望。在此刻,孫麗坤的自我在極端壓抑的環境中產生,并成了她的一個丑陋而堅實的面具。在外她就是那條狡猾的、淫亂的美女蛇,對抗民工粗鄙之語時可以無所顧忌地使用輕佻言辭,對待不合情理的要求可以熟視無睹、毫無羞恥,她可以不在意外表,不維系身材,可以隨意抽煙和罵人,終于在世俗的唾罵聲中活成了世俗期待的樣子,社會話語得到了滿足。而孫麗坤本人卻對這樣的自我產生了深深的厭惡,她的精神包袱是社會用道德層面的罪與罰將其規范成的“惡人”形象,在一次次的指控中、閑言碎語中甚至是認罪書的反復確認中,她被逼迫著接受了這個身份,順從了環境與話語,使其被困于這個壓抑著的自我中麻木度日。
徐群珊的出現喚起了孫麗坤對于本我的記憶,使她的自我與本我發生了沖突。徐群山與孫麗坤之前接觸到的男性不同,她溫和謙遜、禮貌體面,她喚起了孫麗坤心底沉睡了很久的愛與欲,能夠看到孫麗坤壓抑多年的自我的本體,她的愛可以忽視孫麗坤消極自我的丑態,而是直面她最真實的本我欲望,給予她靈魂上的滿足,吸引她的沖動和欲望,使得孫麗坤在與其相處的過程中發生了轉變,本我占據上風,重新練習和盡力打扮,重新去做一個美人而非粗人。在徐群珊的愛中,孫麗坤滿足了本我欲求,實現了自我認同,她認識到無論壓抑或是順從,自己的骨子里始終是渴望愛的白素貞。
而一切在謊言被揭開之時再次發生了逆轉,徐群珊的出現使孫麗坤的超我開始發生作用,對本我進行約束,并異化了其自我。孫麗坤的“發現”、徐群珊的暴露使她的幻想瞬間破滅,世俗植根于腦海中的觀念和社會盤深的教化不停宣判著這段感情的錯誤,深陷于愛與滿足的孫麗坤進入了超我與本我、自我的三重掙扎之中。此刻,孫麗坤的自我既是萬人唾罵的美女蛇,又是即將重返舞臺的養病藝術家,她難以擺脫欲望本我的控制,始終與珊珊保持著親密的關系,同時受到自我的壓抑和超我的規約,只能夠將珊珊安排為妹妹的角色,在珊珊結婚之時任性一鬧而最終也只得作罷。在最后的掙扎中,社會規制中的超我壓制了放浪形骸的本我,同時改變了純粹的自我人格,孫麗坤在這場掙扎中完全跳出被囚美女蛇的丑態,自然順應社會話語場再一次賦予其的新的藝術家身份,完成“蛻變”重生,在放棄了愛與欲望、真與情后,選擇戴上另一種面具,溫柔端莊、勤儉持家,成了德藝雙馨的新文藝工作者,異化為另一種白蛇而實現自我的再生。
孫麗坤的掙扎體現在其不同的人生階段,但其自我始終是社會話語和時代環境強加于其身的枷鎖,是壓抑其本我的源頭,三重人格的斗爭與沖突更是體現其精神困境中充斥的矛盾和掙扎,最終于這樣無盡的壓抑作用之下,孫麗坤選擇了異化,她無法選擇、也不敢去選擇本我,只能遁入更深層次的壓抑之中,放棄本我的追求,尋求短暫的自我與超我的和解。
異化中的人格和解
徐群珊是白蛇中的一個暗線人物,其身份具有迷惑性,一個個體,兩重性別和兩個名字,是她人格中對立而又相互融合的兩重。作為受到本我支配的徐群珊自由、不羈,向往灑脫而不問世俗的生活,追求純粹的美,享受欲望被無所顧忌地滿足的過程。但相對比于孫麗坤直接的身體和社會話語禁錮,徐群珊的壓抑更來源一種潛在的,大環境的壓迫感,這是時代的使命感所生發出的對于廣大普通女性的禁錮感。徐群珊的父母是為國做出杰出貢獻的科學家,她作為英雄的后代,被父輩的榮光包圍,同時代中的其他青年一樣,她做知青,參與勞動,上山下鄉,完成一個優秀的女青年應該完成的使命,在社會的期許中塑造了一個乖巧懂事的自我。
但徐群珊的特別之處在于,在這場自我的虛假表演中,這個懂事的自我始終由本我所控制。徐群珊天真爛漫、不羈灑脫的個性使她看不得社會虛情假意的鬧劇,看不慣社會勞動女性千篇一律的樸實能干、任勞任怨,相反地,骨子里對美與欲的渴望讓她從小就被白蛇的敢愛敢恨、任性妄為所吸引。徐群珊的自我在本我的支配中開始異化,這是對于社會所賦予自己的角色進行無聲的反抗,她梳寸頭,看禁書,做事不守章法,離經叛道,偷偷做著社會所不容的事情,愛著社會所不容的人,甚至想要拋棄上天強加給她的女性身份,重新以男性的身份加入社會。在這場本我嘶吼著的斗爭中,孫麗坤的愛讓她發生了轉變。孫麗坤愛的正是徐群珊的本我,是追求真實的,真誠而赤誠的那個靈魂,孫麗坤揭開了徐群珊以男性身份包裝自己、反抗社會的面具,能夠透過她異化的自我發現她深深隱藏并保護起來的純粹的愛意和人性之美,這也讓徐群珊愿意卸下自我防備和偽裝去面對眼前人,也面對那個無能為力的自己。在這場愛的鬧劇中,徐群珊達成了自我與本我人格的和解,放棄了異化的自我,跟隨本我的呼吁。
自我的再次異化像是徐群珊的一個玩笑,在孫麗坤逐漸回歸人生的正軌后,徐群珊渴望真實的,留戀于純粹之美的本我得到了滿足,而那個她深愛著的、同樣異化著的獨特的靈魂已經在社會的吸納后消失不見,相互糾纏的游戲結束了。徐群珊的本我開始對曾經異化為社會邊緣的自我產生懷疑,是否歸順才是無路可走之時最好的一條路?于是,珊珊選擇離開了孫麗坤的世界,她的自我最終還是選擇了接受社會道德的約束,她在掙扎后平靜接受了二次異化,放棄本我的堅持與反抗,成為超我歸順的樣子,最終走入社會與自我的雙重壓抑之中,以嫁為人婦的方式獲得新的社會身份,融入社會生活,達到新生,獲得社會對自我存在的肯定,實現自我認同。
徐群珊的異化始于時代與環境的壓抑,終于自我的壓抑和妥協,在時代的悲劇面前,個人的反抗過于渺小,結局終為定局,從徐群珊到徐群山是她異化的堅持,而從徐群珊到珊珊則是她異化的服從,她的人格在幾度扭曲之中屈從于壓抑,在壓抑中實現了和解。這是社會的無奈,更是特殊語境之下時代與女性的悲哀。
互為鏡像的雙向認同
孫麗坤與徐群珊之所以能夠相互吸引,是因為她們能夠相互救贖、相互認同。在兩個個體在陷入各自的人格沖突中時,她們彼此都成為雙方享受本我愉悅、感受自我蛻變和接受自我異化的重要一環,彼此角色的缺失就無法達成本我的滿足,更無法做到對自我的認同與和解。
她們兩人都犯了“錯”,一個錯在十指不沾陽春水、只顧修習魅術鉆心于無用之美;一個錯在不愿融入集體,不具女性之溫婉勤勞。她們錯在與社會格格不入,沒有社會期待的女性的樣子,所以得不到社會的認同。唯一能夠得到認同的途徑就是自我的單向認同,但長期生活在壓抑的話語和社會場域之中,飽受著非議與控訴,無論是孫姐還是珊珊,還是任何的女性都不可能有這樣強大的靈魂力量,所以她們選擇了用男性的視角來成全自我認識。孫麗坤在年輕軍官徐群山的眼中找到了自我存在的價值,釋放了壓抑的本我,通過男性的審視和青睞實現了自我歸屬;徐群珊假扮男性,通過性別的倒置去驗證自我存在的意義,二人皆是渴望通過男性的身份證明自己、釋放自己,從厭惡自我到接受、認同自我,這深刻地體現出女性在壓抑中不得所求、無路可走的困境,以及社會規約、刻板印象和輿論話語對女性的摧殘和折磨。徐群山的出現給了兩個人救贖,一個不存在的客體,卻傳遞著真情與真愛,這更是對社會與時代的諷刺,彰顯著時代的悲劇性。
孫麗坤與徐群珊的羈絆不止于相互認同,她們雙方都是彼此理想中的樣子,都是彼此本我不受抑制地想要去追求的東西。孫麗坤的白蛇肆意舞動,愛得張狂,即使接受世俗的審判與懲罰也要愛個轟轟烈烈,這是徐群珊所期盼的不拘禮法、不受束縛;徐群珊的愛熱烈而真誠,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阻礙,永恒而赤誠,這是孫麗坤所向往的、不曾得到的偏愛。她們在這段荒唐的關系中編織了一個夢境,它好像一面鏡子,映照出自己最真實的樣子,也映照著自己的貪戀和欲望。在這段關系中,二人越陷越深卻又越來越清醒,對本我的欲望越發不可收拾而潛藏在意識之中的社會道德對其的控制也就越強烈。最終,鏡像的兩個自我走上了殊途同歸的道路:異化的徐群珊再次異化,妥協于社會的期待,甘為洗衣做飯的勤勞人婦;擺脫一層壓抑的孫麗坤再次走入了新的壓抑,異化為賢妻良母的藝術家形象再次活躍于大眾的視野。
兩種自我的再生,看似是實現認同后的重生,實際則是受到不斷壓抑和控制的本我的逃避,通過自我閹割進行更深的壓抑,去除人性本真的追求和向往,這是特殊語境之中社會、環境與時代強加于女性的,甚至是人性的摧殘和束縛,是對于女性追求平等、多樣個性和自由生活狀態的愿望刻薄冷漠的駁斥和控制,女性感性而真誠的靈魂被迫變得機械和“理性”,最終不斷地自我異化。事實上,在脫離特殊語境的控制后,女性人格得到了極大的解放,女性能夠更加自信地追求多樣化的人生,轉而竭力擺脫社會輿論場的控制與束縛,從而能夠保留心的本真,試圖推動本我、自我與超我的三重人格實現和解,減少異化,這也是時代付之于女性的希望,促成女性真正的蛻變,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社會認同與自我認同。
(作者單位:沈陽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