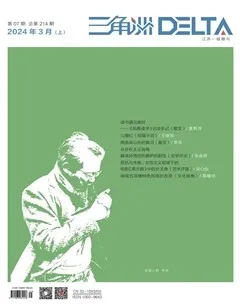世界民族音樂視角下本土化和在地化的概念界定與實例論證
岳芳吉
本土化(indigenization)和在地化(localization)是近年來較為流行的兩種學術概念,這兩個概念最早都源自經濟學領域,后來逐漸引申拓展到了眾多學科領域之中。世界民族音樂的發展經歷了早期的以歐洲音樂為標準的“歐洲中心論”到局內人局外人視角轉換之后的多元音樂理論,強調“本民族的”和“本我的”文化已經成為世界民族音樂的學科內涵。因此本土化和在地化概念也成為該學科熱議的論題之一。
本土化與在地化之概念界定
本土化又稱為本地化,在經濟學中意為跨國公司為適應東道國的生產經濟活動而淡化企業的母國色彩使其成為地道的當地公司的過程。放在更廣泛的理論范疇內,本土化即事物為了適應當前所處的環境而做的變化,突出表現于入鄉隨俗這一特點。因此本土化更像是某一產品進入特定地區后自然而然演變后成果的體現,是東道國對舶來品的吸收與轉變。
在地化是相對于全球化(globalization)而來的另一種趨勢和潮流。在經濟學中是指一個地區或國家,任何一種經濟或商品流動,必須適應地方需求,才有可能加速發展。近年來在地化理論逐漸在不同的學科領域中流行起來,成為當代社會科學研究領域非常受關注的兩個相互關聯的關鍵詞,在中國社會語境下,與在地化理論相關的研究覆蓋了商業、教育、藝術、體育等多種學科門類,尤其是教育、鄉村教育相關的在地化研究涌現出了大量理論成果。在地化理論和全球化理論的提出離不開身份認同概念,在普遍的研究理論中全球化與在地化概念常常與 “身份” “認同”等概念一道構成具有較好的解釋力的學術概念。全球化和在地化通常用于解釋社會文化變遷的現象,而社會文化的變遷往往伴隨著人們身份認同的變遷。今天,全球化和在地化發展出了一種混合的觀念——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它直接指涉全球化、在地化的同時并存及相互影響特質。
本土化與在地化之辯證關系
從理論層面來看,本土化、在地化之間的關系由兩種不同的概念認同,一種觀念認為它們的含義是完全等同的,即“本土化”就是“在地化”。另一種觀念認為這兩種概念在其內容層面有所差異。
首先,在學界主流觀念認為“本土化與在地化是同一名詞localization的不同譯法。”部分學者將在地化(localization)翻譯為“本土化”“地域化”“在地化”或 “地區化”,多強調立足本地和保有個性。此類觀念認為localization無論在中文如何翻譯,其概念都是相較于globalization而言的。前者更加強調個性出發,著重于考慮有沒有采納適應保留當地的個性特征,從而實現自我的發展,而后者則是注重于“一元化”的意識,將全球的文化發展趨向于統一化的程度。但它們的實質都強調關注于新事物在地方的一種為自身發展所產生的變化。
第二,盡管將在地化和本土化視為同一概念的觀點已經占了學術界很大的一部分,但是還有一些學者在此趨勢下有獨到的見解,提出了“本土化與在地化是兩種完全不同概念”的觀點。依據《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中的定義,本土化強調所有權(belong to),而在地化則涵蓋了所有權或相互關聯(belong to or connected with)兩層含義。換言之,本土化本身是一種過程的體現,雖然很難界定是否完成了本土化這一過程,但如果完成了本土化這一過程之后,這一事象就有了一個文化的從屬關系。正如中國揚琴的發展本身就是一個本土化的過程。揚琴源自中亞阿拉伯地區,由于傳入中國之后在中國不斷蓬勃發展,形成了多個風格流派,是一種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樂器,中國揚琴成為世界揚琴體系中代表性的一支。而在地化并不局限于一種文化吸收同化的過程,更多地體現一種“適者生存”的關系,只要與當地的文化有相互關聯性,并因此得以存活,就可以認為其完成了在地化的發展。因此,本土化和在地化的區別之處在于本土化是一種“轉換過程”,在其觀念上更多地偏向于融入當地(本地者歸返鄉土)的過程,從結果向前追索,本土化的過程是事象在當地取得好結果的必要前提,是主觀上的必要條件;而在地化闡述了一種適應性,突出融入當地(外來者融入所居地)的所需要的先決條件。強調能夠得以發展的事象本質與當地屬性相關聯、相適應,從結果向前追索,取得好結果的前提是在地化這一規律,即適應者、關聯者得以發展,強調客觀上的必要條件。
在地化和本土化具有辯證統一的關系,它們是同一事物發展過程中不可分割的兩個部分。雖然就本土化和在地化之間的關系究竟是相同還是相異的仍不能蓋棺定論,而是處于爭論的階段,不可否認的是在全球化日益發展的進程中,以本土的、在地的文化為研究視角,推崇“多元化”,反對“一元論”的理論具有極高理論和實踐價值。對于音樂事象的流變來說,在地化是與全球化潮流相反的發展規律,音樂事象想發展得更好就需要實現本土化,可以說在地化是本土化的前提,本土化是在地化的延伸發展,二者存在著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辯證關系,它們都存在于事物完整發展過程中,只是主要的體現階段不同,因此我們在討論事物的時候不能將二者抽離獨立討論,而是要討論是否滿足在地化的前提,是否完成本土化的過程。由此可以預見,作為同一事物的不同階段,這兩種概念在世界民族音樂學科理論中具有一定的學理價值,世界音樂的諸多發展實例體現了本土化與在地化的過程。
世界民族音樂在地化與本土化實例分析
從理論層面來看,外來音樂事象如果想要在當地落地生根必然是過程性的,外來的音樂事象落地本土之后,首先會經歷被小部分人認識并接受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外來音樂事象還基本保留著其最原始的音樂形態,并與其屬地文化產生著極大的關聯,這一時期的外來文化最需要的是被接納,才能生成一定的生存空間。當外來音樂事象在傳播與發展一段時間之后,形成了一定的規模,伴隨著越來越多的受眾,為了更好地融入當地文化,外來音樂事象開始積極吸收當地文化特色,經過不斷地“改良”之后,外來音樂事象成果完成本土化進程,成為具有本土性和外來性雙重特性的音樂類型。
從實踐層面上來看,本土化抑或是在地化都是世界民族音樂發展過程中的客觀規律之體現。隨著大航海技術的發展,世界音樂文化大交融成為音樂事象流變的特征,部分音樂為了適應新的生存環境開始依據當地的文化特色產生一定的更新變化。相對于早先較為流行的全球化理念,今天學界似乎更加注重于對文化本土化和在地化的研究,著重強調地方文化和地方特色,民族文化認同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
放眼于世界民族音樂世界,民族意識也有諸多體現,其中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歐洲小提琴傳入印度之后的“印度化”。小提琴本是歐洲的一種傳統樂器,無論是從演奏技法、音律音位還是持琴姿勢上都可以說是完完全全的“歐洲血統”,但是當小提琴傳入印度之后,卻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最具有顛覆性的變化就是持琴姿勢由原先夾在下頜和肩膀之間的演奏方式變成了頭腳顛倒,將琴身抵在肩上,琴頭靠在腳上演奏,這種180度的反轉成為印度小提琴最具代表性的特征。第二大變化就是小提琴音律的改變,由十二平均律的調音法變成微分音律調音法,這使得小提琴音樂說起了地地道道的“印度話”。從持琴姿勢的轉變到音階調律的變化,印度小提琴漸漸具有了“符號化”特質,成為印度傳統樂器的代表,這種標志性特征也生動體現了在地化發展要充分地適應當地文化環境。西諺說“身在羅馬,行羅馬人之行。”入境隨俗,尊重包容,才能同體共生。歐洲小提琴印度化就是外來音樂事象本土化和在地化發展的生動實例,不論小提琴在其歐洲老家的民間音樂中是何種身份,到了印度換了一個新的文化培養環境之后,小提琴隨之產生了突破性的變革。這種變革離不開印度音樂家對印度傳統音樂文化的熱愛以及忠實于本土民間性音樂特色的態度,貫徹將外來文化從“兼收并蓄”到“為我所用”的理念,因此也體現出了本土化和在地化對于世界音樂發展所產生的積極影響。
歐洲小提琴遠渡重洋到達南亞地區,作為一種陌生的異域文化象征能夠被那里的人們所接受并學習其演奏方式,使得自己能夠在南亞地區留存下來就體現了歐洲小提琴的在地化過程,然后,隨著歐洲小提琴受眾逐漸擴散,為了能夠更好地融入印度音樂,歐洲小提琴發生的一系列翻天覆地的變化逐漸體現了其本土化的過程。可以看到,在一類音樂事象的傳播與發展中,不同的階段體現了二者不同作用,二者缺一不可。
作為中國的世界民族音樂學習者,我認為在地化問題包含兩個層面,一是對傳入我國的外國音樂事象如何合理接納吸收,二是在吸收之后如何發展將其為我所用,在它們的發展中體現出在地化的特色。就如朝鮮族民歌《阿里郎》在中國的發展一樣,生活在我國東北地區的朝鮮族將朝鮮的民歌《阿里郎》帶入了中國,并且發展出了中國土生土長的《阿里郎》音樂以及“阿里郎演唱團體”,而且這一團體還反向輸出,在國際上贏得了一大片的粉絲的喜愛。這一過程反映了“阿里郎中國化”可以成為一個典型的在地化發展實例。《阿里郎》之所以能夠成功離不開它的發展過程中緊貼本土文化特色,汲取中國文化土壤中的養分,實現極強的中國文化認同。
但不可忽視的是,對于外來音樂落地發展問題,若是一味地為發展而去進行在地化和本土化,忽略了音樂事象本身的特色,音樂可能會失去其天然的美和創造力,因此也不能忽略更加致力于保留音樂核心的本我要素,因為本土化與在地化的本質是適應的過程,代表著本源要接受限制或者加入本身不需要的元素,并非事物本身的自然發展,因而除了傳播與發展所必要的改變外,過度的修飾與變化對事物本身會帶來傷害,違背了我們對于美本來的追求,失去了初心。因此,作為東道主,對舶來品更多的應當是篩選,篩選適當的音樂事象進行適度的本土化;作為傳播者,我們也要依照音樂事象本身選擇適合傳播的土壤,適當進行改編,有限地提高事象的在地化能力。一言以蔽之,吸收外來做到尊重與包容,傳播自我要保持足夠的文化自信。
中國語境是中國學者不能回避的問題,強調中國語境下的本土化和在地化是中國音樂學發展的導向標,在諸多音樂事象不斷吸收中國本土文化的發展之中,也體現了中國特色文化語境的廣博的文化承載力和高度的文化價值認同。當前我國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階段,我國大力推動“四個自信”就是為了弘揚民族文化認同意識,增強民族文化認同感。隨著學科不斷發展,研究者更多地開始注重如何將外來的、全新的文化與本土的、固有的文化更好地結合發展,從而實現一個文化的雙向推動關系。本土化和在地化無論是對外來音樂落地發展還是對于本土音樂內部更新都具有積極的影響意義,但是否能經歷時間的考驗,是值得研究者繼續探索和亟待解決的問題。因此音樂事象在文化變遷的過程中,應把握好發展的風向標,建立他者信賴的文化觀。本土化與在地化是我們不可或缺、不能忽略的課題,把握本土化界限,塑造在地化能力尺度都需要我們持之以恒地探索研究。文化自信與文化尊重的界限也需要我們在這過程中去進一步規范。
作者簡介;
岳芳吉,女,首都師范大學在讀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民族音樂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