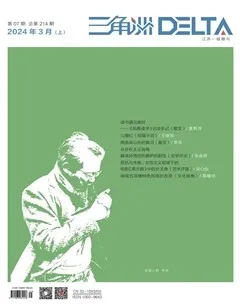“心安理得”的拉德布魯赫公式解
唐靖東
“心安理得”是一種良好的精神狀態,也是個人正義觀的最高追求,在每個具體個案的正義與否的判斷中都能達到這一理想狀態,是減少內耗與促進自我價值實現的必由之路。規范—分析層面的拉德布魯赫公式的本意在于解決法的概念問題與法的效力問題,也即探究文化相對主義和倫理學相對主義下“法”的有關問題,本文語境下的拉德布魯赫公式主要是在描述層面展開,也即探究其在因果命題和免責命題下的產生原因。本文意在通過解構“心安理得”的法哲學概念,解讀“心安理得”在拉德布魯赫公式下的邏輯傳導,討論“心安理得”與個人正義觀的互動,最終說明“心安理得”如何作為一種追求影響個體的正義觀以及行為。
“拉德布魯赫公式”是大陸法系的代表成就之一,也是當今自然法和法律實證主義經過修正發展的一種融合。對于拉德布魯赫本人來說,他的思想經歷了從康德主義到自然法學的轉變,其中雖然尚存爭議,但不影響以“心安理得”的自然法思想去分析拉德布魯赫公式的立場。對于整個“公式”來說,相對主義的良心觀是和“心安理得”的最大連接點,以此為契機發掘拉德布魯赫公式在當代的進一步適用可能就有了出發點與落腳點。
“心安理得”的正義常數
常數是數學公式中的一個客觀存在的穩定值,不隨其他自變量而變化,對于“心安理得”來說,正義就是這樣一個常數:無論個案如何變化;無論內心“心安理得”的自我論證路徑為何,所求皆為“心安理得”之狀態,此間正義會作為求的此狀態的不變之此常數,無論結果如何,正義總是不變的。拉德布魯赫公式(下簡稱公式)在描述層面下是解決服從與免責的問題。從邏輯上來說,“心安”是服從與否的前提,一旦個體作出了令其自己“心安”的決定,就幾乎再無要素可以在非實證法的層面上改變其決策。個體很容易達到“心安”的狀態,但這樣的狀態卻并非一定正面的。從規范倫理學的立場來講,對“心安”的概念作答有兩種根本方向性的選擇:規范個人主義將個人作為第一要素,作為判斷正當倫理義務的出發點,這里的個人指的是自覺的社會個體;規范集體主義則更加強調道德評價需要在某個集體中找尋證成依據,對義務的證成不應該回到某個具體的個體之中去。對于“心安”來說,規范個人主義對于強制性的道德標準有天然的抵制效果,能夠強調個人在道德決策中的主體性和自我決定權,這樣的自主性可以鼓勵個人提高道德意識和道德選擇能力,是個人自覺自范能力的要求與結果;規范集體主義則對群體利益有益處,可以預防群體性道德問題。從現實來看,規范集體主義更適合當下對于“心安”的解釋,即,共同性道德準則目前應該成為“心安”的標準,社會和群體利益應該作為“心安”的目標,社會責任應該成為“心安”的追求。在道德上應該得到考量的個體的欲望或者利益在實現過程中越是依賴其他關聯者,這一個體就越是需要對個體本身作出相對化處理,共同體本身也需要作出更加契合共同體目標的決定,個人欲求和集體欲求的平衡應該以帕累托最優為目標,以尊重個人尊嚴為原則,以權衡兩端的利益為手段。所以,現階段追求的“心安”是基于集體價值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心安,是在實踐中所有實現自己利益的情形下都能實現利益平衡的心安,更是個人自覺的心安。
之所以先講“心安”再說“理得”,主要是因為這個組合的順序是必須與情感的反應與規范要求相適應的,如果我們先講“理得”,再講“心安”,尤其是當“理得”的理解過于限縮時,就可能導致規范與“心安”的割裂,兩者可能會演變為獨立的域,故而對“理”的理解就十分重要。“理得”毫無疑問指符合某種“理”,在一般的語境下,符合法的“理”可以被理解為符合法的全部淵源的精神或者規定,但必須在先“心安”的情況下理解“理得”,顧及二者的關系,也即,心所安之處與理所得之處必須有一定的共性,也即,在法的全部淵源之下與集體價值德性的部分重合—自然法,所得之“理”必須是符合自然法的基本正義精神的。
“心安理得”的因式分解
從描述層面的公式來看,“心安理得”可以類比拆分為因果命題和免責命題兩個因式,而這二者都圍繞實證主義而展開,故而為什么因為“心安理得”可以不為,以及這種情形下為什么能夠免責,也正是這一公式的核心命題所在。從表面上來看,“心安理得”與法實證主義存在巨大的沖突,“法律就是法律”的鐵律因為法律的客觀性和安定性使人不得不服從,“心安理得”最多可以被解釋為正義與否的范疇,并不對實證主義產生影響,因為這是憲法教義學和法的倫理問題的區分。康德將哲學認知中的主體符合客體的思考顛倒了過來,變成了客體對主體的符合,自在之物和自然之物的劃分也說明了道德領域的不可控制性,所以康德只能從形式上回答何為應為;而新康德主義則將認知問題歸納為價值與評價,沒有絕對客觀的價值評價。概括地說,康德將個人的良善意志視作一切義務的出發點,良善意志可以作為獨立于偶然性的存在,具有絕對性。康德所強調的個體的規范是普遍化的,也就是說如果個體a,b,c……所行之事x都是帶來了負面影響,那么x必然是不可為的。回到“心安理得”的語境下,普遍化的個體良善意志就是“心安理得”的基礎,可以越過,或者先于法律實證主義考慮,但這種情況的適用范圍顯然是相當狹隘的,只有一種行為x破壞了整個共同體(所有的a,b.c……)的實踐或者制度時才能以這種標準被排除掉,這無異于直接將“心安理得”等同于社會一般道德,而否認了個體的良善意志的存在,也就是說,僅憑此無法解決為什么“心安理得”是因果命題的組成要素問題,因為這無法回答價值評判和實證法的關系問題。拉氏認為,法律是人類社會實踐的產物,只有在理解其價值的前提下才能理解,基于不同的價值立場,人們對待價值有不同的態度:不考慮,例如在對自然存在展開科學研究時;評價,主體積極批判客體;牽涉,對文化的態度,也就是意義;超越,例如對應宗教活動,往往不考慮價值,進行不求回報的投入。這是拉氏面對價值的考量方式,可以看出,“心安理得”正是在評價和牽涉的框架內進行討論的,是上文所分析的正義價值在“心安理得”的狀態下的投射。拉氏明白,僅從現實中不能推導出價值,因而他用相對主義的方法將某種價值或者狀態作為前提來判斷實證法的正當性,但尋找單一的、科學的一種方法或者形態是不可能的,能夠依靠的只有個人的良心,這也意味著,“心安理得”的人們在面臨利益沖突時并不對利益本身進行選擇,而是以折中的方式,在考量價值的基礎上,以實現價值為目的,顯現出各種應然,相對主義的良知,也就是“心安理得”,可以否認法的不正義,進而解決因果命題的邏輯通順性問題。對公式的免責命題的理解本身就是限制性的,這種限制來自對法實證主義的狹義解讀,公式本身針對的是對第三帝國政權期間以及民主德國時期偏離成文法的精神甚至文字的法官們的辯護,核心也就在于免責。雖然關于免責命題的論述受到了大量的反駁,但公式的可接受性和正確性卻并不在于此,而是在于其實效性,即能否阻止不正義的情形出現。前文提到,“理得”之中的“理”是符合自然法精神的,而拉氏批判背離自然法的實證法就是不具有效力的,但從其本人的思想來看,公式本身又很難以簡單的實證主義或自然法概括。但“心安理得”和免責命題之間存在著規范懷疑主義的鴻溝,直接以上文證成的“心安理得”去尋求免責勢必會導致法制的破壞,所以“心安理得”在這里只能指向“內心的免責”,即在面對非正義之事而不去做時不會產生心理負擔。公式對于個體,尤其是并非司法裁判者的個體的作用也就在于此,自然法精神和正義觀可以成為個人勇敢面對非正義事件的定心石。個體的良善,群體的美德,自然法法理成了其最完善的判斷手段,公式的三要素在這里能夠得到完美體現,安定性因為個體的自發遵守和自然法價值的貫穿而得以保障;正義觀是以上諸要素的總和;而法的合目的性因為社會的整體和諧以及個人價值的實現而最終實現。
“心安理得”的公式求解
這一公式是“不精確”的,許多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都是不確定的,也正是因為此,公式的適用范圍相當靈活多變,這也給了我們利用公式分析“心安理得”提供了便利,尤其是本文基于的描述層面的公式。基于核心價值的“心安”與符合自然法精神的“理得”結合在一起,公式的解讀具有巨大的社會意義。公式能為良法善治提供合理標準:諸多法律價值的沖突會在立法時表現出來,立法者為了響應法律的合目的性和安定性必須積極作出回應,這樣的回應是必須兼顧法的有效性的。立法過程中立法者的個人意志會摻雜于法律之中,會導致絕對價值和相對價值的搖擺。從邏輯上來說,安定性是應該首先考慮的,之后才是正義性問題,缺乏正義性的法律會導致民眾的否認態度,也即“心安理得”地拒絕服從,一項法律只有得到良好的社會反響才具有更好的執行性與可信度,人們對法律的期待更多是應然層面的,也即法的良善價值,為了防止“不法的法”出現,人民群眾“心安理得”這一關,法必須通過;“心安理得”與公式相結合,有利于基本人權的保障。公式中的“正義”包含了人權價值,作為正義的基礎,人權能夠體現所有人的利益。當實證的法侵犯基本人權時,法的安定性就必須被突破,公民無法對這樣的實在法進行積極評價,不符合一般社會價值和自然法精神,也就是對人權的侵害。根據拉氏的解釋,對正義性的突破必須是在“極端不正義”的情況下才能進行的,并且這樣的突破是必須的。人權中的基本權利是不可扣減的,否則會損害人的尊嚴與本性,“極端不正義”本身需要在道德和理性上站得住腳,而道德判斷與知識的客觀性證成是極其復雜的,從已有實踐來看,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認為種族屠殺是“不可容忍”的對正義的違背,這樣的違背很難以對證據進行歸納,而是只能以拉氏的“更高的法”(higherlaw)來判斷,即使是以富勒的一個相對性較低的標準,即以較為明確的合法性要求的(如公開性、不溯及既往等)“在相當大程度上違背”,從結果上來說就是會對法治原則造成較大損害的。而人權中也存在一個不可侵犯的核心領域,也即基本人權。
從描述層面的公式來說,“心安理得”應該被作為最為重要的判定標準,這一標準可以證成因果命題中的評價問題,可以解決免責命題中的道德責任問題,同時這樣的標準可以作為一個促進法治和人權積極發展的動力,以這種方式解讀的正義觀將最終反哺于個人,使得個人的行動能夠朝著利于個人自我實現和有利于社會發展的方向前進。
作者簡介:
唐靖東,男,上海師范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法的一般理論、國際人權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