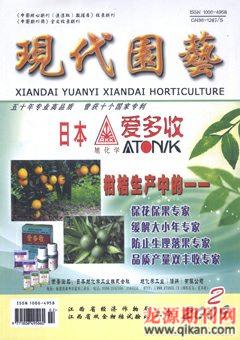有機刀豆生產技術
劉重桂 朱業斌
江西省萬載縣以茭湖鄉為中心的有機生態食品園被國家環保局授予“全國有機農產品生產基地”,成為“江南有機農業第一縣”。2008年該縣進行了有機刀豆栽培,栽培面積為50hm2,全部栽種本地常規品種,667m2產量1500~2200kg,有機刀豆加工成罐頭后遠銷歐盟、日本等多個國家和地區,銷價是傳統刀豆的2~3倍。現將有機刀豆生產技術總結如下:
1定義
有機刀豆生產技術是指遵循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嚴格按照歐共體2092/91《有機農業條例》進行刀豆生產、采收、貯藏、運輸、銷售。不使用化學農藥、化肥、生長調節劑、飼料添加劑等物質,按農業科學和生態學原理,維持穩定的農業生態體系。
2氣候條件
平均氣溫5.8~13℃,冬季最低氣溫不低于-15℃,無霜期在200天左右,年有效積溫3000~3500℃,年日照時數在2500小時以上,年降雨量700mm以上。
3環境條件
生產基地應遠離城區、工礦區、交通主干線、工業污染源、生活垃圾物等。且符合以下要求:
3.1灌溉用水水質必須符合GB5084農田灌溉水質三級標準。
3.2大氣環境達到GB3095環境空氣質量一級標準。
3.3土壤質量符合GB15618土壤環境質量一級標準。
3.4地形地塊宜選擇緩坡或山腳下的較蔭涼地塊,有利于刀豆生長。
3.5土壤條件具有3年的有機土壤轉換期,沙壤土、壤土或粘壤土;有機質含量≥2%,堿解氮≥60mg/kg、速效磷≥10mg/kg、速效鉀≥80mg/kg,符合全國第2次土壤普查土壤養分分級3級以上標準,土層深度要求在40cm以上;土壤pH值在5~7之間,地下水位1.0m以下。
3.6緩沖帶在有機地塊與常規地塊之間設置300m以上的緩沖帶或物理障礙物,保證有機地塊不受污染。
3.7轉換①常規刀豆田地成為有機刀豆田地需要經過轉換。生產者在轉換期間必須完全按本生產技術規程的要求進行管理和操作。②常規刀豆田地的轉換期一般為3年。但某些已經在按本生產技術規程管理或種植的刀豆田地,或荒蕪的刀豆田地如能提供真實的書面證明材料和生產技術檔案,則可以縮短轉換期。③已認證的有機刀豆田地一旦改為常規生產方式,則需要經過轉換才有可能重新獲得有機認證。
4播種
4.1播種期春刀豆的播種期為3月下旬到4月上旬,最佳播種期為4月初。
4.2合理配制茬口做到上下茬銜接,一般以1.5m一個組合最合理,既有利于通風透光生長良好,又有利于耕作和采摘,更有利于上下茬口的連續性。
4.3播種前要開好水溝既橫排水溝深12cm以上,防積水,做到雨停田干。
4.4施足基肥667m2用施腐熟有機堆肥1500~2000kg或沼液肥15200kg或蔬菜專用有機肥800kg,磷礦粉50kg。
4.5土壤消毒667m2用石灰75kg進行土壤消毒。
4.6種子處理下種前曬1~2天。隨拌隨下種確保安全生長;精細選種,分級播種,通過曬種后必須要選種,要把大小粒種子分開存放,分開播種,以利平衡生長。
4.7覆膜和下種在4月5日前播種的可先覆膜,在4月6日后播種的可先下種后覆膜。一般穴距為20~25cm,每穴2粒,667m2確保4400~4500穴,每穴確保2株苗。
5出苗后的管理
5.1 及時放苗如果是先下種后覆膜的一定要在剛透土就要放苗,嚴格注意天氣變化預防燒苗,如果是先覆膜后下種的,也要經常注意苗情,注意天氣,落實好各項應變措施。
5.2注意地下害蟲的危害地下害蟲主要有蠐螬、螻蛄、地老虎等,在播種時和出苗后可進行人工捕捉或者用糖醋誘殺成蟲,減少幼蟲發生量;噴施1次等量波爾多液,防治苗期病害。
6田園管理
6.1病蟲害注意病蟲害的發生發展,應及時地防治。
6.2僵苗如果出現僵苗不發、枯黃瘦小等現象的,要及時采取補救措施。
6.3不良天氣如遇大風大雨天氣,要及時護理,以免影響產量。
6.4排灌開溝排水,疏通田間排水溝,防止明澇暗漬。
7采收標準
長度不限,粗度直徑白籽的在0.8cm內,紅籽的在0.6cm內,無病斑,無風傷,無蟲體,無異物。
8貯藏、運輸
在運輸、儲藏、包裝過程中,優質有機刀豆不能與其它農產品混合。包裝材料、運輸工具應符合有機食品衛生要求。
(收稿:2008-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