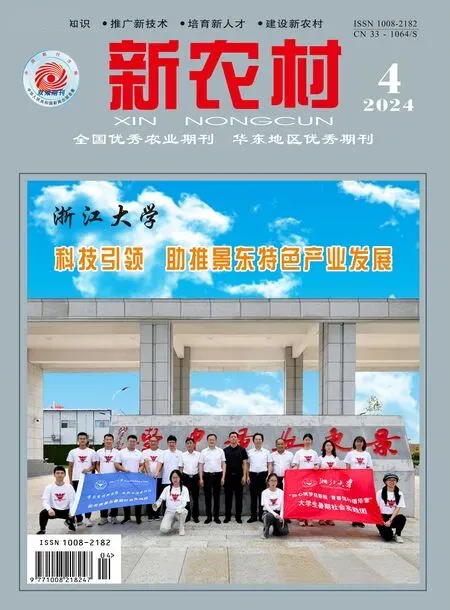進一步發揮新型城鎮化作用 助推山區縣高質量發展
浙江省建設廳(310007) 童 彤 吳 怡 翁大偉 朱 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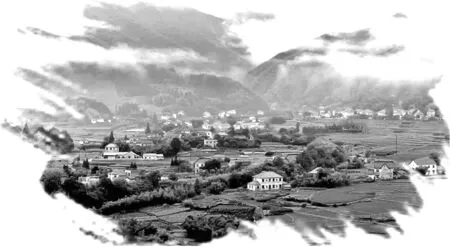
浙江的山區縣高質量發展,事關全省發展大局和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成敗。以新型城鎮化引領山區縣城鄉協調發展,加快構建山區縣高質量發展新格局,對形成山區縣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共同富裕意義重大。
1.山區縣新型城鎮化基本情況
據統計測算,2022 年浙江山區縣平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0.7%,低于全省12.7%。目前三批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中,浙江山區26縣僅開化縣入選,國家發改委公布的120 個縣城新型城鎮化建設示范名單中僅縉云縣入選。從經濟發展水平看,山區26縣地域面積約占全省的45%,GDP 不足全省10%,人均GDP 僅為全省的36.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全省的73.9%。同時,縣域經濟分化明顯,2022年26縣中GDP 增速低于全省平均的縣有7 個,增速最高地區和最低地區差距達11.4個百分點,山區縣規上工業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僅占全省的4.8%。從人口流動看,“十三五”期間山區縣常住人口占全省比重由17.23%降至15.75%,超半數縣戶籍人口下降,至2022年11個縣人口少于30萬。從城鄉建設看,“十三五”期間山區縣人均市政公用固定資產投資增速3%,城市污水處理率由88%上升至96.89%,垃圾分類覆蓋率78%以上,但農村生活污水處理設施標準化運維率僅為19.4%,城鄉建設歷史欠賬較多,仍處在由“量”轉“質”的關鍵期。
2.制約山區縣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問題
(1)土地資源稀缺與利用率低下并存 山區縣受地形地貌、生態環境、經濟社會等多因素制約,建設用地分散,發展腹地有限,集約化程度不高。隨著涉林墾造耕地政策收緊,山區縣后備資源緊缺,耕地保護壓力增大,緩坡資源有待開發。與此同時,前一階段粗放式的城市擴張,導致人口集聚度不高,建成區人口密度偏低,降低了土地利用效率。土地已成為制約山區發展的重要因素。
(2)基礎設施薄弱與建設成本高昂并存 從區位看,山區縣大多在浙西南,偏離大灣區—沿海發展帶、四大都市區等重要經濟區,縣域內外的基礎設施短板依然突出。對外運輸通道結構單一,鐵路、高速公路等重大區域交通與長三角城市群、相鄰都市區聯系不足,較低的區域交通一體化程度限制了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資源的對內輸送。在基礎設施方面,除中心城區外路網密度極低,水、電、路、氣及公共服務均存在布局不均衡、供需不匹配、可持續性差等問題。此外,山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成本相對平原更高、建設難度更大。
(3)建設階段錯位與更新發展訴求并存 除個別縣外,多數縣(區)均以“出售”建設用地指標換取調劑收益,這種“以資源換資本”的方式使得山區縣城鎮化進程嚴重滯后于發達地區,基本處在同類縣城10 年前的發展水平。相較于“十四五”期間全省0.56%的平均增速,該類縣城仍處在城市快速發展區間,未來對城市建設補課趕趟的訴求大。
(4)人口持續流出與低水平城鄉均衡并存山區縣普遍存在戶籍人口增幅收窄或降幅擴大趨勢,常住人口呈現微弱增長乃至負增長現象。老齡化引發社會活力下降,社會保障、健康養老壓力倍增,山區縣均已步入老齡化社會,約20 個縣處在深度或超老齡化區間。部分村工作人員比村民多,教師比學生多,小學陸續被撤并,甚至已無60歲以下村民居住,“未富先老”問題不容忽視。從2022 年城鄉收入看,山區縣中有近半數城鄉收入比低于全省平均,超三分之一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國平均。
(5)風貌品質不佳與資金平衡約束并存 山區縣縣城風貌品質有待提升,歷史地段保護意識淡薄,對當地人文歷史、傳統建筑風格的挖掘和提煉不深,在地化創新不足,縣域特色彰顯不夠。如部分縣重點打造的城市客廳,道路一側像城市、另一側像農村,山腳安置房建設的天際線破壞了山的輪廓線等。另一方面,各縣普遍反映,開展城中村、棚戶區改造等城市更新因錯過了政策窗口期,目前資金缺乏是最大問題,且區塊普遍難以實現平衡,各地往往以提高安置房等新建房屋容積率、增加商住供地面積等方式緩解資金壓力,這與當前城鄉風貌管控、綠色低碳發展等有沖突。
3.對策建議
(1)盡快啟動“兩會一點”,解決山區縣“動力從哪來” 建議召開新型城鎮化或城市工作會議,全面總結我省新型城市化戰略實施工作,系統部署新時代深入實施新型城市化戰略的思路目標和政策舉措。重啟省推進城鎮化工作聯席會議,強化全省城鎮化頂層設計和協調聯動,加大對山區縣的指導幫扶。盡快啟動縣城城鎮化試點,并向山區縣傾斜,為其高質量發展注入內生動力。
(2)再度打開政策窗口,解決山區縣“錢從哪來” 建議允許山區縣適度提高城市更新“拆改留”比例,并爭取國開行等政策性銀行在其城市更新抵押貸款、融資貼息、利率優惠上的支持。結合高質量發展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加快區域重大基礎設施、基本公共服務特別是優質教育、醫療資源在山區縣的布局;加大“國”字號企業在縣內投資建設比例,并適當提高省級財政補助系數;立足山區縣資源稟賦,推出特色化綠色金融產品,并在生態補償機制創新、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農村各類產權抵押擔保融資等方面充分授權,在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發行等方面給予更大支持。
(3)差異供給坡地政策,解決山區縣“地從哪來” 在“框定總量、挖掘存量、做優增量、管控流量”的土地利用背景下,向低丘緩坡拓展發展空間仍是山區縣緩解人地矛盾的必然選擇。建議將低丘緩坡地綜合開發試點向山區縣傾斜,允許利用低丘緩坡地開發70 年產權的住宅類項目,出臺相關政策適當降低占用低丘緩坡地成本。同時,兼顧城鎮布局功能優化、地方發展等需要,合理劃定山區縣城鎮開發邊界,并結合山地發展的不確定性,允許以兩年為周期開展城鎮開發邊界實施管理狀況評估調整,給予山區縣更多發展可能。按照“點狀布局、垂直開發”生態型建設要求,給予山區縣新增建設用地指標。此外,優化“飛地政策”,支持山區縣在大灣區、省級高能級平臺布局和聯建“產業飛地”“科創飛地”,并享受“飛地”空間規劃指標支持。
(4)加快撤村并鎮,解決山區縣“人從哪來” 下山脫貧、移民搬遷仍是山區縣就地城鎮化的重要“催化劑”。建議抓緊探索大搬快聚富民安居運行機制,建立涵蓋多元化資金籌措、多渠道人力開發、多途徑下山安置等政策保障,強化中長期規劃制定和目標考核激勵。省財政要建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獎勵資金持續增長機制,加大對山區縣資金傾斜;要對整村搬遷后的閑置農房再利用、安置小區基礎設施建設給予補助;立足“小縣大城”戰略,抓緊研究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擔機制,建立可持續的人口素質提升機制,構建農業轉移勞動力向產業轉移的綠色通道。
(5)持續西進數字生態,解決山區縣“發展向何去” 立足山區縣生態資源優勢,強化數字變革引領,加快全省數字新基建總體架構覆蓋山區縣優勢區域,推動5G 精品網絡、新型互聯網交換中心、數據中心等向浙西南建設進程,支持遂昌、云和等地利用仙俠湖、云和湖布局云服務器,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讓數字經濟成為山區縣建設“重要窗口”的重要成果。同時,堅持數字賦能生態建設,深化數字經濟與生態經濟融合發展,全力支持山區縣在旅游康養、生物醫藥、功能食品等領域的布局,設立省山區縣數字生態專項資金,用于培育山區數字經濟產業,著力打造“網紅經濟”“流量經濟”。支持有條件的地區積極招引頭部企業入駐,打造總部在大城市、分時在當地,孵化在大城市、轉化在當地,前臺在大城市、后臺在當地的山區縣“分時經濟”發展模式,真正實現“以時間換空間”,推動生態產品價值的實現和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