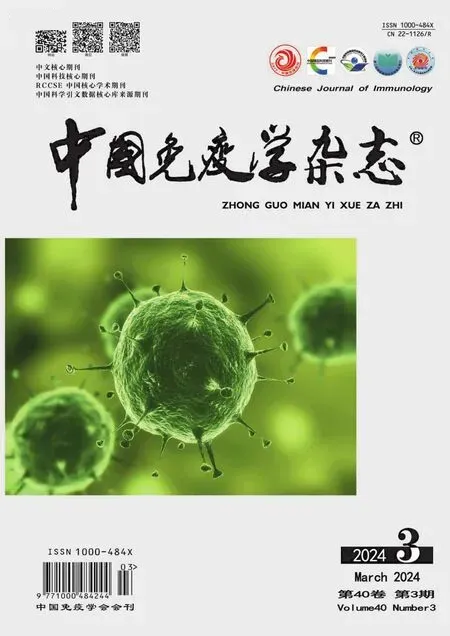lncR NA H19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調控作用及其機制
蔣志行 劉冬梅 (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盛京醫院風濕免疫科,沈陽 110022)
自身免疫性疾病是由于機體對自身抗原的免疫耐受性喪失,導致免疫介導的炎癥異常激活,進而造成靶器官損傷的一類疾病。異常的免疫應答和環境因素均可促進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發生發展[1]。
長鏈非編碼RNA(long non-coding RNA,lnc-RNA)是一類長度大于200個核苷酸的非編碼RNA。lncRNA能夠調控許多免疫細胞的生長分化,包括T淋巴細胞、B淋巴細胞、巨噬細胞、單核細胞、樹突狀細胞和NK細胞等[2],因此在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發生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H19最早于1991年被認定為印記lncRNA。它在胚胎階段大量表達,在出生后受到抑制,曾被認為只在軟骨和肌肉中發揮作用。事實上,在出生后H19參與了很多重要生理和病理過程,例如細胞缺氧、新陳代謝和氧化應激等[3-5]。隨著研究的深入,H19在腫瘤、纖維化和代謝相關疾病中的作用逐漸清晰,逐漸成為有潛力的新型治療靶點,并且有賴于其在炎癥調節中的作用,也被認為是抗衰老治療中的潛在靶點[6-9]。已有研究證實H19也參與了自身免疫性疾病復雜的病理機制,在影響某些疾病的病情發展、藥物療效和預后轉歸等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本篇綜述簡要討論了H19參與自身免疫性疾病發病的相關分子機制,并總結了幾種常見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中H19發揮功能的現有證據。
1 lncRNA H19的作用機制
lncRNA H19是H19基因的轉錄產物,由于經過了選擇性剪接,存在著多種轉錄變體。H19基因位于11p15染色體端粒附近,與胰島素生長因子2(insulin Like growth factor 2,IGF2)基因隸屬于同一個基因印記簇,該基因位點還產生miRNA(稱為miR-675)、一個反義蛋白編碼轉錄本即H19相反腫瘤抑制因子(H19 opposite tumor suppressor,HOTS)以及一個長基因間反義轉錄本(稱為91H)[10]。
H19通過參與表觀遺傳調控、轉錄調控、轉錄后調控和翻譯調控等過程發揮著重要的生物學功能,下面列舉一些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起作用的分子機制。
1.1 lncRNA H19與miRNA作用
1.1.1 發揮ceRNA調控功能 ceRNA理論由SALMENA等[11]于2011年提出,存在競爭性內源RNA(competitive endogenous RNA,ceRNA),包括某些mRNA、lncRNA和假基因,通過競爭性結合microRNA反應元件(microRNA response element,MRE)的方式調節特定的miRNA表達,這一功能也被稱為分子海綿。現有證據表明H19具有作為ceRNA競爭性結合的miRNA從而抑制其表達的分子海綿功能,例如H19通過競爭性抑制miR-124a的表達,解除了其對周期蛋白依賴性激酶2(cyclin-dependent kinases 2,CDK2)和人巨噬細胞趨化蛋白1(human macrophag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MCP-1)的抑制,最終促進了成纖維樣滑膜細胞(fibroblastlike synoviocytes, FLS)的增殖,加重了類風濕關節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的病情[12]。
1.1.2 作為miR-675的前體 miR-675是由H19第一外顯子區域編碼生成的衍生物,H19的生物學功能相當程度上是通過作為miR-675前體物質實現的。在強直性脊柱炎(ankylosing spondylitis,AS)患者的外周血單個核細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PBMC)中,過表達miR-675-5p能顯著抑制轉化生長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表達,但敲低miR-675-5p卻并不能使TGF-β的表達增加,這提示H19可能部分參與了miR-675-5p對TGFβ表達的調節,通過衍生出miR-675-5p發揮協同作用[13]。值得注意的是,H19和miR-675的表達并非總是呈正相關,如在人骨髓間充質干細胞(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BMSC)的成骨分化中,miR-675的表達隨著分化過程逐漸下調,并未與H19的表達上調保持協調一致性,這可能與H19 RNA轉錄本上存在miR-675特異性結合位點以及某些RNA結合蛋白的作用有關[14]。
1.2 通過H19/IGF2印記基因簇發揮作用 H19/IGF2印記基因簇中H19來自母本等位基因,IGF2來自父本等位基因。H19基因上游4 kb處的差異甲基化區域(differentially methylated region,DMR)或印記調控區域(imprinting control region,ICR)的甲基化水平影響H19和IFG2的相對表達,使得IGF2和 H19之間存在復雜而緊密的聯系,并各自通過表觀遺傳的調控方式調節和影響對方的功能[15]。既往研究發現RA的關節破壞存在不依賴T細胞以及以FLS細胞異常增殖為中心的病理機制。RA患者部分FLS細胞中IGF2印記丟失(loss of imprinting,LOI)導致IGF2高表達,有助于在這種機制下促進細胞增殖,促進滑膜增生,導致關節破壞[16]。
1.3 與靶基因結合抑制其轉錄 H19可與DNA通過堿基互補配對的方式發揮作用,抑制靶基因的轉錄。如在系統性紅斑狼瘡(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患者的BMSC中,H19與IL-2基因直接結合抑制其轉錄,從而降低了該基因的表達。實驗表明H19過表達可以明顯下調BMSC細胞中總IL-2水平及其活性,而抑制H19產生則可以明顯促進IL-2表達,進而實現調節Treg細胞分化的目的[17]。
1.4 與蛋白質結合發揮調控作用 H19可與蛋白質直接結合以調節其活性,間接實現對其下游靶基因表達的調控。許多自身免疫性疾病都伴隨著微血管生成的病理改變。在人羊膜間充質干細胞中,H19與甲基轉移酶EZH2相互作用,促進其在血管生成抑制劑VASH1基因的啟動子區域募集甲基,增加VASH1的表達和分泌,抑制血管生成[18]。
2 lncRNA H19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作用
2.1 RA 既往研究顯示H19在RA患者的滑膜組織中高表達,在PBMC中低表達[19-20]。H19在RA中具有調節炎癥的作用,一方面H19通過下調FlS細胞中miR-103a表達,抑制盤狀結構域受體2的功能實現緩解RA炎癥反應和關節破壞的目的,從而起到抗炎的功能[21];另一方面在TNF-α的作用下,H19加快了MH7A人成纖維細胞樣滑膜細胞中酪氨酸激酶激活蛋白1(tyrosine kinase activator protein 1,TKA1)的磷酸化,進而激活NF-κB和JNK/p38 MAPK等炎癥通路,促進了多種炎癥因子釋放,起到促炎作用[22]。除了依賴經典的炎癥途徑,H19還可以通過上調組蛋白去甲基化酶KDM6A的表達促進M1巨噬細胞極化,加重RA的關節炎癥狀[23]。此外,在FLS細胞中過表達H19時,組織金屬蛋白酶抑制劑2的表達顯著增加,表明H19參與了RA滑膜組織中細胞外基質的重建[19]。進一步研究發現,H19通過充當miR-124a的海綿調節CDK2和MCP-1的表達,調控了FLS細胞增殖[12]。值得一提的是,迄今為止還未發現H19的單核苷酸多樣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與RA的遺傳易感性有關[24-25]。
2.2 干燥綜合征(sjogren syndrome,SS) SS主要累及淚腺、唾液腺等外分泌腺體。SS患者唾液中H19 ICR的甲基化水平降低,且降低的甲基化水平與補體C4水平負相關[26],提示H19可能與SS發病和病情活動有關,有望成為診斷SS的新型生物標志物。與在唾液中觀察到的H19 ICR甲基化水平降低一致,SS患者PBMC細胞中H19表達較健康人明顯增加,但可能是樣本量較少的原因,并未觀察到小唾液腺中H19的表達存在顯著差異[26]。
2.3 SLE 與健康人相比H19在SLE患者PBMC細胞及其CD4+/CD14+亞群中的表達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但在患者血清和BMSC細胞中的表達則明顯增加,并與SLE疾病活動指數(SLEDAI)呈正相關,表明其作為評估病情活動新型標志物的潛力[27-28]。在SLE患者體內,H19介導了BMSC增殖和遷移,并最終促進其凋亡,因此影響Treg細胞增殖和分化,破壞了BMSC介導的Tfh/Treg細胞平衡,加快了疾病的發展,這個過程在一定程度上與H19抑制IL-2的轉錄有關[28]。此外,H19現被認為是miRNA Let-7家族的重要調節劑,而SLE患者BMSC中Let-7f的表達降低會觸發Treg/Th17失衡,這種失衡也與SLE病情惡化、炎癥反應加劇有關[29-30]。
2.4 AS AS患者的主要表現是骶髂關節和脊柱附著點炎癥。有研究發現AS患者PBMC中高表達的H19通過與miR-675-5p/miR-22-5p相互作用調控維生素D受體(vitamin D receptor,VDR)的表達,促進了IL-17A、IL-23等炎癥因子的釋放[13]。由于VDR會影響AS患者骨骼的代謝以及炎癥過程,H19與VDR表達的關聯性可能揭示了其參與AS發病機制的重要途徑[31]。此外,AS的強直癥狀被認為是炎癥刺激下反復骨破壞和骨再生的產物,H19可以通過多種途徑促進成骨細胞分化和骨再生[32],因此其在AS發病中的潛在病理作用值得進一步探究。
2.5 特發性炎癥性肌病(idiopathic inflammatory myopathies,IIM) IMM是一組系統性自身免疫性結締組織病,可大致分為多發性肌炎、皮肌炎和包涵體肌炎。抗氨酰t-RNA合成酶抗體陽性的IIM患者常被稱為抗合成酶抗體綜合征(antisynthetase syndrome,ASS),而抗Jo-1抗體陽性的ASS患者又被稱為抗Jo-1抗體綜合征。有研究發現抗JO-1抗體綜合征和包涵體肌炎患者的肌肉組織中H19表達增加,推測該結果可能與肌肉量減少和無力的癥狀有關[33]。此外,H19可以競爭性抑制泛素連接酶TRIM63的活性,增強骨骼肌細胞中肌營養不良蛋白的穩定性,避免其降解,而肌營養不良蛋白減少與肌炎的嚴重程度有關,因此這也可能是H19參與IIM發病機制的途徑之一[34-35]。
2.6 潰瘍性結腸炎(ulcerative colitis,UC) UC患者結腸組織及黏膜中的H19表達水平較健康人顯著增高[28,36]。炎癥因子IL-22通過誘導腸上皮細胞中H19表達,抑制p53蛋白、miR-34a和let-7的釋放,促進了腸上皮增殖和黏膜愈合,使機體在炎癥環境中維持腸上皮穩態[28];然而,H19過表達可能通過多種方式來破壞腸道屏障功能,例如衍生出miR-675下調結腸組織中E-鈣黏蛋白、緊密連接蛋白和VDR表達[36-37]。研究還發現葡聚糖硫酸鈉鹽(dextran sulfate sodium salt,DSS)誘導的結腸炎小鼠結腸組織中H19表達水平顯著升高,以及調控其表達可以抑制小鼠脾臟中Th17細胞的分化[38]。鑒于Th17細胞在維持腸道重要屏障部位穩定中的重要作用,以及H19在上皮細胞更新和腸上皮再生方面的價值[28],H19針對UC潛在的治療效用值得進一步關注。此外,潰瘍性結腸炎相關結直腸癌(ulcerative colitisassociated colorectal cancer,CAC)是UC的一種嚴重并發癥,從活動性UC到CAC的轉化,可能與H19競爭性抑制let-7a,導致原癌基因c-Myc過度表達有關[39]。
3 結論和展望
H19作為一種印記基因已被發現30年了,早期的研究大多著眼于其在妊娠和分娩階段的功能。近年來隨著研究成果的不斷涌現,人們發現H19參與了包括成骨分化、炎癥調節、上皮細胞-間充質轉化、細胞自噬等眾多病理生理過程[9,40-42],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H19在疾病發生發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H19在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病理機制中扮演的角色具有異質性,如在SLE中H19通過干擾Treg細胞增殖和分化破壞了免疫細胞間的平衡,而在AS中則更多展現出其調節炎癥和促進成骨分化的功能[13,17]。即便在同一種疾病的不同部位,H19也發揮著不同的功能:在RA患者的滑膜組織和PBMC中,H19的表達水平完全不同,并在疾病中同時顯現出了促炎和抗炎兩種截然相反的功能[19-20];在同一種疾病的同一部位,H19不同的表達水平也會帶來不同的后果,如在UC中H19可促進腸上皮增殖和黏膜愈合,但其過表達則可能會損害腸道的屏障功能,加重腸道炎癥[28,36]。事實上,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發病是一系列復雜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內分泌和環境因素的影響往往不容忽視。某些自身免疫性疾病有較強的性別傾向,通常與雌激素水平有關,而H19的表達水平同樣受到雌激素的影響[43]。此外,H19也被認為是一種應激誘導表達的lnc-RNA,成年人暴露于環境壓力下時,H19表達增加并積累,而應激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發病的重要誘因[9]。
總之,H19對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影響可能是非常廣泛的,但迄今為止還知之甚少。H19也許可以作為一種新的生物標志物,其表達水平對監測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病情變化有著積極意義,但更重要的是需要進一步了解其參與的分子和細胞機制,加深對自身免疫性疾病發病機制的理解,推動新的治療策略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