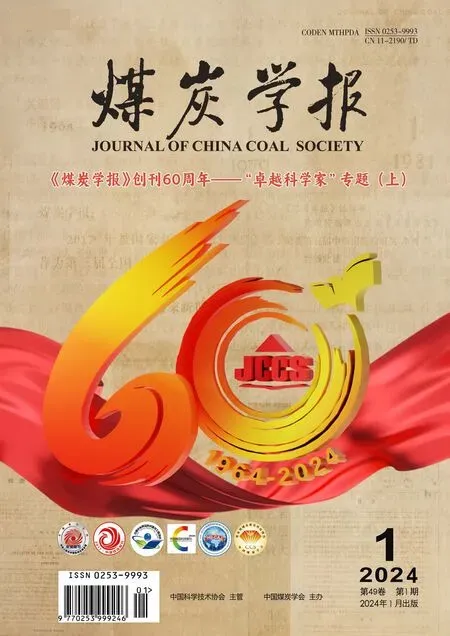煤炭工業數字智能綠色三化協同模式與新質生產力建設路徑
劉 峰 , 郭林峰 , 張建明 , 王 蕾
(1.中國煤炭學會, 北京 100013;2.中國煤炭工業協會, 北京 100013)
能源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和動力源泉。近年來,世界能源格局加速演進,三大體系已呈現出明顯的變化:新冠疫情疊加大國博弈和地緣政治沖突前所未有地沖擊了全球能源供給體系,全球氣候變化倒逼變革能源消費體系,綠色低碳轉型迫在眉睫,與此同時,第四次工業革命與產業變革正在重塑能源技術體系。面對嚴峻的外部形勢和自身發展需求,黨的二十大站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對能源發展作出新部署、提出新要求: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加快規劃建設新型能源體系、確保能源安全、積極參與應對氣候變化全球治理等,為新征程上推動能源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方向。2023 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更是明確指出要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后破”的總原則,進一步為能源行業的健康發展奠定了基調。
基于我國富煤貧油少氣的能源稟賦,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短期內難以根本改變。煤炭工業是支撐我國經濟、社會高速發展和保障國家能源安全的壓艙石與穩定器,承擔著能源保供與支撐新能源穩定發展的時代使命,煤炭工業實現高質量發展既是落實我國能源安全新戰略與產業體系變革的關鍵,也是推進能源產業可持續發展與促進國家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所以,在當前階段任何形式的“去煤化”都是不負責任的錯誤觀點,而如何推進煤炭工業的轉型升級、進一步“做好煤炭這篇文章”則是必須深度思考的重大命題。
煤炭行業多位專家學者針對這一命題開展了系列研究。在能源戰略方面,王顯政[1-2]提出建設創新發展、綠色發展、安全生產等七大體系,推動建設現代化煤炭經濟體系;謝克昌[3-5]提出從能源總量、能源結構、綜合能效、能源科技、體制機制、能源安全6 方面重點分析了未來一段時期內能源發展的關鍵問題,提出了能源革命,碳達峰、碳中和4 個階段的戰略目標;謝和平等[6-7]研判了我國能源消費格局演變趨勢及不同時段煤炭消費規模,闡述了碳中和目標下,我國煤炭行業將迎來實現煤炭高質量發展的機遇、煤炭升級高技術產業的機遇、煤炭搶占新能源主陣地的三大機遇。在煤炭安全綠色開發利用方面,錢鳴高等[8-11]在新世紀初提出煤礦綠色開采技術體系,持續指導我國煤炭綠色開采工程實踐;彭蘇萍等[12-14]研究了礦區生態環境修復關鍵技術,提出了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的工作重點與發展模式;袁亮等[15-17]對我國綠色煤炭資源量進行預測,提出煤炭精準開采的構想,以及關閉/廢棄礦井資源開發利用的科學思考;王雙明等[18-20]探討和展望利用煤炭開采、地下氣化及原位熱解等形成的擾動空間進行CO2地下封存的技術途徑,提出了賦煤區全生命周期能源開發理念,并搭建了賦煤區新能源開發總體框架;武強等[21-23]對我國煤炭主題能源地位和能源戰略形勢開展了思考與對策研究,研發了礦井水害治理關鍵技術體系;岳光溪、劉炯天、劉中民、趙躍民等[24-28]對煤炭清潔洗選和燃燒等技術途徑和技術進行了研究和總結;卞正富等[29]提出煤炭零碳開采理念與技術;陳浮等[30]研究了采煤沉陷區降污固碳協同修復機制;張吉雄等[31]對煤基固廢充填開采技術研究進行了進展總結與展望;潘一山、齊慶新、竇林名、姜福興等[32-36]對沖擊地壓防治方面開展了大量研究,已形成較完整防沖技術體系;周福寶等[37-38]對礦井煤塵和瓦斯防治技術進行了研究和總結。在高效智能開發利用方面,康紅普等[39-41]研究了千米深井巷道圍巖控制難題,提出了煤巷智能快速掘進技術與裝備的發展方向,并針對全球產業鏈與能源供應鏈重構提出了煤礦智能化建設等5 項重點任務;王國法與筆者[42]共同提出煤礦智能化是煤炭工業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技術支撐,并對煤礦無人化智能開采系統理論與技術研發進展進行研究[43-44];葛世榮等[45-48]研究了數字孿生智采工作面、煤礦機器人體系的架構及關鍵技術,初步建立了我國煤礦機器人研發技術體系,并開展了煤基能源動態碳中和模式及其保供降碳效益評估研究;筆者[49-50]系統總結了“十三五”煤炭科技發展成就,分析了煤炭科技發展面臨的共性問題,提出了煤炭科技自立自強、完善現代化煤炭開發利用理論與技術體系的“十四五”煤炭科技發展目標,并以科學定“量”、綠色提“質”、創新領“路”為綱,展開了雙碳目標下推進煤炭消費轉型升級的技術路徑研究。
通過對產業結構、發展模式、管理體制等進行持續變革創新,我國煤炭工業高質量發展已取得階段性成效,現代化煤礦建設取得積極進展,生產開發布局持續優化,生產效率大幅提升,安全形勢明顯好轉,系統智能化建設成效顯著,清潔利用水平逐步提高,現代產業鏈逐漸完善,自主創新能力明顯提升。“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全面開啟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第1 個5 年,也是推進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5 年。在取得成績的同時,全行業也要清醒的認識到,當前煤炭工業的發展水平遠不能滿足中國式現代化的國家需求,煤炭工業的轉型升級仍然任重道遠,發展模式仍需自我革命,科技創新的支撐力度仍然不夠。新時代新征程,亟須形成與中國式現代化相適應的煤炭新質生產力。
筆者分析了當前我國煤炭工業高質量發展取得的階段成效,指出今后發展面臨的挑戰,提出了煤炭工業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三化協同發展的理念與架構,明確了煤炭新質生產力的核心內涵,構建了三化協同發展煤炭新質生產力的總體架構,闡述了通過數字化變革生產要素創新配置、智能化引領關鍵技術跨越突破、綠色化主導傳統產業深度轉型三大要素催生煤炭新質生產力的技術路徑,為煤炭行業高質量發展探索了新的模式。
1 煤炭工業高質量發展現狀與挑戰
1.1 煤炭工業高質量發展取得的階段成效
1.1.1 能源保供成績顯著
面對日趨復雜的國內外政治環境,煤炭安全高效開發和清潔低碳利用有效支撐了我國經濟社會平穩快速發展。2022 年我國原煤產量達到45.6 億t,同比增長10.5%,分別占我國能源生產、消費總量的67.4%、56.2%;原油產量約為2.05 億t,進口原油約5.08 億t,原油對外依存度約為71.3%;天然氣產量約2 201 億m3,進口天然氣1 503 億m3,天然氣對外依存度約為40.6%;發電量約為8.8 萬億kW·h,火電裝機占比約為52%,火電發電量占比約為69.8%,其中煤電占比約為58.4%,如圖1 所示。2023 年1—11 月,全國規模以上原煤產量46.6 億t,同比增長2.9%,2023 全年進口煤炭4.7億t,同比增長61.8%。煤炭資源安全高效開發保障了我國能源的安全穩定供給。

圖1 煤炭生產、消費量與火電占比Fig.1 Proportion of coal production, consumption and thermal power
1.1.2 產業結構不斷優化
煤炭開發布局結構持續優化,煤炭開發效率、效益與安全水平穩步提升。近年來,我國煤炭生產集中度不斷提升,中西部產煤區的重要作用和戰略地位愈發凸顯,截至2023 年底,我國煤礦數量縮減至約4 313座,但產量再創歷史新高。煤炭開發重心加速向晉陜蒙等中西部轉移,2022 年原煤產量超過1 億t 的省(區)有6 個,產量達39.6 億t;晉陜蒙新4 省的產量達到36.9 億t,其中山西、內蒙古原煤產量突破10 億t。煤炭行業生產結構持續優化,企業的產業形態更加多元,上下游產業一體化發展成效顯著,并逐步實現由中低端向中高端邁進。2022 年,規模以上煤炭開采和洗選業利潤總額約為1.02 萬億元,同比增長44.3%;礦山事故起數、死亡人數、煤礦百萬噸死亡率比2012年分別下降75.8%、77.6%和86.0%,煤炭產業經濟與安全形勢持續向好(圖2)。

圖2 煤炭企業經營與安全形勢Fig.2 Management and safety situation of coal enterprises
1.1.3 科技創新能力顯著提高
據不完全統計,大型煤炭企業的科技研發投入強度達到2%,建成國家級研發平臺149 處,初步形成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開放型創新體系;大型礦井智能化建設、特厚煤層智能化綜采綜放、煤與共伴生資源協調共采、燃煤超低排放發電、現代煤化工等技術取得突破,大型煤機裝備國產化、智能化水平穩步提升,煤機裝備制造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建成了世界最大規模的安全高效智能化煤炭開發體系、清潔高效煤電供應體系和現代煤化工技術體系。截至2023 年12 月,全國已有758 處煤礦累計建成智能化采煤工作面1 651 個,其中全國首批示范煤礦累計建成智能化采煤工作面363 個、掘進工作面239 個,涵蓋產能6.2 億t,單個工作面平均生產能力達到500萬t,智能化建設總投資規模超2 000 億元,有力推動了煤炭生產方式加快實現根本性變革,煤炭行業高質量發展邁上新臺階。
1.1.4 綠色開發與清潔高效利用持續推進
近年來,充填開采、保水開采、無煤柱開采、煤與共伴生資源協調開采等綠色開采技術得到大力推廣,我國原煤入洗率由56.0%提升至69.7%,礦井水綜合利用率由62.0%提升至79.3%,土地復墾率由42.0%提升至57.8%,煤矸石及低熱值煤發電裝機由2 950 kW 提高至4 300 kW,實現超低排放的燃煤機組占比達到94%,大型煤炭企業的原煤生產能耗由17.1 kg tce/t 降至9.7 kg tce/t,高效煤粉燃燒技術及煤粉工業鍋爐系統使工業鍋爐熱效率達到90%以上,燃煤工業鍋爐污染物排放達到超低排放標準;攻克了4 000 t/d 水煤漿氣化、3 500 t/d 干粉氣流床氣化成套技術與裝備,建成108 萬t/a 煤直接液化和400 萬t/a間接液化示范工程,煤制烯烴、乙二醇等實現工業化生產,形成了世界上最齊全的現代煤化工技術體系。
1.2 煤炭工業高質量發展仍面臨挑戰
近十年來,我國煤炭工業經受了復雜多變的國內外政治、經濟、技術、裝備等考驗,通過創新發展思路、發展路徑與發展模式,煤炭、煤電、煤化工等產業體系持續轉型升級,為煤炭工業實現高質量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面對數字經濟、新一代信息技術賦能與“雙碳”戰略制約等,煤炭工業實現高質量發展仍然面臨諸多挑戰。
1.2.1 可持續發展受多重因素制約
煤炭仍將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作為我國的主體能源,實現煤炭資源安全、高效、可持續、穩定供給任重而道遠。近年來,隨著開采強度逐年增大,淺部優勢煤炭資源逐漸枯竭,山西面臨后續儲備資源不足等問題,陜西、內蒙古面臨開采深度增大、礦井災害日益嚴重、生態與環境制約等問題,新疆則存在自治區內消費量較低、煤炭資源外運存在瓶頸,山東、河北、河南、兩淮等礦區煤炭資源日益枯竭,面臨持續減產的風險。國際政治環境變化導致國內煤炭供需極易短期內出現過松或過緊的情況,現有煤炭工業體系難以實現煤炭資源智能柔性供給,生產煤礦短期內大幅核增產能,導致采掘接續緊張、災害治理欠賬等,安全高效開采面臨風險。另外,新一代煤炭產業工人對傳統煤礦井下作業環境提出更高要求,傳統煤炭企業面臨招工難的窘境,煤炭產業面臨可持續穩定發展的難題。
促進煤炭行業向生產服務型轉變仍面臨體制機制的制約。我國煤炭消費增速放緩并逐漸進入峰值平臺期,行業發展模式必須由依靠規模擴張、總量增加向提高質量、增加服務轉變。雖然部分企業已經在探索煤礦專業化服務模式,但相關法律法規依然存在障礙,亟待研究推動煤炭行業由生產向生產服務型轉變的法律法規體系和配套體制機制。
1.2.2 數字技術與煤炭開發利用尚未深度融合
數字化本質上是一場新的工業革命和產業變革,是指由數字技術驅動下,實現生產、運營、管理、銷售和服務等全面數字化,從而推動業務模式重構、管理模式變革、商業模式創新與核心能力提升。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是能源工業產業鏈價值鏈走向高端的重要機遇,數字技術是構建煤礦新形態的核心力量,將驅動煤礦生產模式、生產要素、生產者的三重變革:生產模式的變革,意味著從過去的機械化向智能化發展,從過去的人工決策向更高階段的數字驅動決策發展;生產要素的變革,意味著數據將成為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之外的第五大生產要素,深刻影響煤礦運行模式;生產者的變革,意味著煤礦員工工作將遠離環境惡劣的井下,而是置身于綠色的智慧園區。
目前大多數煤礦啟動了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建設了數據中心、云平臺、有線/無線網絡系統等,多數煤礦在以往信息化建設的基礎上實現了經營管理的數字化,但數據資產的利用率較低、利用價值尚未得到有效挖掘,煤炭企業數字化轉型路線仍不清晰,未能實現生產流程的全數字化,未完全打通生產控制系統、經營管理系統、安全管理系統等,缺乏基于數據的決策能力,遠未形成駕馭“數字”的能力。
1.2.3 智能化建設仍處于示范培育階段
煤炭行業屬于傳統的高危行業,井下作業環境惡劣、勞動強度大,且生產過程中伴隨著水害、火災、瓦斯、沖擊地壓、粉塵等災害威脅,智能化建設需求迫切。開采層面,已形成薄與極薄煤層智能綜采、中厚煤層智能綜采、厚煤層智能綜采、特厚煤層智能綜放的智能采煤工作面模式,針對不同地質條件試驗應用TBM掘進機、煤巷快掘系統、掘進機器人系統、智能化縱軸式綜掘設備等,主煤流運輸、供電、供排水、通風系統等可以實現遠程集中控制,露天礦卡無人駕駛編組運行試驗成功。雖然整體智能化建設取得了一些進展,但在智能地質保障、智能防災、智能快掘、智能輔運、智能感知決策等領域存在著明顯技術短板,露天礦無人駕駛技術需要進一步突破。人工智能、大數據、5G、云計算等技術可以有效減少井下作業人員數量、降低工人勞動強度,但受制于井下復雜惡劣的開采環境,新一代信息技術與煤炭開采技術的融合難度大,5G 技術仍然缺乏適宜的應用場景,智能化開采技術裝備對于條件復雜礦井的適應性仍較差,關鍵核心技術裝備還存在諸多瓶頸制約,尚難以實現各系統和應用場景的常態化無人/少人運行;煤炭企業生產、生活環境對高科技人才吸引力弱,礦山從業人員“老齡化”嚴重、知識結構難以適應數字化轉型與智能化建設需要,傳統煤礦組織架構與激勵機制難以支撐企業智能化發展。
1.2.4 綠色化發展不平衡且矛盾突出
黨的二十大指出:必須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當經濟效益與環境生態效益發生沖突的時候,必須堅持生態優先的新發展理念。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要求在合理區間內開發利用和擾動自然資源,煤炭綠色開發和清潔高效利用已成為立足我國資源稟賦、確保能源安全的重要戰略舉措,是建立新型能源體系、實現“雙碳”目標的關鍵支撐。歐洲主要國家在20 世紀90 年代實現了碳達峰,計劃2050 年實現碳中和,而我國碳達峰到碳中和的時間僅30 a,煤炭企業面臨空前的環境政策制約。
大量煤炭開采帶來了煤矸石、礦井水、煤礦瓦斯、地面沉陷、土地占用、地上地下水系損傷、煤塵飛揚等生態環境問題。雖然近年來,無煤柱開采、保水開采、充填開采、礦區生態修復等技術取得積極進展,但綠色開采技術的效率、效益較低,大范圍推廣難度大。多數煤礦仍面臨殘采區遺煤/關閉礦井空間/礦井水/地熱/瓦斯等資源利用率低、采動塌陷面積大、礦工職業健康保障能力不夠等棘手問題。西部生態脆弱區煤礦,亟需采動損傷精準監測感知與控制、礦區生態健康預警與修復等技術。14 個煤炭基地9 個在黃河流域,包括晉北、晉中、晉東,亟需山水林田湖草綜合治理、系統治理、源頭治理。開展煤水資源協調開采、采空沉陷區精細治理、局部精準充填、固廢資源利用等技術攻關。煤炭高效清潔燃燒、清潔轉化、碳捕集與碳封存等關鍵技術的原創性顛覆性突破較少,人才和經費保障不足,政策支持力度較弱,我國煤炭工業尚未建立基于“雙碳”目標的煤炭綠色開發與清潔低碳利用標準體系、技術裝備體系與典型示范工程。
2 煤炭工業三化協同發展理念與架構
2.1 三化協同發展理念
煤炭工業高質量發展要以煤炭資源的安全、綠色、高效、智能開發為基礎,以滿足國家能源安全需求、促進煤炭與其他能源的融合發展、提升煤炭清潔高效可持續利用水平、促進煤炭由高碳能源向綠色能源轉變、提高礦工生活質量與礦區生態文明建設為約束,通過科技、人才、管理、體制機制變革賦能,實現煤炭資源勘察設計、建設開發、洗選運輸、轉化利用等全產業鏈的高質量發展。我國煤炭工業實現高質量發展應以煤炭資源的安全、綠色開發為前提,以數字化、信息化、智能化開采為手段,以煤炭產業全鏈條穩定供給、價值最大化利用為依托,實現煤炭資源的高效開采與清潔低碳利用。基于新一代信息技術與煤炭開發利用技術深度融合應用,實現煤炭資源開發利用全流程的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三化)協同發展,是現階段實現煤炭工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
基于我國煤炭工業高質量發展現狀及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協同發展需求與挑戰,提出我國煤炭工業三化協同的發展理念,如圖3 所示,即通過構建“數字基礎設施、智能管控基礎設施、綠色開發與生態修復基礎設施、清潔低碳利用基礎設施、安全保障基礎設施、產業協同基礎設施”等6 類基礎設施,形成煤炭開發利用上下游全產業鏈、全要素、全生命周期的基礎設施底座,上述相關基礎設施主要指煤炭開發利用相關的數據采集、數據傳輸與深度融合治理、軟硬件平臺及相關裝置裝備,是實現煤炭資源開發利用全流程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協同發展的基礎。

圖3 煤炭工業三化協同發展理念框架Fig.3 Framework of concept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izations of the coal industry
基于上述基礎設施,重點研發形成6 類技術體系。通過研發全產業鏈數據高效采集與深度治理技術體系,打通煤炭產—運—儲—銷—用全流程的數據壁壘,通過數據治理技術深度挖掘不同場景數據的融合應用價值,以數字產業化賦能煤炭產業數字化;通過研發構建煤炭行業知識圖譜與智能決策管控技術體系,深度挖掘煤炭產業上下游各業務場景的關聯關系與價值,為煤炭生產利用全流程的自主決策與智能控制奠定基礎,實現煤炭產業數字化賦能煤炭產業生產利用決策控制的智能化;通過研發煤炭產業安全協同保障技術體系,實現煤炭生產安全、生態安全、數據安全、網絡安全、平臺安全,保障國家能源安全、穩定、可持續供給。將上述數字化、智能化融合發展成果應用于煤炭開發、生態修復、低碳清潔利用相關應用場景,研發形成煤炭資源智能-綠色-高效開發技術體系、礦區生態智能監測-預警-修復技術體系、煤炭柔性開發與清潔低碳利用技術體系,實現煤炭開發利用全產業鏈、全流程的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協同發展。
上述技術體系的研發應用,需要科技、產業、標準、管理、人才、運營等6 類創新引擎進行支撐,共同構建煤炭工業“產業數字化、系統智能化、全程綠色化”三大生態體系,最終實現以“減人、增安、提質、創效、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為特征的煤炭工業三化協同高質量發展目標。
煤炭工業三化協同是以數字產業化賦能煤炭產業數字化為基礎,以煤炭產業數字化與系統智能化為支撐,實現煤炭產—運—銷—儲—用全流程的智能系統化運行,將煤炭產業數字化、智能系統化應用于煤炭資源開發利用的各主要環節,實現煤炭工業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三化協同發展,助力煤炭工業高質量發展。
2.2 三化協同發展架構
上述煤炭工業三化協同發展理念的詮釋,三化協同指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等新一代技術與煤炭開發利用技術的融合創新應用,賦能煤炭工業上下游全產業鏈的協同發展,實現煤炭工業探-建-采-選-儲-運-銷-用-監管等于一體的協同發展,為此構建了煤炭工業三化協同發展總體架構,如圖4 所示。
總體架構的最底層涵蓋煤炭工業全產業鏈的主要參與方,包括地質勘探、礦井建設、煤礦企業與選煤廠、煤化工企業、燃煤電廠等,是信息生產與采集的基礎層,也是上部行業智能綜合管控平臺與監管平臺智能決策指令的執行層,構成了煤炭工業三化融合的基礎設施底座;通過煤炭工業融合網絡將底層各類信息上傳至煤炭行業數據中心,大部分數據通過高速、高可靠有線網絡傳輸,部分涉密數據可以采用專網傳輸;部分應用場景也可以選擇公-專融合的5G 無線網絡傳輸,借助5G 公網的網絡切片技術,可以降低傳輸成本,通過5G 專網可以提高數據傳輸的時效性、可靠性與安全性。
采集的各類數據分別匯入煤炭行業數據中心,根據應用場景差異,分別設立煤炭行業勘查數據中心、開采與洗選數據中心、生態環境數據中心、煤化工數據中心、燃煤電廠數據中心等,并根據不同的應用場景設置裝備、物料等數據中心,以及融合應用數據中心,采用“云-邊-端”協同的多層級處理方式對數據進行分析,實現根據業務場景的數據深度挖掘分析及多場景數據的融合應用。將“云-邊-端”協同的數據處理中心可以劃分為4 層,底層為數據采集層(端側),將采集的數據匯聚至邊緣云或企業云;邊緣云則主要在系統側,支撐業務系統的數據處理;第3 層為企業云或集團云,用于對本企業或集團相關數據的融合處理;第4 層為行業云,用于對全行業數據進行分析、融合及應用,形成煤炭工業三化融合的數據支撐底座。部分應用場景(如洗選、運輸、銷售等)可以采用區塊鏈技術,提高數據的可靠性、交易的透明度等。
通過技術平臺、數據平臺、模型庫與算法庫等行業基礎平臺賦能,將新一代信息技術與煤炭資源勘探、設計、建設、開發、生態修復、洗選、運輸、銷售、清潔利用等技術進行深度融合,實現數字產業化對煤炭產業數字化賦能,支撐構建不同業務場景的智能綜合管控平臺,其中生產企業端主要實現基于數據深度挖掘與融合分析對各業務系統的綜合管理與集成控制,重點實現對底層各場景基礎設施的智能控制,突出生產單元體或業務場景的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協同發展;而上部集團層則重點實現對所轄企業各類場景的監管或管控,突出集團所轄各類應用場景的三化協同發展,重點為各類應用場景的協同;再上層則為行業監管層,重點對煤炭行業上下游全產業鏈的監管,突出三化技術賦能煤炭行業探-建-產-洗-運-銷-用等全鏈條的協同發展,以及與長下游輔助行業的協同發展。上述煤炭工業三化協同發展架構的實現不僅需要多專業科技協同創新支撐,還需要管理體制變革、國家與行業政策激勵、人才隊伍建設等保障措施支持。
2.3 煤炭新質生產力的內涵
2023 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特別是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新質生產力。”生產力是人類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新質生產力是以科技創新為內生動力、包含全新質態要素的生產力。生產力變革離不開產業作為載體和表現形式,所以實現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是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必由之路。煤炭開發利用的全生命周期,是廣大礦工改造自然環境、同各類災害不懈斗爭的過程,也是自然反作用人類攫取利用資源而互相對抗的過程,加快形成煤炭新質生產力是推動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重要途徑。
煤炭新質生產力,是在煤炭安全區間內科學定“量”的前提下[50],以綠色提“質”、創新領“路”為綱,通過數字化變革生產要素創新配置、智能化引領關鍵技術跨越突破、綠色化主導傳統產業深度轉型三大要素協同融合,進而推動煤炭開發利用水平大幅躍遷的先進生產力。發展煤炭新質生產力是煤炭工業進入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以創新推動變為全面創新驅動的自我革命式的新發展模式。
縱觀百年以來的煤炭開發利用史,每一次開發利用的技術革命都會帶來生產力的重大躍升。新時代新征程,亟須形成與中國式現代化相適應的煤炭新質生產力,提升適應環境、改造災害、利用資源的能力。立足煤炭行業高質量發展階段性成果,以數字化設施為基礎,以智能化技術為突破,以綠色化轉型為方向,發揮科技創新的增量器作用,煤炭新質生產力將依托煤炭智能綠色安全高效開采、清潔低碳協同轉化利用兩大基礎理論的進步,以及5G、AI、礦山大模型、高可靠傳感器和終端裝備、核心元器件、煤化工新型催化劑、負碳固碳等技術的革命性突破,對煤炭工業的勞動者、勞動工具、勞動對象等進行系統性重塑和整體性重構,大幅度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深刻改變煤炭工業生產形態:基層勞動者將由體能型、技能型向科技型、復合型轉變;勞動對象將由器械、設備、原料等物質實體拓展至包括大數據、工業互聯網等在內虛擬對象;生產資料將進一步從物質資源等實體資本向科技資本、人才資本側重;生產要素除勞動力、資本、土地等傳統要素外,拓展出數據這一全新關鍵生產要素;勞動產出將由煤炭、化工品等實物產品類向智能技術應用場景、礦山大模型算法、提質降碳模式等技術服務類拓展轉變。
3 三化協同培育煤炭新質生產力的技術路徑
3.1 數字化變革生產要素創新配置
基于煤炭工業三化協同發展總體架構,采用工業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一代ICT 技術,建設覆蓋現場、煤礦、企業、行業4 層架構的煤炭全產業鏈云網融合數字基礎設施,推動煤炭行業全要素、全過程、全生命周期數字化,建設煤炭工業大數據中心,構建“數據驅動”的煤炭數字產業新生態,激發數據作為新的生產要素創新活力,驅動煤炭工業生產方式變革,建立全產業鏈數據高效采集與深度治理技術體系和知識圖譜與智能決策管控技術體系,深度融合賦能煤炭資源開發與清潔利用全產業鏈數字化轉型。
3.1.1 全產業鏈數據高效采集與深度治理技術體系
以煤炭行業工業互聯網體系架構為框架,構建煤炭工業全產業鏈數據高效采集與深度治理技術體系,如圖5 所示,從下至上,主要包括:
(1)全面開展煤炭全產業鏈數字化、煤礦智能化建設,以煤礦、企業為單元建設數字化、智能化基礎設施,構建集團級、邊緣側二級云邊協同私有云數據平臺,具備煤炭全產業鏈全要素監測、識別、采集能力,實現煤炭資源及環境動態高精度數字地質模型、礦井采掘工程設計及裝備數字化、煤炭開采工藝和生產系統數字化、煤炭洗選儲運全流程數字化、煤炭消費利用全過程數字化,實現數據橫向跨生產系統、縱向跨業務管理層級自由流動。
(2)構建開放共享的煤炭行業可信公有云工業互聯網平臺,建立數據安全高效采集機制,匯聚全產業鏈數據資源,融合礦山AI 大模型、BIM+GIS 時空信息模型等技術平臺能力,開展數據開發、建模、訓練,形成面向全行業數據深度治理及智能應用服務能力;依托國家工業互聯網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構建煤炭行業工業互聯網標識解析二級節點、企業節點和公共遞歸節點3 個層級的鏈網基礎設施,形成跨產業鏈上下游、跨組織壁壘的數據互聯互通路徑,在統一行業數據標準下,實現對全產業鏈業務場景的解析服務。
(3)統一煤炭全產業鏈數據標準體系,統一煤炭行業數字產業結構和數據字典,破除行業數據孤島,采用分布式網絡、隱私計算加密、智能合約等區塊鏈技術,構建煤炭行業數據透明、不易篡改、可追溯的數字可信空間,形成煤炭全產業鏈各要素原生數字身份與大規模可信協作網絡。利用數據資產管理、數據目錄、供需撮合等數據流通功能,實現數據資產的統一登記和管理;利用數據訪問控制、使用控制和延伸控制等功能,實現數據主體、數據本身的使用時間、地點、方式等管控;利用可信環境、日志存證和自動審計功能,實現使用環境和行為安全可控。
(4)基于煤炭行業工業互聯網平臺、標識解析鏈網基礎設施和大規模數字可信協作網絡,構建形成煤炭工業全產業鏈數據高效采集與深度治理技術體系和數字基礎設施,為全產業鏈監測數據、分析模型、決策依據等提供承載空間,為實現“數據驅動”的產業控制決策模型提供數字化支撐手段。
3.1.2 知識圖譜與智能決策管控技術體系
基于煤炭工業全產業鏈數字基礎設施重塑煤炭生產要素配置,構建基于知識圖譜支撐的煤炭工業智能決策管控技術體系,如圖6 所示,煤炭工業數字基礎設施承載煤炭行業全產業鏈圖數據資源、煤炭工業知識文檔數據資源、煤炭工業地質與采掘部署時空數據資源和煤炭工業監管準入規則數據資源等;建立煤炭工業全產業鏈知識圖譜引擎,融合知識圖譜任務引擎、大模型任務引擎、規則算子流程引擎,構建煤炭工業全產業鏈多模態超融合知識引擎;支撐構建煤炭工業知識圖譜、煤炭工業文檔知識庫、煤炭工業規則知識業務庫,形成煤炭工業全產業鏈知識體系跨形態建模支撐體系;打造煤炭工業全產業鏈知識賦能與決策支撐能力,包括煤炭行業知識檢索、知識推薦、關系推理、圖譜相似度計算、文檔生成、多模態驅動規則流程定義等;聚焦煤炭工業全產業鏈智能柔性供給、安全高效柔性生產、設備全生命周期預測性維護、安全態勢分析預測和安全生產培訓及運維服務等應用場景,提供業務決策、規則計算、知識支撐能力,支撐煤炭工業全產業鏈探-建-產-選-運-銷-用一體化產業監管與控制平臺的智能決策水平。

圖6 煤炭工業全產業鏈知識圖譜與智能決策技術體系Fig.6 Technological system of knowledge map and intelligent decision of the whole industrial chain of the coal industry
3.2 智能化引領關鍵技術跨越突破
依托煤炭工業數字化創新要素配置體系,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與煤炭資源開發清潔利用深度融合,促進煤炭科技創新、煤炭數字技術和煤炭數字產業全面升級,構建煤炭全產業鏈智能-綠色-高效開發技術與供給體系,打造形成煤炭工業新質生產力,推動煤炭全產業鏈全要素實現泛在互聯、深度融合,煤炭傳統產業與數字產業實現以新促質、數實融合,煤炭數字技術與數字產業實現自主可控、自立自強,3 方面融合共生、協同演進。
3.2.1 煤炭資源智能-綠色-高效開發技術體系
煤炭工業新質生產力促進煤炭新型工業化進程,以國家“3060”雙碳戰略目標為要求,建立煤炭資源開發、智能生產、柔性供給、低碳減排、綠色生態發展路徑,形成煤炭資源智能-綠色-高效開發技術體系,基于煤炭工業數字要素配置體系與知識圖譜智能決策管控技術體系,部署面向全產業鏈現場級、企業級和產業智能技術與應用集群,推動煤炭全產業鏈地質資源、開采裝備、應用系統等全要素上云、用數、賦智,全面提升煤炭資源開發技術體系應用水平,如圖7 所示。

圖7 煤炭工業智能-綠色-高效開發技術體系Fig.7 Technological system of intelligent-green-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the coal industry
煤炭工業智能-綠色-高效開發技術體系包括縱向國家級、產業級、企業級和工業現場級4 層,橫向產業鏈從資源勘探、礦井設計與裝備選型制造、煤炭開采、煤炭運銷、煤炭利用等5 個階段,形成橫縱交織的數字管控產業鏈網,主要包括:
(1)工業現場級。實現系統及設備的智能化升級改造,包括煤礦現場或井下、智能制造工廠、運銷路網基礎設施、發電廠及化工廠等,通過煤炭數字產業基礎設施建設,打通物物流通及數字互聯互通路徑,包括煤礦智能化建設構建的信息基礎設施、透明地質數字孿生保障、智能開采自主精準截割。裝備及系統智能化升級、智能化綜合管控平臺及各類應用APP;煤機智能制造工廠MES 系統、數控產線、故障檢測等,實現廠礦端到端網絡化協同;煤礦智能化生產與煤炭運銷基礎設施形成煤炭資源流動網,實現火力發電廠、煤化工廠按需供貨。
(2)企業級。實現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包括煤炭設計企業、煤機制造企業、煤炭企業、煤炭運銷企業、煤炭消費企業等,打通企業間的管理流程,形成跨組織間的協同協作模式。煤炭設計企業需提升數字化設計及交付、孿生仿真、設計工具等能力,實現設計、交付、運營一體化服務;煤機裝備企業需提升云協同設計能力、制造產線智能化水平、設備維修響應速度,實現設備及系統運維網絡化協同;煤炭企業需提升業財一體化及營銷一體化水平,提升人員零傷害、環境零擾動的安全管控和精準開采能力,實現煤炭資源按需開采;煤炭運銷企業需提升對煤炭需求、價格、煤質、儲量及車輛路網等數據的實時獲取、預測分析能力,實現煤炭最優配置供給;煤炭消費企業需提升煤炭燃燒利用的低碳減排量化控制水平,實現“3060”雙碳目標下的最優減排路徑,滿足企業ESG 評價信息披露要求。
(3)產業級。實現煤炭全產業鏈上下游數字化轉型和高質量發展,行業安標準入、安全監管監察、煤炭經營監管、低碳減排監管等實現服務化轉型,在統一產業標準體系、數據標準體系和監管管控流程規范下,產業鏈上下游形成可信認證的數字流通空間,形成物物按需流通、數據安全可信、數實融合共享的煤炭數字產業發展態勢,實現煤炭消費按需調控、煤炭運銷柔性供給、煤炭開采以銷定產、煤炭裝備精準維護和服務體系全面升級。
3.2.2 煤炭產業安全協同保障技術體系
煤炭作為我國主體能源,保障了我國能源安全可靠,在新能源產業體系中發揮了穩定器、壓艙石作用,一方面是煤炭資源開發過程的安全可控,包括地質安全、生產安全、設備安全、環境安全、管理安全和經營安全等;另一方面是供給消費端安全保障,包括煤炭質量與煤質安全、煤炭供給安全、煤炭清潔利用安全和低碳減排安全等,形成煤炭工業全產業鏈安全協同保障技術體系。構建國家級、煤炭企業集團級、煤礦、工業現場等4 級架構,支撐煤炭行業探-建-產-選-運-銷-用一體化產業監管與控制平臺,實現煤炭產業鏈可管可控。
構建煤礦全地層高精度構造地質模型、巷道模型、采空區模型、地質屬性模型等,構建地質預測預報信息化模型,對采掘范圍內的主要災害進行預測預報,采掘位置與致災體空間三維距離關系,構建采掘空間三維立體預報體系,與礦井通訊系統聯動,實時傳輸信息。前沿數字化技術與基礎研究的結合,煤礦災害防治正向著定量化精準化的階段發展,利用數值仿真技術與大尺寸物理模擬實驗的結合厘清災害發生的機理,自主感知的監測設備和機器學習算法的融合應用將豐富工程尺度下數據質量的提升,全空間長時監測裝備助力實現全維度信息的透明化,為災害防治決策提供全面、可靠的基礎數據支撐,深度學習、大模型等前沿算法,將打通覆蓋煤炭開發利用全生命周期的系統工程。
建立從煤礦、礦區、煤炭行業等3 個維度安全體系,其中煤礦生產安全從煤礦綜采、掘進、主運輸、輔助運輸、生產輔助、供配電、智能洗選、供配電等固定場景數據融合、協同管控與遠程控制,實現無人少人則安。礦區級產業協同與礦井協同主要以“產-運-銷”業務鏈為核心,以礦區級銷售訂單與產業需求,對各礦井生產與銷售計劃動態編排、跟蹤與指標管控,從生產監督管理視角進行;行業級柔性生產監測體系,重點圍繞區域性能源需求,進行能源生產調度管理,綜合提升能源安全和產業安全協同保障水平。
3.3 綠色化主導傳統產業深度轉型
當前,能源綠色低碳轉型引發了新一輪技術創新高潮,促使我國能源發展進入了“化石能源清潔化、清潔能源規模化、多種能源綜合化”格局。煤炭工業綠色低碳發展應以煤炭資源安全、高效、高采出率開發為基礎,以智能開發技術與裝備為基本保障,以生態環境保護為約束,運用先進的科學技術與現代管理理念,構建和諧有序、協調一致、智能高效、綠色可持續的煤炭資源開發新格局,助力煤炭工業實現高質量發展。
3.3.1 礦區生態智能監測-預警-修復技術體系
圍繞煤炭資源低損害智能開發前沿科學問題,系統研究煤炭開采“三場”時空演化規律、覆巖斷裂及地表生態損害機理、透明地質與智能化開采基礎理論、地表生態自修復機理、礦井水凈化與離子交換機理、粉塵擴散與防控機理等,為煤炭資源安全智能綠色開發奠定理論基礎。重點研發煤炭開采對地表生態環境損害機理及智能監測、預測、預警技術體系,突破低損害開采圍巖控制理論難題;研發煤礦高精度地質探測技術與裝備、復雜環境自動化掃描重構與全時空透明地質建模等技術,構建礦井地質透明、應力場透明、滲流場透明等透明地質技術體系;研發厚及特厚煤層安全高效智能開采技術與裝備,突破多系統融合與智能協同管控技術瓶頸;研發構建礦井災害智能監測預警與綜合防治技術體系,開發低損害智能留巷與減量化智能充填技術裝備,以及礦井水資源循環利用技術體系,形成煤礦采-選-充-復智能一體化開發模式;研發采空區碳封存、負碳開采等技術,實現開采過程的降碳、固碳;研究深部煤炭資源原位流態化開采技術體系,實現“地上無煤、井下無人”的深部煤炭資源流態化、智能化、無人化開采;研發露天礦源頭減損與智能高效采-排-復一體化技術裝備,提高露天礦智能高效開采綠色開采水平。
研究高強度開采沉陷區生態自修復機理,以及煤炭開采擾動區人工干預及自修復誘導促進技術與裝備,有效減緩煤炭開發對地表生態破壞。研發礦區土地損傷修復智能監測技術與裝備,開發基于多元物聯網感知技術的礦區生態環境監測與治理系統,構建形成煤礦地質環境治理應用與生態重建技術體系。研發露天礦環境地質災害智能協同監測預警與風險評估技術和裝備,構建礦山地質災害綜合防控、生態環境修復等綜合技術體系。研發煤基固廢智能高效利用與采注協同智能開采技術,變廢為寶,降低煤基固廢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研發井上下空氣污染物“分源-分區-分級-分策”智能精準監測與高效協同防控方法,構建“人-機-環-管”四位一體的煤礦職業健康保障體系。
3.3.2 煤炭柔性開發與清潔低碳利用技術體系
目前,我國處于新舊能源交替轉換的關鍵時期,煤炭作為我國能源安全穩定供給的壓艙石與穩定器,煤炭需求與供給的劇烈波動對我國能源安全帶來深遠影響。發展以煤礦智能化技術支撐煤炭資源柔性開發的能源供給體系,有效消除因氣候、突發政治事件等帶來的能源波動沖擊影響,以煤為基保障能源供需的動態平衡,提高能源供給的穩定性、可靠性與經濟性。
針對煤炭清潔低碳利用技術難題,應研發高精度在線測灰儀、旋流場重介質精準分選、界面調控增強選擇性浮選、煤炭智能干選、煤泥水高效固液分離等關鍵技術與裝備,突破工藝參數和產品質量高精度在線檢測及預測技術,開發選煤設備智能診斷、管控與決策系統,攻克一批基于精細化和智能化的煤炭分選加工共性關鍵技術,突破自適應原煤品質全流程智能控制、數字孿生運維等技術,構建煤炭生產、智能配煤、產品結構與成本利潤模型,實現煤炭洗選管理流程化、洗選過程智能化、洗選運銷柔性化。
著力突破靈活智能燃煤發電、高效清潔燃煤發電、新型動力循環燃煤發電等新技術,開發高低旁熱電解耦高效適應性熱調峰技術與深度電調峰技術,實現燃煤電廠熱電靈活調節;研發大型燃煤電站自主化靈活高效智能控制系統,開發燃煤發電過程泛在狀態感知體系、工業實時數據中臺、工業智能計算引擎等,提高大型燃煤電站的智能化水平;研究燃煤污染物高效低成本深度控制與資源化回收技術、煤電機組混氨燃燒技術、汽輪發電機組性能優化與智能運行監控技術,實現燃煤發電的降本、降碳、提效。研究燃煤機組綜合能源轉型技術,開發“火電+”源網荷儲一體化技術,構建風光火儲一體化大型多能互補智能綜合管控平臺,提高能源利用率及促進可再生能源消納。
對煤炭直接液化、間接液化、煤制烯烴產業鏈技術進行迭代升級,重點突破費托合成油中的α-烯烴分離提純技術、煤基特種燃料、高端聚烯烴、高端潤滑油、高端碳素材料加工轉化技術,實現煤化工產業鏈的延鏈、補鏈和強鏈。研發氣固熱載體雙循環粉煤快速熱解技術、高瀝青質含量中低溫煤焦油全餾分加氫技術、煤焦油全餾分加氫產物制環烷基油品技術,開辟低階煤清潔高效轉化利用新路徑。研究煤炭轉化過程中污染物控制及煤基固廢資源化利用技術,探索現代煤化工與“光伏+制氫+儲熱+儲能”一體化互補資源開發。
4 愿 景
以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三化協同培育發展煤炭新質生產力,將為煤炭工業整體形象的提升帶來根本性變革,徹底顛覆傳統落后的生產面貌,未來煤炭將是呈現以下6 個新特征的“煤”:
(1)本質安全煤。煤炭新質生產力將保障煤炭工業的發展安全。一方面通過數字技術賦能、智能技術變革,實現煤炭生產各類災害的精準定量防控,發展消災無害化開發利用模式;另一方面,將更好統籌發展與安全的關系,確保能源安全、產業鏈安全。
(2)開發高效煤。煤炭新質生產力將推動煤炭工業生產效率變革。提升從勘探—設計—建設—開發—洗選—運輸—轉化利用全產業鏈的效率和效益,釋放先進生產力的科技效能。
(3)低碳綠色煤。煤炭新質生產力將推動煤炭工業生產質量變革。環境友好型開發利用模式助力創建零碳減損礦區,同時實現開采利用的全流程的碳排放跟蹤監測。
(4)創新驅動煤。煤炭新質生產力將推動煤炭工業發展動力變革。由勞動密集型轉變為技術密集型,搶占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競爭制高點,不斷推動煤炭工業向價值鏈中高端發展,拓展高技術輸出服務。
(5)礦工幸福煤。煤炭新質生產力將提升煤炭從業者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職業健康水平大幅改善,素質優良、規模充裕、結構優化、分布合理的新型勞動者隊伍將成為新質生產力最重要的基礎性核心支撐。
(6)和諧文化煤。煤炭新質生產力將變革各生產單元傳統的生產關系。通過管理創新、機制創新、文化創新,形成與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生產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