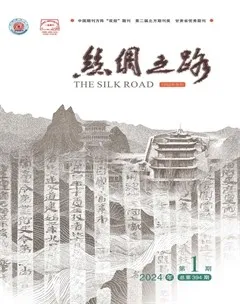吉爾吉斯語跨境變異及表現(xiàn)形式探析
才甫丁·依沙克



[摘要] 吉爾吉斯語的跨境類型與特征多種多樣,其在語音、詞匯、語法、語義和文字等方面產(chǎn)生了不同程度的變異。從地理角度進(jìn)行的研究表明,跨境語言變異類似于地域方言,由山脈和河流等自然空間阻隔導(dǎo)致不同地區(qū)的語言逐漸產(chǎn)生差異。國界劃分、政治、經(jīng)濟(jì)和文化制度等社會(huì)空間因素影響著吉爾吉斯語的變異,社會(huì)因素對(duì)吉爾吉斯語的跨境變異也具有重要意義。此外,吉爾吉斯(柯爾克孜)族群的遷徙和與其所居住國家的主體民族以及周邊民族的交往,對(duì)跨境吉爾吉斯語的變異產(chǎn)生影響。這幾個(gè)方面的因素相互交織,并共同作用,呈現(xiàn)出一定的跨境變異特征。
[關(guān)鍵詞] 吉爾吉斯語;跨境變異;地理因素;社會(huì)因素;語言結(jié)構(gòu)
[中圖分類號(hào)] G115? ?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 A? ? [文章編號(hào)]1005-3115(2024)01-0117-09
語言的跨境現(xiàn)象(Languages Across Borders)是世界上一種普遍存在的語言現(xiàn)象,跨境語言是指分布于不同國家境內(nèi)的同一種語言或方言。吉爾吉斯語是吉爾吉斯斯坦的國家語言,被吉爾吉斯斯坦的主體民族吉爾吉斯族和一些少數(shù)民族所使用,在10多個(gè)國家廣泛分布,其中包括吉爾吉斯斯坦、中國、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俄羅斯、塔吉克斯坦、土耳其、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全球范圍內(nèi)大約有700萬人使用吉爾吉斯語。吉爾吉斯斯坦國內(nèi)有超過600萬人口,其中大部分是吉爾吉斯族人,有四五百萬人使用吉爾吉斯語(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22 Revision. Medium-fertility variant)。根據(jù)《中國統(tǒng)計(jì)年鑒·2021》,中國境內(nèi)的柯爾克孜族人口數(shù)為204402人,其中大部分人居住在我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的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特克斯、庫克鐵列克、夏特)和黑龍江省富裕縣的部分地區(qū)。
一、吉爾吉斯語跨境變異的形成及它們相互之間的關(guān)系
吉爾吉斯族是中亞歷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其相關(guān)記錄最早出現(xiàn)在我國古文獻(xiàn)里,不同朝代古文獻(xiàn)里記載的稱呼發(fā)音上略微不同,一般認(rèn)為,文獻(xiàn)所見堅(jiān)昆、結(jié)骨為 Q■rq■z 族稱的對(duì)音譯寫,如堅(jiān)昆這個(gè)詞最早出現(xiàn)在《漢書》里。“堅(jiān)昆”一詞始見于《漢書》,唐中后期猶見于載籍;“結(jié)骨”之名隋朝即有,至唐高宗時(shí)期仍延用。Q■rq■z 一名在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時(shí)期又作鬲昆、隔昆、契骨、居勿、紇骨(子)、紇扢斯、黠戛斯、戛戛斯等[1]。遼朝時(shí)期被稱為黠戛斯或轄戛斯,元朝時(shí)期被稱為乞兒吉思或吉利吉思,以后的清朝時(shí)期被稱為布魯特。“布魯特”一詞來自于蒙古人對(duì)吉爾吉斯人的稱呼Burut(布魯特) 一詞。雖然以上不同稱呼發(fā)音上有所不同,然而都指吉爾吉斯(Q■rq■z )這個(gè)族在不同時(shí)期的不同稱呼。840-1207年存在的強(qiáng)大的黠戛斯汗國在被蒙古帝國吞并后,先后受到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的統(tǒng)治,分別接受西伯利亞汗國、浩罕汗國、準(zhǔn)噶爾汗國、葉爾羌汗國和我國清朝的統(tǒng)治。
19世紀(jì)末,全球格局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其中之一是中亞地緣政治的重組。隨著沙俄帝國向中亞擴(kuò)張,吉爾吉斯人的一部分部落受到俄羅斯人的統(tǒng)治,而另一部分吉爾吉斯部落仍處于我國清朝的統(tǒng)治之下。在新中國成立之后,柯爾克孜族如其他少數(shù)民族一樣,在語言和文字發(fā)展方面實(shí)現(xiàn)了顯著的進(jìn)步。他們的母語吉爾吉斯語,受到了廣泛的保護(hù)和發(fā)展。得益于國家的語言政策,柯爾克孜族的語言教育得到了重視,相關(guān)機(jī)構(gòu)積極地組織語言課程和文化活動(dòng),以便傳承并推廣柯爾克孜族的語言文化。他們已經(jīng)擁有自己的文字系統(tǒng),各種類型的期刊及電視臺(tái)節(jié)目,出版各類書籍,包括教育、文學(xué)、歷史文化等領(lǐng)域的豐富書籍。到此,已經(jīng)形成了被中國柯爾克孜人廣泛采納的標(biāo)準(zhǔn)吉爾吉斯語,這種語言有一套完整的語法規(guī)則。
1970-1980年,蘇聯(lián)境內(nèi)帕米爾地區(qū)的一部分吉爾吉斯人遷徙到阿富汗的帕米爾地區(qū)并定居,隨后,在首領(lǐng)熱合曼庫魯?shù)念I(lǐng)導(dǎo)下,約有2000人遷徙到巴基斯坦境內(nèi)。然而,由于無法適應(yīng)巴基斯坦的炎熱氣候以及各種傳染病的原因,他們被迫再次遷徙到土耳其,并在土耳其的萬地區(qū)定居,尋求新的生活。這形成了土耳其境內(nèi)的一個(gè)吉爾吉斯族群體。
蘇聯(lián)解體后,中亞各國的國界逐漸得以明確,原先屬于蘇聯(lián)的吉爾吉斯族人口因此在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哈薩克斯坦境內(nèi)逐漸形成了吉爾吉斯人群體。這一歷史變遷導(dǎo)致吉爾吉斯語的跨境變異現(xiàn)象日益顯著。1991年,吉爾吉斯斯坦宣告獨(dú)立,并通過國家法律將吉爾吉斯語確立為官方語言,從而為其提供了法律保障。此舉不僅確立了吉爾吉斯語的地位,更為其未來的發(fā)展開辟了新的道路。隨后,受多種因素影響,尤其是被就業(yè)機(jī)會(huì)所吸引,許多吉爾吉斯人選擇前往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等國。這一人口遷移行為不僅增加了跨境人口數(shù)量,同時(shí)也對(duì)語言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
我國黑龍江境內(nèi)的柯爾克孜人的來源有所不同,他們是吉爾吉斯人的特殊群體,因?yàn)樗麄儾⒎莵碜灾衼喌貐^(qū),而是在早期時(shí)期從吉爾吉斯人的故鄉(xiāng)——葉尼塞河流域遷徙過來的。根據(jù)相關(guān)研究,他們的語言特征更接近古代吉爾吉斯語,他們是元朝時(shí)期幾次遷徙過去的。至今,這個(gè)群體中的吉爾吉斯人不會(huì)說吉爾吉斯語,他們已經(jīng)發(fā)生了語言轉(zhuǎn)變,使用漢語。
結(jié)果,原本使用同一語言、共享相同文化的清朝管轄的吉爾吉斯人逐漸演變?yōu)榭缭郊獱柤顾固埂⒅袊⒐_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等國家的跨境民族,其語言也變成了跨境語言。他們受到其他國家境內(nèi)主體民族或其他民族語言的影響,開啟了新的發(fā)展方向。吉爾吉斯語形成跨境語言的原因多種多樣,既包括地理上的障礙,也包括族群遷徙和國界的確立,而這些跨境化的過程發(fā)生的時(shí)間也有所不同。
二、吉爾吉斯語的跨境類型與特征
跨境語言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跨境語言是地理分布于不同國家境內(nèi)互相接壤和非接壤的同一種語言。例如英國的英語和美國的英語,我國的漢語和新加坡華人語言,中國、美國、加拿大的苗語。狹義跨境語言則是地理分布于不同國家境內(nèi)且相接壤的同一種語言。例如朝鮮語主要分布在朝鮮、韓國和我國吉林延邊朝鮮族自治州[2],這些地方在地理上是相互接壤的。根據(jù)這一理論,吉爾吉斯語屬于廣義的跨境語言。因?yàn)殡m然分布于中亞地區(qū)和我國新疆的吉爾吉斯族相互接壤以外,其一些群體地理分布方面處于不接壤的國家。例如土耳其的吉爾吉斯語和中亞及我國的柯爾克孜(吉爾吉斯)語在地理上不接壤,吉爾吉斯斯坦的吉爾吉斯語和俄羅斯的吉爾吉斯語不直接接壤,同樣我國東北的柯爾克孜(吉爾吉斯)語和其他地方的吉爾吉斯語也完全不接壤。
跨境語言在地理分布、使用情況、跨境時(shí)間和語言差異等方面具有多樣性。吉爾吉斯語的跨境特征可以說是非常復(fù)雜的。第一,吉爾吉斯語分布于世界許多國家,除了中亞幾個(gè)國家之外,還分布于中國、俄羅斯、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國家。第二,吉爾吉斯語在境內(nèi)外的使用人口數(shù)量不同。吉爾吉斯斯坦是吉爾吉斯語的主要使用國,人口數(shù)量遠(yuǎn)遠(yuǎn)超過其他國家;第二名是俄羅斯境內(nèi)的吉爾吉斯人口最多;第三名是我國境內(nèi)的柯爾克孜族,有20多萬人。然后按照數(shù)量多少順序應(yīng)該是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薩克斯坦、阿富汗和土耳其。第三,各國對(duì)該族群的名稱并不一致。在我國境內(nèi)稱之為柯爾克孜,而境外則稱之為吉爾吉斯,在中亞國家則稱為“Кыргыз”,在阿富汗和塔吉克語中稱之為“Киргиз”,而在土耳其則稱之為“■”。不同國家的主體民族根據(jù)其語言特征來稱呼吉爾吉斯人。第四,吉爾吉斯人的地理分布非常復(fù)雜,既有相鄰的地區(qū),也有非相鄰的地區(qū)。例如土耳其的吉爾吉斯人和中亞的吉爾吉斯人在地理上沒有直接接壤,吉爾吉斯斯坦的吉爾吉斯人和俄羅斯的吉爾吉斯人也沒有直接接壤,阿富汗的吉爾吉斯人與吉爾吉斯斯坦的吉爾吉斯人以及我國東北的柯爾克孜(吉爾吉斯)人完全沒有接壤。
第五,跨境時(shí)間方面更加復(fù)雜。有些地區(qū)的跨境時(shí)間較長,而其他地區(qū)則較短。例如自18世紀(jì)末我國、英國和俄羅斯帝國的邊界劃定以來,我國境內(nèi)的柯爾克孜(吉爾吉斯)人與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哈薩克斯坦境內(nèi)的吉爾吉斯人之間已有將近一個(gè)多世紀(jì)的跨境歷史。然而,如果以蘇聯(lián)解體后為基準(zhǔn),其他中亞國家的吉爾吉斯語與吉爾吉斯斯坦吉爾吉斯語之間的跨境歷史僅有30多年。土耳其的吉爾吉斯人已經(jīng)遷徙了近半個(gè)世紀(jì)。而跨境歷史最悠久的是我國東北黑龍江省富裕縣的柯爾克孜(吉爾吉斯)人,他們自元朝開始就從葉尼塞遷徙到現(xiàn)在的地方,跨境歷史長達(dá)近八百年。根據(jù)相關(guān)研究,他們經(jīng)歷了三次遷徙。最早的一次遷徙發(fā)生在1293年,當(dāng)時(shí)元朝(蒙古大帝國)的創(chuàng)始人忽必烈將部分吉爾吉斯人從葉尼塞遷徙到我國松花江河岸,并使他們從事農(nóng)業(yè)[3]。目前尚不清楚他們是否融入了其他民族。此外,1732-1761年,我國清朝的這些古代吉爾吉斯人的祖先遷徙到了現(xiàn)在黑龍江境內(nèi)[4]。
第六,吉爾吉斯語的跨境語言差異情況有所不同。讓我們首先談?wù)劮植荚谧钗鞫说募獱柤拐Z情況。在過去的半個(gè)世紀(jì)中,土耳其的吉爾吉斯語在詞匯方面發(fā)生了變化,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這些變化可以通過相關(guān)的視頻和書面材料觀察到。年輕人的語言使用出現(xiàn)了雙語現(xiàn)象,即他們同時(shí)使用吉爾吉斯語和土耳其語,并在吉爾吉斯語中混入一些土耳其語詞匯。年輕人逐漸轉(zhuǎn)向使用土耳其語的趨勢(shì)。一方面,山川地形阻隔了與其他國家的吉爾吉斯人之間的接觸,如果必要的話,只能通過交流工具進(jìn)行交流。另一方面,該地區(qū)的吉爾吉斯人口相對(duì)較少,受到土耳其語的影響,語言發(fā)生了演變。另外,他們的祖先是來自帕米爾高原的原住民,在較早的時(shí)候就已經(jīng)定居在那里。眾所周知,帕米爾地區(qū)的生活條件惡劣,交通不便,因此當(dāng)他們?cè)谶@里定居時(shí),無法與其他地方的吉爾吉斯人保持密切聯(lián)系,處于相對(duì)孤立的狀態(tài),在語言上保留了古代詞匯。另一方面,土耳其的吉爾吉斯語本來就屬于吉爾吉斯語西南部的方言,與其他地方的吉爾吉斯語存在一些較大的差異。至于阿富汗的吉爾吉斯語,正如前面所述,那里的吉爾吉斯人是土耳其吉爾吉斯人的祖先。他們居住在阿富汗的帕米爾地區(qū),生活條件惡劣,交通不便,人口數(shù)量明顯較少(兩三千人),外來文化很難進(jìn)入該地區(qū),可以說是典型的被山川所隔絕的群體。他們?cè)谡Z言上保留了吉爾吉斯語西南部方言的特點(diǎn)。與吉爾吉斯斯坦的吉爾吉斯語相比,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周邊國家境內(nèi)的吉爾吉斯語的跨境語言差異相對(duì)較小。這是因?yàn)樗鼈冊(cè)缧r(shí)候曾統(tǒng)一屬于蘇聯(lián),受到俄羅斯語言和文化的影響。盡管蘇聯(lián)于1991年解體,中亞各國獲得獨(dú)立,但他們?nèi)匀粺o法完全擺脫俄羅斯對(duì)中亞的軟實(shí)力影響。因此,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國家境內(nèi)的吉爾吉斯語差異相對(duì)較小。談到我國的柯爾克孜語和其他國家的吉爾吉斯語,正如前文所述,這兩個(gè)國家的吉爾吉斯(柯爾克孜)語已經(jīng)分離了一個(gè)多世紀(jì),并且這種語言差距還在擴(kuò)大。其外部原因是我國境內(nèi)的柯爾克孜語過去受到維吾爾語的影響,近十幾年來漢語對(duì)吉爾吉斯語的影響逐漸顯現(xiàn)。如今,我國境內(nèi)會(huì)說中文的柯爾克孜人(吉爾吉斯人)逐漸增多,很多人是雙語或多語使用者,年輕人基本上都會(huì)說中文,整體人口素質(zhì)提高,文化交流也更加緊密。語言內(nèi)部原因是我國境內(nèi)的柯爾克孜族有其獨(dú)特的文字和語言規(guī)范體系,保留了相對(duì)多的古代語言詞匯。因此,我國境內(nèi)的柯爾克孜語和其他國家境內(nèi)的吉爾吉斯語走向了各自不同的發(fā)展方向。
三、吉爾吉斯語中、吉跨境變異的體現(xiàn)形式
跨境語言的變異通常表現(xiàn)在語音、詞匯、語法、語義和文字等方面。其中,詞匯方面的變異最為顯著[5]。就語音而言,吉爾吉斯斯坦的吉爾吉斯語和我國的柯爾克孜語在語音數(shù)量以及同一詞中的少數(shù)音位發(fā)音等方面存在差異。
(一)語音差異
吉爾吉斯斯坦的吉爾吉斯語中共有39個(gè)音位,與我國的柯爾克孜語在輔音音位上存在差異,其中包括ц、ж、щ三個(gè)輔音音位,以及я、ё、ю、е四個(gè)復(fù)合音。這三個(gè)輔音音位和四個(gè)復(fù)合音主要用于源自俄語的外來詞,其引入主要受到俄語的影響。在元音數(shù)量方面,兩種語言沒有差異,都有14個(gè)元音。此外,一些單詞中的音位發(fā)音存在差異,具體差異如表1所示。
從表1可以看出,吉爾吉斯斯坦的吉爾吉斯語和我國的柯爾克孜語在許多語音方面存在明顯的差異。首先,吉爾吉斯語將字母“o”讀作“a”,而不是“o”。而我國的柯爾克孜語按照語音發(fā)音的拼寫規(guī)則,將這個(gè)音讀作“o”。吉爾吉斯語中的“в”對(duì)應(yīng)于我國柯爾克孜語中的“p”,吉爾吉斯斯坦的吉爾吉斯語中的“ц”對(duì)應(yīng)于我國柯爾克孜語中的“s”,吉爾吉斯斯坦的吉爾吉斯語中的“у”對(duì)應(yīng)于我國柯爾克孜語中的“o”,吉爾吉斯斯坦的吉爾吉斯語中的詞尾“д”對(duì)應(yīng)于我國柯爾克孜語中的“т”,吉爾吉斯斯坦的吉爾吉斯語中的“щ”對(duì)應(yīng)于我國柯爾克孜語中的“ч”。此外,吉爾吉斯斯坦的吉爾吉斯語一個(gè)音節(jié)中可以出現(xiàn)兩個(gè)元音,而我國的柯爾克孜語則不會(huì)出現(xiàn)這種情況。
從表1可以清楚地看出,對(duì)于個(gè)別詞語而言,吉爾吉斯斯坦的吉爾吉斯語和我國的柯爾克孜語在一些語音上是相對(duì)應(yīng)的。吉爾吉斯斯坦的吉爾吉斯語的這種差異主要是受到俄語的影響而產(chǎn)生的,而我國的柯爾克孜語則保留了其原有的語音和發(fā)音規(guī)則。
(二)詞匯差異
詞匯差異主要體現(xiàn)在用詞的差異和造詞特點(diǎn)兩個(gè)方面。用詞的差異可以在外來詞、新詞和固有詞中觀察到。表2是外來詞的一些示例,展示了詞匯差異。
在這些例子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吉爾吉斯斯坦吉爾吉斯語中的借詞主要來自俄語和英語,而我國柯爾克孜語中的借詞主要來自漢語。尤其是近年來,從漢語中借用的外來詞在柯爾克孜語中被原汁原味地使用。
此外,兩種語言在新詞的使用方面也存在差異。表3是吉爾吉斯語和柯爾克孜語中一些新產(chǎn)生的詞匯示例。
從表3可以看出,在吉爾吉斯斯坦吉爾吉斯語中新產(chǎn)生的一些詞匯,我國柯爾克孜語中采用了借詞或固有詞的方式進(jìn)行替代。同樣,在我國柯爾克孜語中新形成的一些詞匯,在吉爾吉斯斯坦吉爾吉斯語中則使用了一些借詞進(jìn)行替代,具體如表4。
這些示例展示了吉爾吉斯斯坦吉爾吉斯語和我國柯爾克孜語中新詞形成的差異和借詞的使用情況。
這兩個(gè)國家的吉爾吉斯語在使用自古以來的固有詞方面也存在差異,例如在表5中,我們可以看到吉爾吉斯斯坦吉爾吉斯語包含了許多從俄語中吸收的外來詞,而我國柯爾克孜語則相對(duì)保留了固有詞。俄語對(duì)吉爾吉斯斯坦吉爾吉斯語的影響深遠(yuǎn),其中包括很多俄語單詞,甚至這些借詞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基本詞匯中也存在。例如月份名稱、星期一到星期天每天的稱呼,甚至早上、中午、晚上等時(shí)間名稱都來自俄語。
這些例子表明俄語對(duì)吉爾吉斯斯坦吉爾吉斯語的影響廣泛,這種影響跨越了不僅僅是特定領(lǐng)域的詞匯,而是延伸到日常生活中的基本詞匯和時(shí)間表達(dá)。吉爾吉斯斯坦吉爾吉斯語和我國柯爾克孜語在固有詞的使用上存在差異,可能由于歷史、文化和語言接觸等因素導(dǎo)致的語言演變和發(fā)展。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觀察到吉爾吉斯斯坦吉爾吉斯語中的借詞主要來自俄語和英語,這反映了俄羅斯文化和國際交流對(duì)該地區(qū)的影響。許多俄語和英語詞匯被吉爾吉斯語直接引用或適應(yīng),以滿足新的概念和現(xiàn)實(shí)生活的需要。這種借詞現(xiàn)象在語言中形成了一種跨文化的交融。
而在我國的柯爾克孜語中,借詞主要來自漢語。特別是近年來,從漢語中借用的外來詞在柯爾克孜語中被原汁原味地使用。這反映了我國各民族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和文化交流。隨著經(jīng)濟(jì)合作和人員往來的增加,漢語成為柯爾克孜語中的重要借詞來源,涵蓋了各個(gè)領(lǐng)域,如科技、商業(yè)、娛樂等。
這種借詞現(xiàn)象對(duì)吉爾吉斯語和柯爾克孜語的詞匯豐富化和發(fā)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dòng)作用。借詞的使用不僅豐富了語言表達(dá)的能力,還促進(jìn)了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和理解。同時(shí),這也反映了語言的適應(yīng)性和變化性,以適應(yīng)不斷變化的社會(huì)和文化環(huán)境。
(三)語法差異
語法差異主要表現(xiàn)在一些短語或句子中的單詞順序以及造詞時(shí)的詞綴使用上。吉爾吉斯斯坦吉爾吉斯語和我國柯爾克孜語在語法方面存在許多差異。這個(gè)主題是一個(gè)更廣泛而復(fù)雜的課題,我們只舉一個(gè)已知的比較突出的語法差異的例子。例如在吉爾吉斯斯坦吉爾吉斯語中,表達(dá)“非常感謝”的詞組是“ыракмат чо■”,而我國柯爾克孜語中則是“чо■ ыракмат”。這意味著單詞順序發(fā)生了變化。同樣,在生日祝福中,吉爾吉斯斯坦吉爾吉斯語中說“туулган к■н■■ менен”,而我國柯爾克孜語說“туулган к■н■■ кут болсун”。前者受到俄語影響導(dǎo)致語序變化。
此外,吉爾吉斯斯坦吉爾吉斯語中使用了詞綴“-ский”來構(gòu)造一些詞語,這些詞語在口語中很常見,例如“Китайский”(中國的)、“женский ”(女性的)等,這個(gè)詞綴來自俄語,而在我國柯爾克孜語中則沒有這個(gè)詞綴。這意味著吉爾吉斯斯坦吉爾吉斯語不僅在語音和詞匯方面受到俄語的影響,而且在造詞方面也受到了影響,從而增加了其語法特點(diǎn)并增強(qiáng)了其生命力。相比之下,我國柯爾克孜語中外語的影響沒有那么深刻。
(四)語義差異
我國柯爾克孜語和吉爾吉斯斯坦吉爾吉斯語在語義上也存在差異。例如在吉爾吉斯斯坦吉爾吉斯語中,詞匯“улут”表示民族,并且已經(jīng)擴(kuò)展到國家或人民的意義,而我國柯爾克孜語中僅表示民族的概念。另外,詞匯“кат”在吉爾吉斯斯坦吉爾吉斯語中表示信封,而在我國柯爾克孜語中除了信封的意思外,還具有“字”的含義。目前,吉爾吉斯斯坦吉爾吉斯語使用詞匯“иеорогилф”來表示字。詞匯“жа■ылык”表示“新聞”,而我國柯爾克孜語中的“жа■ылык”沒有新聞的意思,而是表示“新事物”或“新東西”,而“新聞”一詞用“кабар”來表達(dá)。在吉爾吉斯斯坦吉爾吉斯語中,詞匯“кызыкчылык”的意思是利益,而在我國柯爾克孜語中表示興趣,而非利益的意思。詞匯“манил■■”在吉爾吉斯斯坦吉爾吉斯語中表示“重要的”,而在我國柯爾克孜語中表示“有意義的”。吉爾吉斯斯坦吉爾吉斯語中說“светти к■йг■з”表示“開燈”,而我國柯爾克孜語說“чыракты жарыт”表示“點(diǎn)燈”。詞匯“агай”在吉爾吉斯斯坦吉爾吉斯語中表示“老師”,而在我國柯爾克孜語中表示“長兄”。詞匯“азчылык”在吉爾吉斯斯坦吉爾吉斯語中表示少數(shù)民族,而我國柯爾克孜語使用“аз сандуу улут”來表示少數(shù)民族。吉爾吉斯斯坦吉爾吉斯語中使用詞匯“чогулуш”表示“會(huì)議”,而我國柯爾克孜語中該詞表示“活動(dòng)”“集中”。詞匯“кыймыл”在吉爾吉斯斯坦吉爾吉斯語中表示“動(dòng)作”“行動(dòng)”,而我國柯爾克孜語中除了這一含義外,還包括“運(yùn)動(dòng)”和“革命”的意義。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值得進(jìn)一步收集和整理。
(五)文字差異
在過去,吉爾吉斯人通常使用察合臺(tái)文進(jìn)行交流。然而,如今不同國家境內(nèi)的吉爾吉斯人使用不同的文字系統(tǒng)。在中亞地區(qū),吉爾吉斯人使用西里爾文作為主要的書寫系統(tǒng)。這可以追溯到蘇聯(lián)時(shí)期的影響,當(dāng)時(shí)蘇聯(lián)將西里爾字母引入該地區(qū)的語言文字中。西里爾文的使用使得中亞吉爾吉斯人能夠與俄羅斯人和其他西里爾字母使用國家的人進(jìn)行更容易的交流和合作。
而阿富汗境內(nèi)的吉爾吉斯人使用波斯文作為書寫系統(tǒng),這與阿富汗主流文化和波斯文化的影響有關(guān)。這種差異可能使得阿富汗的吉爾吉斯人在與其他吉爾吉斯族群的交流中遇到一定的障礙。
在我國,柯爾克孜人使用基于阿拉伯文的文字系統(tǒng),而我國東北地區(qū)的柯爾克孜(吉爾吉斯)人則使用中文。這些差異反映了我國不同地區(qū)的歷史和文化背景對(duì)吉爾吉斯人語言的影響。柯爾克孜人的阿拉伯文書寫系統(tǒng)可能受到了阿拉伯文化和周邊地區(qū)的影響,而我國東北地區(qū)的柯爾克孜(吉爾吉斯)人使用中文則反映了他們與漢族人的接觸和交往。
四、吉爾吉斯語跨境變異的成因
跨境語言變異是由地理和社會(huì)因素所引起的。從地理角度來看,跨境語言與地域方言和土話類似,它們由于自然空間的隔離,如山脈和河流,導(dǎo)致語言內(nèi)部逐漸出現(xiàn)差異。目前,全球吉爾吉斯人居住在幾個(gè)相鄰的國家境內(nèi)。從社會(huì)角度來看,這是由國界劃分、不同的政治、經(jīng)濟(jì)和文化制度等社會(huì)空間的影響所致。從東到西,我國東北的富裕吉爾吉斯人早期就遷移到東部,與其他民族混居,并逐漸受到他們的影響,如今已沒有使用母語的人。我國新疆境內(nèi)的柯爾克孜人受到周邊民族的影響,近年來漢語的影響明顯增加。另一方面,該地區(qū)的大部分吉爾吉斯人居住在山區(qū),他們的母語得以相對(duì)保存良好。阿富汗的吉爾吉斯人受到普什圖語言和文化的影響,此外,由于外部因素的影響較少,其語言保持相對(duì)純正。中亞地區(qū)的吉爾吉斯語主要受到俄羅斯文化的影響,并在多樣化的語言環(huán)境中得到廣泛發(fā)展。土耳其的吉爾吉斯人受到土耳其文化的影響,加上人口少,走上了一條不同的發(fā)展道路。然而,這兩個(gè)因素,社會(huì)和地理,密切相關(guān)且難以分割。由于地理和社會(huì)因素的相互作用,跨國語言的變異速度比普通方言和地方語言更快。
五、結(jié)語
吉爾吉斯族作為中亞地區(qū)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其歷史上受到多個(gè)統(tǒng)治者的影響,因而不斷遷徙,造成吉爾吉斯語在不同時(shí)期和地區(qū)的演變。中國黑龍江地區(qū)的柯爾克孜人(吉爾吉斯人)源自葉尼塞河流域的遷徙,其語言直接延續(xù)了古代吉爾吉斯語,而如今則已轉(zhuǎn)變?yōu)闈h語。19世紀(jì)后期,由于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原本居住在中亞高山地區(qū)且具有類似地理環(huán)境的吉爾吉斯人分散至不同國家,其中一部分被沙俄、然后后期的蘇聯(lián)統(tǒng)治,使用斯拉夫字母,接受大量的俄語詞匯,另一部分則仍處于我國清朝的支配之下。繼承早一些的語言和文字,并創(chuàng)造阿拉伯字母基礎(chǔ)上的文字系統(tǒng)。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柯爾克孜族等少數(shù)民族在語言文字方面取得了顯著進(jìn)展與發(fā)展,他們的母語柯爾克孜語從維吾爾語、漢語吸收詞匯,豐富其詞匯,也得到了廣泛的保護(hù)和發(fā)展,并開辟了獨(dú)特的發(fā)展道路。到了20世紀(jì)七八十年代,一部分生活在蘇聯(lián)境內(nèi)的吉爾吉斯人遷徙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最終在土耳其定居,這進(jìn)一步加劇了吉爾吉斯語的跨境變異。蘇聯(lián)解體后,吉爾吉斯語的跨境變異進(jìn)一步加劇,即絕大部分吉爾吉斯人除了居住在吉爾吉斯斯坦,還有少部分分布在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哈薩克斯坦等鄰國,因此也受到其他民族語言的影響。
吉爾吉斯語的跨境特征可以概括為多國使用、使用人口數(shù)量不同、族名差異化、地理分布復(fù)雜、時(shí)間復(fù)雜、語言差異情況不同的特點(diǎn)。將吉爾吉斯斯坦吉爾吉斯語和中國的柯爾克孜語比較,可以發(fā)現(xiàn)吉爾吉斯斯坦吉爾吉斯語在語音、詞匯、語法等方面不同程度受到了俄語的影響,中國柯爾克孜族則多受到了漢語的影響。分析與研究吉爾吉斯語跨境變異的原因,既要關(guān)注語言內(nèi)部的發(fā)展變化,同時(shí)也要注意外部因素的影響,例如國界阻隔,所在國的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體制不同,所在國的民族語文政策等。將內(nèi)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統(tǒng)籌結(jié)合,便于更好地去研究吉爾吉斯語的跨境變異。
[參考文獻(xiàn)]
[1]賈依肯.唐前期堅(jiān)昆(結(jié)骨)國與唐朝的交往[J].《歐亞學(xué)刊》,2019,(09):1-2.
[2]戴慶霞.社會(huì)語言學(xué)[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4:71.
[3]吳元豐.柯爾克孜族東遷黑龍江歷史研究評(píng)述[J].黑龍江民族叢刊,2001,(01):77.
[4]戴慶霞.社會(huì)語言學(xué)[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4:78.
[5]Baytur, A. Lectures on Kirghiz History. Artish: Kizilsu kirghiz press,1986:228.
[6] Кееш Жспов.“Кыргыздар” (Санжыра, Тарых, Мурас, Салт), Бишкек: Кыргызстан басмасы, 1991.
[7] Реми Дор.“Ооган Памириндеги Кыргыздар”(Тарыхый-этнографиялык баян), которгон.П.Казыбаев, Бишкек: Кыргызстан басмасы, 1993.
[8] Sh. Japarov, T.S. (2013).Textbook of dialectology of the Kyrgyz language (2ed.).Bishkek: I.Arabaev Kyrgyz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9] Sartbaev, K.K., Kudaybergenov, S.Akmatov,T.K.(1980).Grammar of the Kyrgyz literary language. Frunze(Kyrgyzstan): Ilim Publishing House.
[10] Mukambaev, J. (1972). Dialectical dictionary of the Kyrgyz language. 1(6). Frunze, Kyrgyzstan: Ilim Publishing Ho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