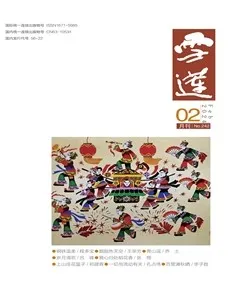向晚眠火炕
【作者簡介】 任靜,女,陜西省作家協會會員,陜西省青年文學協會會員。著有散文集《枕著你的名字入眠》 《想要一座山》,長篇小說《浮生》《淬火》,公開發表散文、中短篇小說、詩歌等計300余萬字。作品散見于《文藝報》《光明日報》《中國文化報》《中國青年報》《農民日報》《延河》《延安文學》《佛山文藝》《文學天地》《作家天地》等報刊。
1
我出生在一鋪火炕上,火炕是我抵達人世間的起點。
在我的故鄉西北黃土高原,不管是富裕還是貧窮,家家戶戶少不了一鋪滾燙的火炕,火炕是家里最顯眼的陳設。貴客迎進門,最高的禮遇是殷勤請上炕。一張油漆四方炕桌擺在火炕最中間,瓜果梨棗,花生瓜子一股腦兒傾囊而出,家鄉的父老鄉親最是慷慨,很快就有一盤熱騰騰的油糕,一壇熱滾滾的米酒端上桌來。賓主皆歡,圍著炕桌嗑瓜子,剝花生,吃紅棗,嘮家常,一杯一杯勸酒,喝得興起時,酒曲唱起來,秦腔吼起來,鏗鏘的道情,悠揚的民歌飄出窗外,歡快地縈繞著山圪梁梁。此時,故鄉的火炕,最是它的熱鬧榮光時刻,仿佛舉行一場盛大的音樂會。歌者立于燈前扯開嗓子唱,聽眾沉醉其中,或擠立地下,或坐擁炕頭,或干脆愜意地躺進灶圪嶗的柴火堆上,個個搖頭晃腦沉迷于激越悠揚的旋律中,有人沉浸式的隨著節拍敲碗打筷,好不熱鬧盡興。
故鄉火炕最喜慶的時刻,是新娘子娶回家,洞房花燭夜。記憶中最切近的一位新娘子是表嫂。表嫂被震天嗩吶響吹細打迎回來時,已是黃昏時分,所有的燈都被撳亮了,院子里的路燈映照著打彩門的紅綢,晚風將裹紅綢的黑色絲穗吹得簌簌作響。那是我見過表嫂這一生最為光鮮亮麗的時刻。她身穿一身紅衣,被人從驢背扶下來,背坐在洞房的炕上,身影端莊,低眉含羞,接受眾賓客的注目禮。炕席四角凹凸的地方,舅媽預先給壓了桂圓、紅棗、花生和喜錢,象征了早生貴子的美好寓意。緊接著要進行一道“上頭”儀式,據說是木命的一位長輩親戚將表嫂的長發放在表哥的寸頭上,象征性地梳攏,嘴里喃喃有詞:“一梳金,二梳銀,三梳梳個聚寶盆,四梳兒孫滿炕跑……”上頭儀式嚴肅而虔誠,仿佛完成了一對新人生命的交付,此生此世將與身邊這個人榮辱與共,不離不棄。故鄉的“上頭”儀式,就好比西方教堂里神父肅然宣讀結婚誓詞:“無論貧窮還是富有、疾病或健康、美貌或衰老、順利或失意……”
夜幕降臨,按鄉俗,窗根下的暗影里一定會立著幾位聽房者,屏聲息氣不敢發出絲毫動靜,生怕驚動了屋里漸入佳境的小夫妻。聽房的有長輩,潑辣的嫂子們,還有村里一幫漸已洞曉男女之事的小伙子們。女孩子一般是不參與聽房的。聽房者個個縮著脖頸,忍著陣陣二半夜襲來的寒流,聽得面紅耳赤,津津有味。
黎明前,趁小夫妻熟睡之際,新升任公婆的舅舅和舅媽撕破新房的窗戶紙,給炕上扔進去幾個雪白的紅點饃饃,這是本地一種鄉俗,其中滿含著健壯兒女滿炕跑的寓意。
2
草席是炕上最重要的鋪陳。一些人家可能還會在草席上鋪上幾條黑沙氈、白棉氈,滿炕大的棉線老虎單子,碧綠干凈的油漆布,其上通常會盛開著大朵馥郁的荷花。光景好的人家,更講究一點,在棉氈上再鋪一大塊暖融融的手工栽絨毛毯,印有富貴吉祥的圖案。在我的故鄉,日子即使過得再清貧,誰家的熱炕上也不會少了一領草席。草席宛如熱炕上一只碩大的翅膀,每夜馱著一家人的夢飛翔。
草席,別的地方通常用藤子、蘆葦、蒲草或竹條等編織而成。在我的故鄉,編織席子離不了紅高粱。紅高粱,北方又叫稻黍。在硬朗的北方,稻黍是秋天蔥蘢的景象。青紗帳,白象床,晚涼生,月輪初上。故鄉只有青紗帳,縱橫交織的青紗帳是鄉野秋天最美的風景。白象床確乎沒有,也不需要,有一鋪冬暖夏涼的火炕足矣。白象床,大概屬于南方大戶人家的家什,就像《金瓶梅》中孟玉樓陪嫁的南京描金彩漆拔步床,李瓶兒陪嫁來的羅鈿床。
故鄉不產稻子等南方作物,但是盛產稻黍和玉米,玉米產量最高,占領了灌溉便利的平川地。而比較耐旱的山坡地,則是生命力旺盛的稻黍與谷子的樂園。到了立秋時分,黃土高坡仿佛就成了稻黍的天下,一株株頂著沉甸甸紅彤彤的穗子,格外惹眼,密布于漫山遍野,像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排兵布陣。當農人穿梭于那林間,便親密地接觸了大自然的肌膚,感受到了黃土地顫動的脈搏。大暑小暑,稻黍趁著陽光憋足了勁兒生長。立秋三天鐮刀響,稻黍顆粒歸倉。
收獲后,別的莊稼秸稈都用來當作農家燃料,唯有稻黍秸稈上端那些細長端直的蔪蔪,還要被派上大用場,納蓋簾、編席子都少不了它們。每逢冬月閑下來后,勤謹能干的農人,便動手扦掉稻黍穗,整理出來幾捆稻黍秸稈,剝盡葉子,先往秸稈上灑水使秸稈潮濕,再用篾刀將上端的蔪蔪一劈兩半,仔細把中間的芯瓤刮干凈,然后使勁兒用碾棍碾壓。還要在水里耐心泡幾日,直至泡得軟硬適度,堅韌而富有彈性為止。這樣耐心處理出來的蔪蔪皮,無節,平展,適于編織成一領潔白的席子。
我的父親是一位心靈手巧的陜北漢子,他會編織毛衣、毛襪子,還會編籠,編席子。少年時的夏夜,我望著瑩白細長的蔪蔪皮,在父親手指尖歡快地起伏跳躍,驚奇不已。繼而看到父親身后很快出現了一大片縱橫交錯的潔白花紋,那一刻,父親宛如坐在輕盈的云朵上了。我便想到孫犁筆下的水生嫂:“月亮升起來,院子里涼爽得很,干凈得很,白天破好的葦眉子潮潤潤的,正好編席。女人坐在小院當中,手指上纏絞著柔滑修長的葦眉子。葦眉子又薄又細,在她懷里跳躍著。”父親手法快,一領丈二長的席子,兩天就能編好,平展展地鋪在熱炕上。稻黍蔪蔪用它曾經丈量過陽光長度的身體,又開始丈量一個家庭的喜樂年華。
我們那地方很少有賣席子的人,每家每戶都有現成的稻黍蔪蔪,不會編席子的,也會想辦法用自家的體力、畜力或農具等變工請別人來編。在小城農貿市場,我曾見過一個賣席子的,用一根粗壯的木棍,挑著一卷草席進了市場。許多草席被緊緊卷成圓筒狀,腰里用麻繩系著,像身著縞素的清麗女子,一卷一卷地豎立在寬敞的地面上,令我想起剛剛看過的一部電影《卷席筒》。這是一個澄清冤案,大快人心的感人故事。因為一領打算收尸的卷席,使得故事主人公倉娃被皇上封為正五品“卷席將軍”。
“紅旗溝的席,火炕上的寶。賣席子嘍,三年五年睡不爛……”賣席人滿口鄉音,粗獷的吆喝聲,歡快地穿梭于各種噪雜的市聲中,很快有婦人被吸引過來,解開麻繩,將席子攤開在地面,仔細查看編織的是否精細,紋路是否密實。有婦人細心,還用粗糙的手掌一遍一遍地撫摸席面,試探那席子刮不刮肌膚,一邊摸一邊贊,紅旗溝的席子真是耐磨,吸汗,還說她已經在家里的舊席子上生養過四個孩子。
有一年還鄉,看到故里的老屋已經破敗得不像樣了,透過鏤刻精美的棗木窗戶,散發出一股久遠的落寞氣息。炕席卷起來放在炕頭,窯頂中間一塊墻皮坍塌下來,不偏不倚地砸到炕席卷上,炕席卷凹陷了下去,仿佛我兒時玩過的對折卷紙筒游戲一樣,翹起了兩旁的小喇叭。環顧寂然落寞的村莊,我知曉村莊里的兒童再也不會玩那種對折游戲的小喇叭了,更不需要一領稻黍蔪蔪皮編織的席子,他們甚至連村莊也不需要了,許多人早已遠離故土,到城市安家落戶。我定定地望著炕上翹起的小喇叭,眼前浮現出曾經豎立在農貿市場上那一卷卷潔白的席子,它們展開云霞般美麗的翅膀,引領著我濃郁的鄉愁,穿越時空飛回故里。
3
還是那鋪火炕,總是少不了一個拴孩子的炕頭石獅子。沉甸甸的炕頭石獅子,是守護神,被賦予守護孩子的魔法。每過一個生日,炕頭獅子身上就要被纏裹上一圈孩子過生日時戴過的紅色鎖線。滿十二歲時,十二根鮮紅的鎖線才從炕頭石獅子身上解下來,捻成一根褲腰帶讓孩子系在腰上,說是辟邪。秋夜,勁風呼呼吹得門楣上的對聯簌簌作響。勤勞的母親們,舍不得早點鉆入熱被窩,總要盤腿坐在炕上,在煤油燈下飛針走線,熬上大半夜為一家老小做鞋補衣。
腰里系著鮮紅鎖線的少年,依然愛撫著從小陪到大的炕頭石獅子,透過斑駁的月光,呆呆望著窗外被風吹亂的樹影出神。樹影映照在窗戶紙上,一忽兒像條白龍,一忽兒宛如奔馬,一忽兒是朵朵粲然盛開的菊花,一忽兒仿佛仙女提著籃子向人間散花……變化莫測的樹影,天馬行空地豐富了少年貧瘠的想象力。火炕燒得正好,母親新絮的棉被,在陽光下曬過,特別松軟,說不出的安逸暖身,它的柔滑觸感有大自然的親和,埋頭輕嗅,棉花有股子陽光的味道和秋季綿綿的田野氣息,像母親溫暖的手輕撫過額頭。少年乘著想象的快馬,很快進入了香甜的夢鄉。耳畔隱約飄過母親清甜的歌聲:雞蛋殼殼點燈,半炕炕明,燒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窮……
剛記事那年七月的一天,我一覺從睡夢中醒來,驚異地發現家里的氣氛與平常有些不同。窯洞里彌漫著一些渾濁悶熱的空氣,血腥味兒、汗味兒和奶味兒,攪拌進母親痛苦的呻吟聲,母親的身旁睡著一個小東西,小東西穿著我兒時穿過的粉紅色小衣裳,甜甜地睡在小被窩里。原來是二妹出生了。父親不知何時候從城里趕回來了,正坐在炕沿上,對著襁褓中的二妹呵呵直樂。
我將視線從熱炕上移到腳地上,瞬間被眼前的情景震撼住了——大院里十多個年紀尚不太大的叔伯和姑姑們,正像士兵一樣整整齊齊地排列兩行,用好奇的目光檢閱著炕上那個小東西。小腳的外婆被接來了,和大腳的祖母一起做了妹妹的接生婆。北方人把做月子的地方叫月窩窯,母親躺在月窩窯的火炕上坐月子,要坐三四十天。虧空的身體需要進補,不能下地勞作,忌用生冷,忌受風寒,頭上晝夜包一塊厚厚的方頭巾,炕楞前圍了一塊大床單,用來擋風,小孩子不允許在月窩窯里打鬧,不然扇起的涼風會使月婆落下終身難以醫治的月子病。生產后的母親面色蒼白,神態疲憊,像秋天刈過的土地需要修整,這是勞作后獲得的恬靜的歇息,這片土地將在賴其生存的農人的關懷與融融秋日的愛撫下,靜靜地睡去,直至春風在它的夢里再度吹拂。
那一天,對于年幼的我來說,是喜憂參半的,我興奮地迎來一個妹妹,而那個妹妹卻霸道地侵略了我的地盤,從此壟斷了獨屬于我的乳香。以后,每次鋪炕時,我只能跟外婆睡。現在回憶起來,四五歲時,我已經領略過惆悵的滋味了。
4
到了冬天,西北風卷著雪沫肆意飛舞,撲打在白麻紙糊的窗戶紙上,發出噗噗的輕微聲響。我們身穿暖和的棉衣,腳踩棉窩窩奔走在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或者將墻頭晶瑩的雪粒含在舌尖上,舔舐那種凜冽的涼意,常常將屋內母親的呼喚置若罔聞。像這樣寒冷的天氣,大人們總喜歡煨炕,不再吝惜柴草的不易,從打麥場上摟來麥秸和豆窠,緩緩塞入爐灶內,在灰燼里順便埋入幾個紅薯或者土豆,慢慢煨熟。不一會兒,整個房間里彌漫開了烤紅薯和烤土豆的香氣。此時,不用母親再倚門呼喚,僅那股烤紅薯的香氣,就能把貪戀玩雪的孩子一個個揪扯回來。孩子們顧不得燙嘴,迫不及待地將烤紅薯塞進嘴里,陶醉在食物釅釅的香氣里。
在寒氣襲人的向晚時分,火炕已經燒得滾燙了,被窩早早焐好。我捧著一本泛黃的舊詩作,反復吟詠喜歡的句子:“向晚脫貂眠火炕,當風嘶馬踏冰河。”祖母對詩句不感興趣,她催促孩子們脫了衣服,在溫暖的熱炕上睡上一夜,百病全消。我鉆進熱乎乎被窩里,瞬間走進了詩人所營造的意境里,心頭不禁拂過絲絲感動的暖意。
半夜里,我被凍醒了一回,伸在外面的手臂凍得冰涼。原來是窗戶紙破了一個小洞,凜冽的寒風,順著那個小洞呼啦啦地灌進來。母親說針尖大的洞,一夜能鉆三斗三升風,明天得趕緊打了面黏子糊窗戶。冬季夜長,睡到后半夜又醒了,我鬧著讓母親給我說西游,母親不會講安徒生童話,像美人魚、丑小鴨,她全然不知,母親只會講一些老掉牙的故事,什么毛野人巧用智慧背走了鄰家的俏妹子,狼變成的白胡子老漢,竟然對可憐的孤兒發了慈悲之心,田螺姑娘趁家中無人,從專門擺放棗山的木方上飛下來,給勤勞的山里漢子做了一鍋香噴噴的小米飯……
漸漸地,天空呈現出淺青色的天光,風把天刮得十分干凈,幾顆小銀星星,圓盤一樣的月亮,掛在院子里最高的古槐樹上。黑黢黢的玉米架橫斜在槐樹下,隱約泛出陣陣飽滿的糧食香味,那是一種喜悅的收獲感。窗外是一個人造大平原,阡陌交錯,朗朗月光傾瀉下來,田畈一片銀白,仿佛鋪了一層厚厚的雪。那一切熟稔的景象,烙刻在記憶深處,是我今生難以割舍的精神皈依。
5
有一年,表叔來我家幫忙收秋。聽說他來了,我喜不自勝地從學校里跑回來。這位表叔雖然沒有念過多少書,卻裝了一肚子故事,他能繪聲繪色地講四大名著和《說岳全傳》《薛仁貴征東》《楊家將演義》等中國古典小說,這是童蒙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它們的奇幻色彩、英雄主義和人間正氣,適時地滋養了一個鄉村少女的骨骼與心智。這個寒涼而美麗的清秋,常常令我懷戀。我最喜歡聽表叔講《五女興唐傳》。勞累了一天的秋夜,表叔仰躺在火炕上,我們幾個半大孩子圍著表叔坐了一圈,在一盞昏黃的電燈下,眼巴巴地纏著他開講。
一提起講故事,表叔頓時也來了精神,他一骨碌坐起來,盤腿坐正,手里拿著兩根筷子,一個碟子,故意瞇縫著眼睛,模仿瞎子來村上說書的模樣,叮叮咚咚猛敲一氣。然后張口即來:“彈起三弦定起音,細聽我給大家說分明,今日我且不說張家長來李家短,說一段五女興唐傳……”表叔講得聲情并茂,昏黃的光線里,又敲出一氣急促的鼓點。在表叔給我家收秋的那十天里,我可謂享受了一頓精神盛宴。只是遺憾每當講到緊要處,表叔便犯困得不行,要且聽下回分解。當夜睡在炕上,我翻來覆去睡不著,回味著瞎子曾在村里說過的書,李懷玉、李懷珠兩位文曲星和武曲星怎地就引出五位奇女子,一把青龍寶劍在江湖上掀起一場軒然大波。
6
表叔終究還是離開了,任我怎么哭鬧也挽留不住。秋雨從后半夜開始下起,淅淅瀝瀝,順著青石板屋檐,滴答滴落,打濕了我晾曬在窗臺上的一雙花布鞋,也打濕了我沉浸在故事里綺麗的夢。夢里的我常常會變成颯爽英姿的吳月英,手執一柄青龍寶劍,像風一樣馳騁江湖,懲惡揚善。那一夜,火炕仿佛一艘古老的舟船,在雨滴匯聚的河流上,緩緩順水漂流。母親仍坐在燈下納鞋底,麻繩嘶嘶地穿過,恍惚間船槳輕搖著我的舟船。耳際再一次傳來外婆紡線的嗡嗡聲。外婆的紡車擺放在涼快的前炕上,像一位疲憊的老人,老得已經快要散架了,木軸轉動時吟唱的歌謠不再悠揚動聽。
“平常的扁食三分三,今兒的扁食一分一,因為你是個當兵的……”
這是我聽過外婆給我唱過的唯一一首古老歌謠。紡車在外婆手里搖呀搖,我的整個童年,就咿呀咿呀地隨著紡車快活地轉動。從早晨轉到黃昏,直至外婆脫下那件月白色的偏襟衫子,紡車聲和外婆悠揚的歌聲,才被一群星星拍打著翅膀馱進巢里,馱進我的夢里。
自從母親生了妹妹后,我就被送到距離我家五里路的外婆家,我記事初的童年時光里,彌漫著外婆的影子。外婆盤腿端坐在火炕上,我則坐在外婆懷里,一遍遍纏磨她講從前的舊事,外婆的母親給她纏了一雙粽子大小的三寸金蓮,怕她偷偷穿寬松的舊鞋子,狠心將舊鞋子剪破,揚手扔到柴房頂上。外爺在不惑之年撇下她和四個兒女,一病不起……外婆常常說著說著,就會傷感,聲息漸漸沉落下去,仿佛沉到水里,有淚水從眼眶里緩緩滲出,“啪嗒”一聲落下來,打濕了月白色的偏襟衫子,先是一滴,兩滴……慢慢擴大,像一朵褐色的落葉,別在了外婆月白色偏襟衫子胸前。
隊里分糧食時,我聽到過會計喊外婆的名字——“馬王氏”。我特別不喜歡那個缺少感情色彩的稱謂,我曉得,在婆家馬家和娘家王家,外婆從來沒有一次真正做過自己的主。有一天黃昏,外婆又坐在熱炕上給我講古,說到吳月英,她含羞說自己其實也有個好聽的名字,叫王月英。外婆說,自從你外爺去世后,再也沒有人喊過了。外婆的聲音里掠過一絲不易覺察的愁緒。我當時的注意力都在王月英這個名字上,瞬間聯想到表叔講過的《五女興唐傳》里的那些傳奇女子,心想,外婆是不是從故事里走出來的那位吳月英呢?
外婆去世那年,我在高考,錯過了外婆的葬禮。出得考場,我恍惚靈魂附體,變成了未曾謀面的外爺,借口傳言,仰頭對著虛空喊了一聲外婆的名字:“王月英!”
無人回應。
我又喊了一聲“王月英!”
回應我的仍是一片空曠。
我這才曉得,屬于我和外婆的那鋪火炕上,再也不會響起嗡嗡的紡線聲了。有兩行清淚倉皇落下,順著我的衣襟輕輕滑落,恍如那年秋夜,屋檐上寂寥的雨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