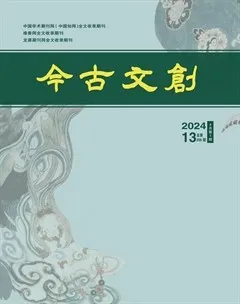淺述馬林諾夫斯基的科學民族志研究方法
【摘要】馬林諾夫斯基通過特羅布里恩德群島的長期田野調查,開創了科學民族志研究方法,使人類學研究的科學化程度大大提高。本文梳理了科學民族志研究方法確立的基礎,其方法的具體內容與創新,以及馬林諾夫斯基身后對其民族志研究的批判,指出馬林諾夫斯基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是在前人基礎之上結合自身田野實踐提出的,相較前人有若干突破,才能開創科學民族志研究的新范式,同時嘗試討論其在身后遭受的批判。
【關鍵詞】馬林諾夫斯基;科學民族志;實證主義;田野調查
【中圖分類號】K18?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13-0085-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13.025
民族志研究指的是對某一特定社群、文化現象展開的專門調查,并通過文字記述成“志”[1],在人類學處于發展階段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一稱呼往往專指對異民族的社會、文化現象的記述,它既是一種特定的文體,同時還是與田野調查相依托的一種特定人類學研究方法,并且隨著人類學的發展,人類學研究刻上了深深的田野印記,民族志研究成為人類學不可忽視的研究方式。
而20世紀上半葉馬林諾夫斯基對于科學民族志研究的探索,為民族志研究貼上了科學的標簽,同時也對人類學這門定義于社會科學的學科的科學化發展打上了不可磨滅的烙印。可以說現在對于人類學科學民族志研究方法發展的討論,永遠繞不開馬林諾夫斯基的貢獻和《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馬林諾夫斯基在前人對于民族志調查方式的探索基礎上,通過特羅布里恩德群島之旅的實踐,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學化的田野調查手段:通過不同于以往扶手椅上的人類學家的參與式觀察方法,極力縮小了人類學家與異民族之間的文化差異;通過了解異民族的“骨骼”“血肉”與“精神”,確定了一整套在此地(beingthere)的田野調查要求;通過客觀的民族志敘事,確立了民族志研究的科學色彩。
一、科學民族志研究方法確立的基礎
1910年,時年26歲的馬林諾夫斯基剛剛踏上英國之旅,懷揣著對英國的企盼和對人類學的熱情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投入了對人類學的學習。這一年出版了許多日后知名的人類學著作,如塞利格曼的《英屬新幾內亞的美拉尼西亞人》、弗雷澤的《圖騰崇拜與異族通婚》、蓋內普的《通過禮儀》,而就是在這一年,馬林諾夫斯基正式踏入了人類學領域,15年后,在回憶中馬林諾夫斯基將這一年描繪為人類學發展的轉折點[2]189。但對這個操著一口蹩腳波蘭口音英語的年輕人來說,當時的科學民族志研究領域并非一片空白,在實踐和理論上,都已經有前人為他鋪好了未來的道路。
此時英國乃至世界人類學發展的大趨勢,便是資料收集者和資料分析者的勞動分工正在被打破,以往扶手椅上的人類學家現在需要親自到田野中去,而不再是通過殖民官員、傳教士、探險家收集資料。這集中反映在英國人類學調查的指導手冊《人類學筆記和問詢》版本的變更上,初版由泰勒等人執筆,其目的是指導旅行者對原始人進行準確的人類學觀察,提供信息供英國國內的人類學者進行科學的人類學研究。而到了第四版,已經是為了受過專業訓練的研究者而非旅行者準備的了,還明確提出了一年周期的時間要求,而這個新版本的手冊正是突出了自然科學出身的新一代英國人類學家哈登、里弗斯、塞利格曼等人的觀點。而這三人對馬林諾夫斯基日后的研究產生了莫大的影響[3]45-47。
哈登、里弗斯、塞利格曼三人分別出身于動物學、實驗心理學、醫學病理學。在托雷斯海峽的探險和對人類學研究的共同熱情讓他們聚集于倫敦和劍橋。哈登對地理分布感興趣的進化論研究將他引向了田野調查。里弗斯通過在托利人當中數月的田野工作,提出了一個科學的田野調查框架,并提出了“譜系法”的研究技術。塞利格曼則通過頻繁的田野工作撰寫了《英屬新幾內亞的美拉尼西亞人》,這個富有科學精神的田野研究者盡管不喜歡理論創建工作,但走在倡導田野工作的第一線。這些新一代英國人類學家繼承了弗雷澤他們撰寫民族志的傳統,擅長對于專門性的異民族問題進行分析,但不同于分析資料提供者帶來資料所撰寫的《金枝》,新一代的英國人類學家提倡親身參與資料的收集,展開人類學家的“探險”。這一傾向一方面來自他們從自然科學帶來的科學實證精神,另一方面則是人類學發展專業化帶來的對資料收集專業性要求的必然反映。盡管在具體操作上,在田野調查的時間和參與程度上,他們的民族志研究方法還有待完善,但是這種用科學的研究方法收集資料的精神,無疑深深吸引了此時的馬林諾夫斯基,在英國經受的理論訓練,也為之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礎。
有關1914-1918年間,馬林諾夫斯基在特羅布里恩群島的研究,儼然已成為一個人類學領域的傳奇,但是馬林諾夫斯基究竟是在何時超出了前人的框架,提出了獨具特色的科學民族志研究方法仍然說法各異。張連海通過比較馬林諾夫斯基在此期間的三次民族志實踐,認為馬林諾夫斯基第一次在麥魯島上參與的人類學研究,依然是遵循《問詢與記錄》和里弗斯的親屬制度研究方法,進行不加區分的資料搜集,是一種沒有針對性的社會調查。而在后兩次針對特里布羅恩德群島的調查中,為了避免無意義的重復調查,他開始從特定的角度進行民族志研究。為了親眼見到更多事實,他開始在土著人當中扎帳篷[4]。為了深入理解土著文化,他開始放棄帶翻譯親自學習土著語言。馬林諾夫斯基在調研中開始量體裁衣,提出新的研究方法。
因此可以說,馬林諾夫斯基這些不同于扶手椅人類學家的科學民族志研究方法,一方面是建立在英國新一代人類學家以實證精神對民族志調查方式革新的基礎之上;另一方面更是建立在馬林諾夫斯基的田野調查實踐經驗需求之上。這兩方面經歷的共同基礎,則是當時日趨專業化的人類學研究發展的必然要求和更多科學實證精神的引入。馬林諾夫斯基正是人類學民族志研究方法科學化、專業化大潮的引領者、實踐者。
二、科學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內容
馬林諾夫斯基無疑十分重視自己的研究方法,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開頭的導論部分,他就明確了自己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圍。特別是對于科學民族志的資料收集方法,馬林諾夫斯基指出“民族志資料若要有確鑿可信的科學價值,就應該使我們能夠清晰地分辨出,哪些資料來自直接觀察及土著人的陳述和解釋,哪些則是作者基于常識和心理洞察力的推測”[5]14,因此他十分重視原始資料的重要性,在此之前,歐洲的人類學家的資料來源往往都是傳教士以及探險家的見聞,或者人類學家僅僅是短暫的在原住民的聚落落腳一陣,之后便在向導的簇擁中揚長而去,忽視了原始材料在此過程中能否真實地反映原住民生活的本貌,通過這樣的原始材料,也就很難站在被調查者的視角對其社會生活背后所反映的文化做出深入闡釋。
馬林諾夫斯基期望自己的研究可以“改變民族志的現狀,為后面的研究鋪墊道路”[5]14。為此他提出了自己的調查原則和調查方法,他認為田野調查應當堅持三個原則:即堅持科學的目標,將自己置于良好的工作環境當中;直接長期居住于土著人中間;使用若干特殊方法以搜集、操作、確定他的證據。同時他將自己的調查方法總結為骨骼、血肉以及精神,骨骼即調查對象的組織結構、文化框架,通過骨肉可以全面整體的了解調查對象的社會全貌。血肉即“不可測量”的例證、行為、細節,這些具體的行為則需要同土著進行親密接觸,進行參與式的觀察獲得。精神則是調查對象的觀點、看法、思考,馬林諾夫斯基特別強調通過學習土著人的語言,建立“文字語料庫”來了解土著人的精神,特別是土著人的巫術與宗教。通過結合骨骼、血肉與精神的資料,便可以“理解土著人的觀點、他和生活的關系,認識他眼中他的世界”[5]34,而在馬辛地區以及特羅布里恩群島,土著人最關心的便是“庫拉”這一獨特的貿易方式,馬林諾夫斯基便以此為中心進行了自己的研究。
相較于哈登、里弗斯、塞利格曼等人,馬林諾夫斯基的科學民族志研究方法有三個方面的突破。
首先是在研究的題材上,馬林諾夫斯基反對以往人類學家不加區分的資料搜集方式,而是認為應當帶著預設性問題即假設進入田野,這種問題是通過提前進行理論研究獲得的并應該隨著田野的調查進行改變,因此民族志資料的搜集也不是漫無目的的,而是圍繞問題展開的,并在離開田野后進行相應的理論概括,這種假設驗證的實證思路無疑極大地增強了民族志的科學性。
其次,在研究的過程上,馬林諾夫斯基提倡投身到土著人中間,這并不是單純調查時間上的疊加,而是一種長期的參與生活,與土著人生活的融合經驗,將為民族志研究帶來此前從未獲得過的資料,即一種參與觀察資料[5]15-18。
最后,在研究的實施上,馬林諾夫斯基極力重視學習研究對象語言的重要性,可能最初僅僅是在實踐中為了避免翻譯作為中介造成的資料損失和溝通困難,但是在研究中,馬林諾夫斯基發掘了語言作為思維工具對于思想的影響之深,想要對土著人的思想進行深入了解,就必須對土著人的語言進行深入發掘[5]428,這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及之后的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三、科學民族志研究方法的身后審視
馬林諾夫斯基對于特羅布里恩德群島的田野調查無疑是大獲成功的,其田野調查資料無疑也是翔實而充分的,在其結束調查,回到倫敦后,馬林諾夫斯基也利用自己的這次調查成果完成了對文化功能理論的建構,出版了《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等七部民族志專著,每一部都圍繞著一個特定的主題,這是他對民族志寫作最好的實踐。馬林諾夫斯基的研究無疑啟發了全世界的人類學者,在馬林諾夫斯基之后,無數的人類學家沿著馬林諾夫斯基開創的科學民族志研究方法道路繼續探索,科學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成為人類學田野調查的主流。
但除此之外,在馬林諾夫斯基去世之后,其調查日記《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日記》被出版之后,隨即引起了軒然大波,這本日記揭露了另一個不為人所知的馬林諾夫斯基,為我們展現了一個真實的,惆悵于白人和土著人之間、奎寧與海灘之間的真實的馬林諾夫斯基,它打破了完美的人類學家的表象。盡管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中馬林諾夫斯基立下了在田野調查中保持客觀性、對原住民最大限度的理解的原則,但日記確為我們展現了一位人類學家在真實的田野調查中面對的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張力,其中既有對原住民生活方式的難以理解和鄙夷,也有獨自生活在異鄉的思鄉之苦,還有身體上的病痛。而這一切都是一位人類學家“在當地”進行長期田野調查所必然遇到的困難[6]。
日記的出現打破了馬林諾夫斯基在民族志中為自己創造的神話,卻也折射出人類學家應該對自身的反思性,作為一個有主觀思維的個體,人類學家將自己作為觀察工具投入田野,但人永遠不是客觀的工具,人的主觀性在陌生的環境和社會當中會無限地放大,跨文化的理解也并非如此簡單,人類學家所能能做的只有努力去跨越這其中主觀與客觀的距離,這一距離或許將注定無法化解。但是正如日記所記述的,盡管輕視于土著人的“粗鄙”,沉迷于自己的思鄉之情,飽受愛情和身體上的痛楚,馬林諾夫斯基仍然在日記中時不時提及堅持自己的田野調查目標與計劃,堅持對特羅布里恩群島上的風土人貌進行記述,這也是盡管與自己的描述有偏差,馬林諾夫斯基的田野調查仍然能夠成為民族志的研究方法的典范的原因。
日記出版于1967年,恰恰就是在這個時段,整個人類學隨著后現代思潮和解釋學、現象學的傳播,進入了一個反思性的時代。民族志研究也被置于反思性審視當中,對于實驗民族志、現實主義民族志、后現代民族志等新方向的探索接踵而至。其中一個重要的探索方向就是作為民族志寫作者的研究者自身的主觀性和客觀性之間的關系,人類學家自身的主觀性被置身于討論當中。作為科學民族志研究方法的代表,馬林諾夫斯基和他的民族志研究在此時被批判性審視,被日記祛魅,或許恰恰為民族志研究方法的革新帶來了新的動力。而以實證精神為內核的科學民族志研究,并不會隨著馬林諾夫斯基的被批判走向終點,馬林諾夫斯基本身對科學民族志研究方法的開創意義和人類學學科科學化的貢獻也絕不會被埋沒,時至今日,仍然值得我們細細品味。
參考文獻:
[1]何星亮.文化人類學調查與研究方法[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4.
[2](澳)邁克爾·揚.馬林諾夫斯基——一位人類學家的奧德賽[M].宋奕,宋紅娟,遲帥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3]Urry J. "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ield Methods in British Anthropology,1870-1920[C].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972:45-57.
[4]張連海.論現實民族志方法的源起——以馬林諾夫斯基的三次民族志實踐為例[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41(02):71-79.
[5](英)馬林諾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M].弓秀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
[6](英)馬林諾夫斯基.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日記[M].卞思梅,何源遠,余昕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
[7]王銘銘主編.20世紀西方人類學主要著作指南[M].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9.
[8]高丙中.民族志發展的三個時代[J].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03):58-63.
[9]胡鴻保,張麗梅.“從事民族志”:馬林諾夫斯基與格爾茨[J].世界民族,2010,(01):38-44.
[10]彭兆榮.民族志“書寫”:徘徊于科學與詩學間的敘事[J].世界民族,2008,(04):34-41.
[11]王銘銘.遠方文化的迷——民族志與實驗民族志[J].西北民族研究,1996,(02):128-142.
[12]謝燕清.馬林諾夫斯基與現代人類學工作方式[J].民俗研究,2001,(01):132-143.
作者簡介:
劉寧超,男,漢族,內蒙古呼和浩特人,內蒙古工業大學人文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社會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