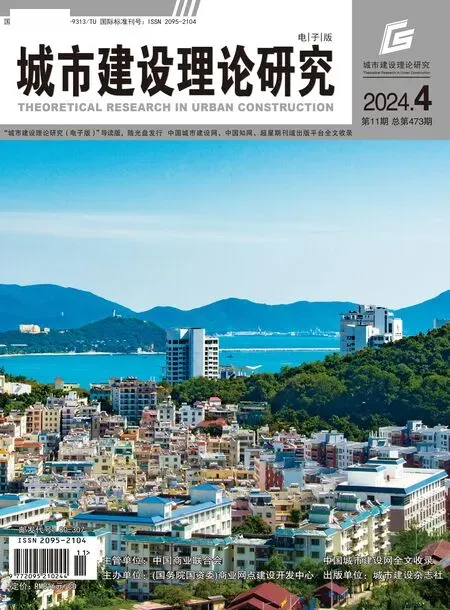UHPC梁極限承載力計算方法研究
王佳瑋 孟 醒
三峽大學 土木與建筑學院 湖北 宜昌 443000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蓬勃發展,城市化水平穩步提高,城市人口越來越密集,高層建筑的數量急速增長,對高強度、高性能混凝土的需求不斷增加[1],超高性能混凝土逐漸被廣泛關注和應用。為繼續推廣鋼筋UHPC在工程領域的深入應用,不同學者提出了多種開裂荷載、裂縫寬度、剛度、承載力的計算方法,還有一些專家編制了超高性混凝土結構的設計規范。然而不同方法對于模型假定和參數取值不同,且關于鋼筋UHPC構件的抗力性能研究較少,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此外,不少研究表明高強鋼筋能充分發揮出UHPC的超高強度、超高韌性以及超高耐久性,同時可以減少鋼筋用量、截面尺寸。為此,本文基于配置HRB600級鋼筋的超高性能混凝土梁進行正截面抗力性能加載試驗,研究了鋼纖維類型、摻量及配筋率對梁正截面極限承載力的影響,并對比分析了試驗結果以及不同極限承載力計算方法的差異性,提出了超高性能混凝土梁極限承載力的計算方法。
1 試驗設計
1.1 原材料及配合比
UHPC-CA的主要原材料包括水泥P·C42.5水泥、P·O52.5、碎石、硅灰、石英砂、鋼纖維、高效聚羧酸減水劑和水,水泥的離子含量、強度和各項性能指標均符合相應的規范要求。碎石選用粒徑為5~10mm;石英砂為30~40目,細度模數為7.3;硅灰采用埃肯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生產的,其比表面積為22000cm2/g,二氧化硅的含量在94%以上;鋼纖維選用平直型、波紋型、端勾型三種類型,直徑為0.2mm,等效長度為13mm,密度為7850kg/m3;高效聚羧酸減水劑減水效率為40%。UHPC-CA配合比設計見表1。

表1 UHPC-CA 配合比 (單位:kg/m3)
1.2 試件設計
試驗梁截面尺寸為100mm×200mm,跨度為1200mm,計算跨度為1050mm,保護層厚度15mm[2]。試驗梁共六根,以受拉縱筋為HRB600級鋼筋的適筋梁4根L1~L4,變量為鋼纖維類型和摻量;少筋梁L5受拉縱筋為HPB300級鋼筋;超筋梁L6受拉縱筋和箍筋間距變小,均采用HRB600級鋼筋;試驗梁具體參數見表2。

表2 試驗梁工況
1.3 加載制度
試驗梁采用團隊自主設計研發的鋼筋混凝土梁反力加載裝置[3]進行加載,如圖1所示,此裝置更加便于觀察和測量裂縫。

圖1 加載裝置
試驗梁彎剪段和純彎段均為350mm,在試驗梁的側面、梁底和梁頂粘貼120-80AA 型混凝土應變片,使用uT700Y優泰采集儀進行應變采集;在試驗梁的鋼墊板和跨中區域沿梁高布置千分表;在跨中梁縱筋對應位置處布置位移計,防止應變片斷裂無法繼續監測變形。 加載制度驗根據 《混凝土結構實驗方法標準》(GB50152-2012)制定,采用分級加載制度,正式加載前,通過預加載檢查各種儀器工作狀態。通過觀察試驗梁受壓區破壞狀態,來判斷是否達到其極限承載力。
2 試驗結果分析
2.1 應變分析
試驗梁在加載過程中,應變沿截面高度是線性分布,說明應變符合平截面假定,如圖2所示。將四根適筋梁彎矩-鋼筋應變進行匯總繪出曲線圖(圖3),在彈性階段,不同試驗梁的彎矩-縱筋應變幾乎重合在一起,表明不同的鋼纖維形狀和摻量在加載初期對梁的剛度影響不大。在梁表面裂縫開展階段,鋼筋的應變迅速增大,在開裂截面處鋼纖維對混凝土有著阻裂作用,從而有效的限制鋼筋應變的增加。由圖可得,在梁承受的彎矩和鋼纖維摻量一定時,鋼筋承受的拉力從大到小依次為:直纖維梁、端勾型纖維梁、波紋型纖維梁。在梁承受的彎矩和鋼纖維形狀一定時,3%直纖維梁鋼筋承受的拉力更大比2%的直纖維梁鋼筋承受的拉力更小,即3%直線纖維混凝土承受的拉力比2%直線纖維混凝土承受的拉力更大。鋼纖維由于摻量和形狀的改變增加了鋼纖維和混凝土的粘結力,在承受荷載時可以提供更多的拉應力。

圖3 適筋梁荷載-鋼筋應變
2.2 承載力分析
試驗梁破壞數據如下表3所示,由適筋梁L1~L4的數據可得,鋼纖維形狀對極限承載力影響不大,但是對破壞撓度有一定影響;提高鋼纖維摻量、配筋率能提高梁的極限承載力,3%鋼纖維摻量梁大約比2%鋼纖維摻量梁承載力提升8.84%;少筋梁L5和超筋梁L6破壞時撓度和極限壓應變均不大。抗拉強度是影響超高性能混凝土梁極限承載力的主要因素,配筋率是次要影響因素;鋼纖維類型及摻量通過影響混凝土的抗拉強度間接影響梁的極限承載力。

表3 試驗破壞數據
3 極限承載力計算方法
采用普通混凝土梁極限承載力計算的方法對于超高性能混凝土梁進行極限承載力計算并不適用,本文參考美國預制UHPC蓋板設計規范[4]、湖南規范 (DBJ43/T325-2017)[5]、瑞士MCS-EPFL規范[6]、法國UHPFRC規范[7]、西安建筑科技大學梁興文計算方法[8]、湖南大學方志計算方法[9]對試驗梁承載力進行計算,極限承載力計算值與試驗值比值如表4所示。

表4 極限承載力計算值與試驗值比值
所有規范都未考慮鋼纖維摻量的影響。美國規范和瑞士規范評判破壞的標準對本文試驗梁不適用,過高的計算了試驗梁受壓區混凝土的承載力,因此,兩個規范的計算值均大于試驗值;湖南省提出的活性粉末混凝土結構技術規程由于忽略了混凝土受拉區荷載的貢獻,計算值明顯小于試驗值;法國規范和梁興文計算方法的計算值略小于試驗值,規范中系數的取值往往是偏向于安全的,故取值偏小,而梁興文計算方法拉應力大約是實測混凝土抗拉強度的60%左右,可見對受拉區混凝土貢獻考慮偏于保守;方志的計算方法與本文的試驗值較為接近;在梁截面高度相同的條件下,鋼纖維長度越長,折減系數k值越大,鋼纖維長度的增加有利于更好的發揮鋼纖維的橋接能力,承擔更大的拉應力。
綜上分析,依據方志的承載力計算公式乘以調整系數來計算超高性能混凝土梁正截面極限承載力較為貼合實際,調整系數取值1.07。
4 結語
(1) 超高性混凝土梁沿截面高度應變符合平截面假定;鋼纖維由于摻量和形狀的改變增加了鋼纖維和混凝土的粘結力,在承受荷載時可以提供更多的拉應力;抗拉強度是影響超高性能混凝土梁極限承載力的主要因素,配筋率是次要影響因素;鋼纖維類型及摻量通過影響混凝土的抗拉強度間接影響梁的極限承載力。
(2) 鋼纖維形狀對超高性能混凝土梁正截面極限承載力影響不大,但是鋼纖維摻量的提高可以提高試驗梁的極限承載力,鋼纖維摻量為3%的試驗梁相比鋼纖維摻量為2%試驗梁正截面極限承載力提高8.84%左右。
(3) 美國預制UHPC蓋板設計規范和瑞士MCS-EPFL規范由于受拉和受壓破壞判斷標準對配置HRB600級鋼筋的超高性能混凝土梁實際破壞狀態不適用導致計算值偏大;我國湖南省提出的活性粉末混凝土結構技術規程由于未考慮受拉區UHPC的影響導致計算值偏小;法國UHPFRC規范、西安建筑科技大學梁興文考慮受拉區混凝土影響過于保守導致計算值略小,湖南大學方志計算值和試驗值較為為吻合,方志公式乘以調整系數的計算方法較為貼合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