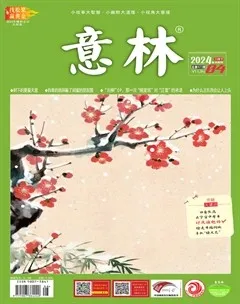網絡拾荒者

我成了B站的“6級大佬”,這應該能算作我在網上經年累月“撿垃圾”的證明。
如果不上傳自己的創作,只是東點點西看看,像逛天橋一樣,順手給優秀視頻投投幣,一個普通用戶每天最多能得到60經驗值,但升到6級需要28800經驗值。
我在網上“拾荒”多年,既不發彈幕,也不參與評論,只給一鍵三連。能升到6級,只因趴在B站的時間夠久。“撿垃圾”也是一件持之以恒的事情。
“網絡拾荒者”是我貼給自己的標簽。有一回,辦公室歡聲笑語:“你是怎么知道這么多亂七八糟的知識的?”我鬼使神差地回了一句:“我只不過用你們喝咖啡的時間在網上撿垃圾罷了。”
下班的路上自己咂摸了幾回這個回答,越來越喜歡。
網絡沖浪的清涼時代已經一去不返。漫布在互聯網海灘上的,是無窮無盡的信息垃圾。各色App如同一艘艘海盜船,劫掠著網民的時間和精力。
但又能怎么辦呢?上網早就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剛上大學的時候,我有一段時間出門不帶手機,想聯系到我,得知道我舍友們的聯系方式才行。現在不可能了,晚幾個小時沒有回復,微信那頭就得炸鍋。
回想起來,注冊B站就是我積極對抗網絡垃圾的開始。我所哼唱的歌曲大多出自B站。有些普通的口水歌,被“B站方文山”們重新填詞、調音,朗朗上口,甚至感人至深。
如“我素聞蜀國天府鄉,且民殷國富兵馬壯”(《此物天下絕響》)。一些經典的場面被UP主們反復二次創作,簡直成了互聯網時代的“詞牌”“曲牌”。比如諸葛亮和王司徒的對決,就被“二創”了成百上千次。一個場景竟有這樣蓬勃的生命力,讓我想到那些“戴著鐐銬跳舞”的格律詩——往往,命題之下的格律,有著近乎無限的創作可能。
圖一樂,就是我在網上“撿垃圾”的動力。興趣廣泛,博采眾佳。
給學生解讀《朝花夕拾》時,講到《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魯迅得知了一種名為“怪哉”的小蟲,是人的怨氣所化,但澆一點酒便會消失不見。他想問問私塾先生是怎么回事,結果惹怒了這位舊學儒生。
我特意提到了這個情節,調侃學生們,年少的魯迅跟你們年紀相仿,也喜歡聽一些無用但是有趣的冷知識。嘖嘖嘖嘖,讀書寫作你們無精打采,論起沒用的玩梗冷知識你們勁頭十足。他們哈哈大笑。
但對一個成年人,尤其是對那些充滿規劃的人來說,在網上“撿垃圾”或許是浪費時間。這些知識的用場頂了天是在辦公室捧哏和參與群口相聲。網上時有這種論調,那些什么都懂一點的人,往往什么都不懂。
那么,在網上看這些亂七八糟的知識,天天“撿垃圾”,有用嗎?
比如,在一些行業人眼中,小說只是調劑生活的消遣。小說也是“無用但有趣的冷知識”。
我由此想到了昆汀的電影。他的電影中充斥著大量目的性不強的廢話。初次觀看,你會想當然地以為,這些對話會為接下來的情節埋下伏筆。當情節急轉直下,你會發現,原來他們剛才真的是在說廢話。
我聽塞繆爾·杰克遜講廢話對白的時候總是興致盎然。這些廢話是生活節奏的一種隱喻。在生活某些無意義的間隙,意義又會從天而降,驅使著你去做出選擇,命運就這樣悄然而至。
“圖一樂”“沒用但有趣的冷知識”,是生活的碘元素,需要持續、微量地攝入。如果缺少,我們也許就會罹患上一種電子無趣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