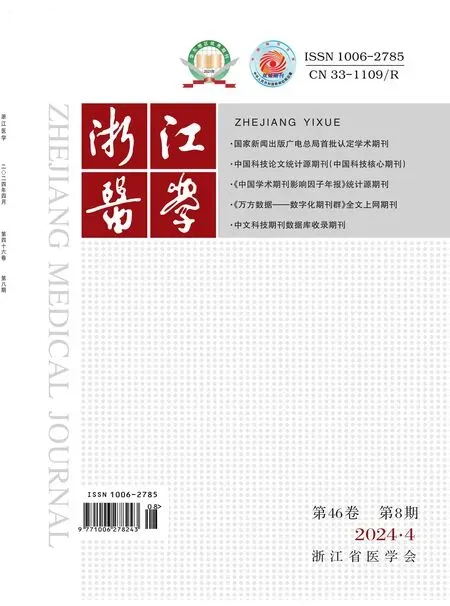乳腺乳頭狀癌的臨床病理及影像學特征分析
葉欣 黃建
乳腺乳頭狀腫瘤是一類含纖維血管軸心乳頭結構的上皮源性腫瘤,是一組異質性病變。乳腺腫瘤分為導管內乳頭狀瘤(intraductal papilloma,IDP)、原位乳頭狀導管癌(papillary ductal carcinoma in situ,pDCIS)、包裹性乳頭狀癌(encapsulated papillary carcinoma,EPC)、實性乳頭狀癌(solid papillary carcinoma,SPC)和浸潤性乳頭狀癌,其中后4 類屬惡性腫瘤[1]。乳腺乳頭狀癌與非特殊類型浸潤癌相比預后較好,多呈惰性生長,但其具有不同惡性潛能,有復發(fā)、轉移風險[2]。乳腺乳頭狀癌臨床上罕見,目前其診斷尤其是各亞型的鑒別是臨床上的難點,在冷凍切片診斷中乳腺乳頭狀癌的確診率明顯低于良性乳頭狀腫瘤,且具有較高的延遲診斷率[3]。所以影像學檢查在乳頭狀癌的鑒別診斷中的地位更加重要。本文通過分析不同亞型乳腺乳頭狀癌患者的臨床病理、超聲、乳腺X 線、增強MRI 檢查等資料,以期為臨床精準診療提供依據(jù),現(xiàn)將結果報道如下。
1 對象和方法
1.1 對象 回顧性分析2015 年1 月至2022 年6 月在浙江大學醫(yī)學院附屬第二醫(yī)院行手術切除治療并經(jīng)病理檢查證實為乳腺乳頭狀癌的患者82 例,均為女性,年齡28~81(57.0±5.6)歲。納入標準:手術病理檢查診斷符合WHO 乳腺腫瘤分類第5 版中對乳腺乳頭狀癌的定義;患者年齡≥18 歲。排除標準:手術病理診斷為乳腺乳頭狀瘤;患有其他惡性腫瘤;有乳腺癌病史。其中pDCIS 組23 例,EPC 組10 例,SPC 組13 例,浸潤性乳頭狀癌組24 例,乳頭狀癌伴其他成分(混合型組)12 例。本研究經(jīng)浙江大學醫(yī)學院附屬第二醫(yī)院醫(y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批準文號:(2023)倫審研第(0928)號]。
1.2 方法
1.2.1 患者臨床病理資料收集 患者臨床病理資料均取自術前穿刺及術后常規(guī)病理檢查報告,兩者不符合以后者為準。均行HE 染色及免疫組化檢查。記錄雌激素受體(estrogen receptor,ER)或孕激素受體(progesterone receptor,PR)、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2,HER-2)、Ki-67增殖指數(shù)檢查結果以及淋巴結轉移情況等。
1.2.2 超聲檢查 采用荷蘭飛利浦公司IU22 型超聲診斷儀,探頭頻率4~13 MHz。囑患者取平臥位,雙手上舉充分暴露乳房和腋窩。由1 名具有10 年以上工作經(jīng)驗的超聲科醫(yī)師檢查。記錄病灶超聲征象,包括形態(tài)、邊緣、縱橫比、腫塊內鈣化情況、血流情況。
1.2.3 乳腺X 線檢查 使用美國GE 公司Senographe 2000D 型全數(shù)字化乳腺鉬鈀X 線機,常規(guī)行雙側乳腺頭尾位和內外側斜位攝影。
1.2.4 乳腺增強MRI 檢查 使用德國西門子公司Trio Tim 3.0 T 超導型MRI 掃描儀,使用8 通道乳腺專用線圈。患者雙側乳房行定位掃描、T1WI、T2WI、增強掃描序列。對比劑采用釓噴酸葡胺注射液。記錄患者乳腺病灶MRI 增強表現(xiàn)、時間強度曲線(time intensity curve,TIC),曲線形態(tài)分為Ⅰ型(持續(xù)上升型)、Ⅱ型(平臺型)、Ⅲ型(洗脫型)。
1.3 統(tǒng)計學處理 采用SPSS 25.0 統(tǒng)計軟件。計量資料以表示;計數(shù)資料以百分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或Fisher 確切概率法。P<0.05 為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各組患者臨床表現(xiàn)及病理檢查結果比較 各組患者臨床表現(xiàn)、HER-2 表達比較,差異均有統(tǒng)計學意義(均P<0.05)。pDCIS 組及SPC 組乳頭溢液或溢血發(fā)生率高于EPC 組、浸潤性乳頭狀癌組、混合型組(χ2=25.333,P=0.013)。各組免疫組化指標比較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均P>0.05)。HER-2 陽性表達均在pDCIS組。見表1。

表1 各組患者臨床表現(xiàn)及病理檢查結果比較[例(%)]
2.2 各組患者術前超聲檢查結果比較 各組患者病灶占位性質、形態(tài)、邊緣、內部回聲比較,差異均有統(tǒng)計學意義(均P<0.05),而縱橫比、大小、與乳頭距離、血流信號方面比較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均P>0.05)。pDCIS 組中12 例(52.17%)患者超聲表現(xiàn)為片狀低回聲區(qū),而在其余4 組中57 例(96.61%)患者表現(xiàn)為腫塊型占位。EPC 組均表現(xiàn)為邊緣清晰腫塊影,其中6 例(60.00%)患者表現(xiàn)為囊實性混合回聲,見表2。典型的EPC 超聲表現(xiàn)見圖1。

圖1 典型EPC 囊實性回聲圖像

表2 各組患者術前超聲檢查結果比較[例(%)]
2.3 各組患者乳腺X 線特征比較 對超聲檢查無法明確的48 例患者加行乳腺X 線檢查。5 例(50.00%)SPC 及4 例(50.00%)pDCIS 患者在乳腺X 線檢查中未被發(fā)現(xiàn)。EPC 組、浸潤性乳頭狀癌組、混合型組乳腺X線下形態(tài)多為邊緣清晰腫塊,5 例(50.00%)pDCIS 及3例(37.50%)SPC 患者腫塊型占位邊緣均模糊。各組病灶乳腺X 線特征中鈣化、腫塊密度比較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3。

表3 各組患者乳腺X 線特征比較[例(%)]
2.4 各組患者增強MRI 特征 對超聲及乳腺X 線檢查結果無法明確的35 例患者加行增強MRI 檢查,均檢出異常。7 例(77.78%)SPC 增強MRI 圖像表現(xiàn)為區(qū)域強化。各組除病灶形態(tài)外,邊緣、動態(tài)增強及TIC 表現(xiàn)方面比較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4。

表4 各組患者增強MRI 特征比較[例(%)]
3 討論
乳腺乳頭狀癌是一種罕見的惡性腫瘤,占女性乳腺癌的1%~2%[4]。近年來,關于乳腺乳頭狀癌臨床病理學及影像學特征的研究越來越多。82 例乳腺乳頭狀癌患者的平均年齡達(57.0±5.6)歲,高于中國女性自然絕經(jīng)年齡,這與既往報道一致。乳腺乳頭狀癌通常表現(xiàn)為異常腫塊、血性溢液或影像學異常。本研究中,47 例(57.32%)查體可見異常腫塊,15 例(18.29%)可見乳頭溢液,其中pDCIS 組及EPC 組患者最為常見(分別是46.15%、30.43%),這進一步證實乳腺乳頭狀癌起源于導管并圍繞纖維血管惡性增殖[5]。
從病理檢查特征來看,乳腺乳頭狀癌多為激素受體陽性、Ki-67<10%、HER-2 陰性,僅3 例(3.66%)患者出現(xiàn)淋巴結轉移,這與既往研究報道的5.10%類似[6],說明乳腺乳頭狀癌惰性生長、侵襲性低。若分期為Tis~T2N0-1M0,根治性外科手術后僅部分需要全身治療[7],術后低復發(fā)轉移風險,預后好,與AI-Shehri 等[8]的報道一致。
超聲檢查是亞洲女性乳腺癌最常用的檢查方法[9]。本研究發(fā)現(xiàn)超聲占位性質中,pDCIS 較其他亞型更多呈片狀低回聲區(qū),符合pDCIS 乳頭狀增生的病理特征[10],并提示該亞型沿導管生長,術前診斷應關注其與導管結構的關系。腫塊內部回聲特征在組間有差異,6 例(60.00%)EPC 呈囊實性腫塊,有研究認為EPC是原位癌至浸潤性癌的過渡形態(tài)[11],超聲圖像中EPC多具有復雜囊性腫塊伴囊壁內實性乳頭狀突起的特征[12-13],且腫塊邊緣模糊提示侵襲性更高[14],因此超聲檢出復雜的囊實性乳腺腫塊應在診斷中考慮EPC,并注意與乳腺髓樣癌、葉狀腫瘤相鑒別[15]。乳腺X 線檢查是乳腺癌篩查手段之一。本研究發(fā)現(xiàn),pDCIS 和SPC 易被漏診(均為50.00%),與既往研究結論符合[16]。EPC 因其膨脹性生長特性,多評為BI-RADS 3級,但未發(fā)現(xiàn)其在鈣化及占位密度上與其他組的差異,故應重視老年女性乳腺X 線邊界清晰的橢圓形病灶[17]。為更好地診斷乳腺乳頭狀癌及揭示其形態(tài)特征,需進行額外影像學檢查,乳腺X 線非首選[18]。
本研究行MRI 檢查患者的病灶均被檢出,MRI 在乳腺乳頭狀癌診斷中更能反映其與導管的關系[19]。形態(tài)學上,MRI 能發(fā)現(xiàn)在乳腺X 線檢查中漏診的乳頭狀癌,如SPC、pDCIS。在增強動力學方面與,乳腺乳頭狀癌的表現(xiàn)與其他浸潤性乳腺癌相似,各組未見差異[20]。MRI 在術前評估乳頭狀癌手術范圍和鑒別侵襲性病灶方面有優(yōu)勢[21]。
綜上所述,乳腺乳頭狀癌作為罕見的乳腺腫瘤,好發(fā)于老年女性,臨床癥狀多是乳房腫塊及乳頭溢液。乳腺X 線檢查對于SPC、pDCIS 檢出率低,超聲結合MRI 檢查對乳腺乳頭狀癌檢出和明確病灶與乳腺導管的關系更有效。各亞型影像學表現(xiàn)部分重疊,橢圓形囊實性腫塊是EPC 特征性影像學表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