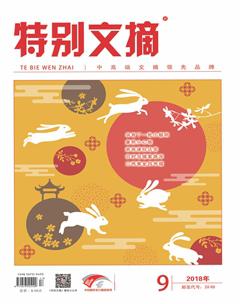雷人雷語
老公讓老婆去做飯,但老婆坐在沙發上看電視,沒有理他。
過了一會兒,老公忍不住又催了一次。老婆指了指柜子里的青花碗,問:“這是你花十幾萬元買的吧?”老公點了點頭。
老婆又問道:“你舍得用它盛飯嗎?”老公趕緊搖頭:“這是藝術品,是用來欣賞的。”老婆接著說:“我是你花一百多萬元娶的,比它值錢吧?你怎么舍得要我來給你做飯呢?”
兒子放學回家,對媽媽說:“今天的足球比賽,我踢進了4個球。”
媽媽朝兒子蹺起了大拇指,夸獎道:“真厲害!”頓了頓,又問,“進了4個球,你為什么還不高興呢?”
兒子撇嘴道:“哎,我們隊沒有贏。結果打成了平局……”
媽媽說:“這是怎么回事?是你們后衛出了問題嗎?”
兒子吞吞吐吐地說:“也不是……比分是2∶2。”
這天,老公很晚才到家,沒等妻子發問,他搶先解釋道:“單位加班,正好手機又沒電了。”
妻子笑了:“你剛才說話時,三次拿起水杯喝水,暴露了你內心十分緊張。你在說謊!”
老公故作鎮定:“就憑我三次喝水,你就判定我在說謊?”
妻子白了他一眼,說:“水杯里根本沒有水,你在喝什么?”
兒子剛才說:“爸爸我最喜歡周四了。”我問他為什么,他說:“周一、周五是英語,周二是樂高,周三是輪滑,周六是游泳,周日是足球,只有周四可以從放學玩到睡覺。”
我心疼地抱住他:“兒子啊,爸爸也沒辦法。如果你不從幼兒園就開始上各種興趣班的話,爸爸哪有時間在家里安靜地待著呀。”
女兒自豪地問我:“媽媽,請問有一個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兒,是什么感覺呀?”
我有些迷惑,想了半天,對女兒說:“這個問題我還真回答不上來,你去問你姥姥吧,她是最有資格回答這個問題的人。”
小李最近時不時聽見老人被騙的傳聞,他想到了自己的母親,因為母親最容易輕信別人。于是,小李趕緊回家告訴母親要小心騙子,說完他還不放心,對母親說:“要不然,您把存折交給我吧,省得哪天您不小心被人騙去。”
母親警惕地看著兒子,說:“交給你?那和被人騙去有什么區別?”
表弟的女兒一直不同意表弟夫婦再生二胎。
有一天,侄女對表弟說,“爸,你不是要生二胎嗎?那趕緊生吧。生三胎我都沒意見了。”
表弟聽了侄女的話后,很奇怪,問她:“去年跟你說,你堅決不同意,怎么過個年你就想通了?說真的,你不后悔嗎?”
侄女點點頭,說:“我早就想通了,決不后悔。”
“你咋想通的?”
“我覺得靠我一個人實在養不起你!這才幾個月呀,我幾千塊錢的壓歲錢,全被你騙去花光了……”
(摘自“糗事百科”“捧腹網”等 圖/陳明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