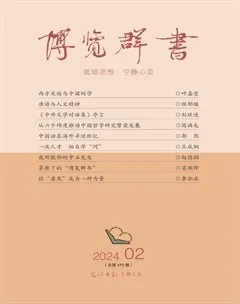《論語》對語文教育的啟示
張慶利
《論語》記載了孔子許多有關教與學的論述,體現了他豐富的教育思想。而其中記錄的孔子教育過程中的片段,更是彌足珍貴,深入挖掘,庶可見其多方面的思想內涵和文化影響。《論語》中有如下兩則教學片段,今天讀來,仍覺意義深遠: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論語·學而》)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后素。”曰:“禮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論語·八佾》)
這兩則記言都是孔子與弟子的對話,弟子提問,孔子作答,然后弟子談認識,孔子進行評價,也可以看作是兩個完整的教學互動環節的記錄。雖然孔子的時代,還沒有“語文”的概念,但在這兩段對《詩》的征引、疑問、說解與聯想中,從其中涉及的內容與原則、方法與步驟、風格與特征等問題中,仍然可以感受到其對當今語文教育具有重要啟示。
啟示之一,思想教育是語文教育的應有之義。在孔子的教育中,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并重,而德行為先。這兩則材料中,子貢問及的正是道德的問題。貧窮的時候不諂媚別人,富貴的時候也不驕傲自大,這是孔子經常提到的一個道德層次,他曾經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是要求以“仁”的方式獲得富貴,去掉貧賤。他還說過“巧言令色,鮮矣仁”(《學而》),認為花言巧語、諂媚作態,是不仁的表現。但這是基本要求,所謂“富而無驕易”(《憲問》)。孔子對學生有更高的要求,所以他引進以“禮”約束的更高境界,子貢則聯想到了《詩》中的話語。子夏問及《詩》的理解,又從孔子的解釋聯想到“禮”的意義。仁與禮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主內,禮主外,禮的教育是德行的重要組成部分。
《論語·雍也》中說:“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這是一段非常有名的話,人們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多方面的闡發,但從根本的意義上說,“文質彬彬”談的是君子風范。“質”強調內在的品格,主要是指其所具有的仁、義、智、信、勇等;“文”強調外在的修養,主要是指其禮儀等方面。《論語》中的“君子”具有多種品格特征:好學精進、樂觀向上、過而能改、謙虛謹慎、言行合一、團結協作、胸襟開闊、任重道遠、正道直行、禮樂情懷、憂患意識等,都是重要之處。
“文質彬彬”的君子風范,首先,要有向道精神。“道”是信念,是理想。孔子說過:“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衛靈公》)可見對“道”的規劃和憂慮是“君子”之人的突出品質。孔子曾憧憬地表白:“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可見他一生都充滿著向道的精神和求道的熱情;他的弟子子夏也說過:“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子張》)可見“道”是孔門一直的追求。“向道”就要有胸懷天下、安定天下的責任感,有開闊坦蕩的胸襟,有任重道遠的擔當意識,還要培養正直品行,正如曾子所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泰伯》)。其次,要有優良品質。孔子重視學習素養,他開創了我國古代教育的新局面,把引導弟子學習作為第一要務,《論語》開篇就講:“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他把“好學”作為評價學生的重要標準和作為君子的首要條件,聲稱“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學而》)。《論語》具有豐富的學習思想,對學習目的、學習態度、學習方法等都有具體的論述,至今仍有重要意義。孔子重視求實品格,他認為仁人志士必須實事求是,因而君子之人要言行統一,要先行后言,不能言過其行。他說:“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里仁》)古人不多說話,就是因為怕做不到。又說:“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里仁》)要言語謹慎,行為敏捷。人無完人,孰能無過?孔子理解別人的過錯,并認為君子之人善于改過遷善,“過則勿憚改”是君子的重要條件。認識到錯誤,并且積極地去改正錯誤,這樣才能不斷吸取教訓,從而成就君子的品格,正如子貢所說:“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張》)。為此,他特別贊賞顏回“不貳過”的精神!孔子崇尚謙遜作風,孔子認為君子從不因為別人不理解自己而不高興:“人不知而不慍”(《學而》),而總是擔心自己能力不及人之所望,經常從自身方面思考增強其能力:“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衛靈公》)。他們從不驕傲自滿:“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子路》),所以能夠團結協作而不結黨營私:“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衛靈公》)另外,要有禮樂修養。孔子認為“禮”是立身、立業、立命的重要根據,因而說:“不學禮,無以立”(《季氏》)。“樂”為“德之光華”,發于內心,感人至深,具有“移風易俗”“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的作用。因而孔子非常喜歡音樂,在齊國聽到舜時的樂章《韶》,竟然陶醉得“三月不知肉味”,而且深深感慨:“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述而》)他非常重視樂教,認為修身從學《詩》開始,以禮立身,通過樂來成就中正平和之性:“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泰伯》)。禮與樂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正如《禮記·文王世子》中所說:“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于中,發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這是“君子”之人的重要條件,也是家國之治的理想境界。
文化的承載與弘揚離不開語言文字和文學藝術。語文學科是個綜合學科,承載更加厚重,責任更加重大。孔子的時代,還沒有“語文”的概念,但在經典閱讀的教育中,在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的強調中,其培養目標明確地指向了君子人格。
啟示之二,經典閱讀是語文教育的重要基礎。在孔子的時代,《詩》具有特殊的功用。不僅可以“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可以領悟“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的道理,而且可以“興觀群怨”具有多種審美意義,可以“賦詩言志”進行溝通與交流,所以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禮體現著規范,也是一種修養,所以孔子說:“不學《禮》,無以立。”(《季氏》)可言、可立,便具備了“君子”的基本條件。從教育的角度,《詩》則是一部可以認知名物、可以提升道德、可以學會表達的經典教科書。不只是《詩》,儒家教育中的《書》《禮》《樂》《易》等也都是經典之作。
在一個民族的發展中,總有那樣一些著作,她以不多的語言,給人無盡的啟迪,不斷被闡釋,讓人們常讀常新;她以不變的姿態,卻涵容著歷史的變遷,不斷被證明,成為準則,成為典范,“秩秩德音,洋洋盈耳”(《史通·敘事》);她以不爭的經驗,承載著民族文化的記憶,不斷被喚醒,又不斷被印證。這就是經典,這就是經典的魅力。它們的存在照亮了歷史的天空,在人類的精神長河中如點點白帆,通往過去,也駛向未來。
這些經典的主角或創造者都是一個一個的文化大師,他們用不尋常的人生創造了不朽的經典。《論語》中的孔子,以藹然長者的形象,懷著博大的胸襟,“有教無類”地播種智慧,“誨而不倦”地布施仁愛,帶領弟子們由北到南貫通天下、“知其不可而為之”地傳送德政;描繪《道德經》的老子,站在“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大道之巔,在“惚兮恍兮”的世界中探索著不可名說之“道”,闡揚著“自然無為”的帝王之術,構造出“小國寡民”的理想世界;“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孟子,高揚著“大丈夫”的氣概,馳騁天下,睥睨王者,意氣風發,雄辯滔滔,堅持“民為貴,君為輕”,始終為民眾爭取著一席之地,全身充滿著“至大至剛”的凜然正氣。“衣弊履穿”“釣于濮水”的莊子,他以精神世界的豐滿充盈,對抗著生活的貧困,拋開了名利的物累,超越了生死的限界而奔向“逍遙游”的輝光!寫作《史記》的司馬遷,靠著巨大的力量,以一人之力,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完成了貫通歷史的構建;帶著理性的情感,撥開傳說的迷霧,從蒙昧混沌的洪荒梳理出民族發展的脈絡;憑著高超的技巧,描繪千百年中遽來遽去的人物,把再現的歷史敘述得入情入理。就這樣,經典展露了它最本初的端倪,帶著世人穿梭在歷史的長廊。千年稍縱即逝,而經典巋然不動。
在《論經典》一書中,作者詹福瑞曾論到經典的傳世性、普適性、權威性、耐讀性、累積性,談到“教育之于經典的傳播與建構”,認為“經典傳播的主要形態之一,是學校的教育”(詹福瑞《論經典》,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這些經典,揭示了人間的至真情性,帶領我們從人類發展的成敗得失中尋求歷史智慧。以《周易》《詩經》《尚書》《三禮》《春秋》《論語》《老子》《孟子》《莊子》等為代表的中華元典,不僅具有政治、經濟、社會、軍事、歷史、文學、藝術等多方面的宏觀的文化價值,而且,就個人生命來說,它們探討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等許多方面的問題,對每一種人生都會產生十分重要的影響。韓愈自幼刻苦為學”,從“佶屈聱牙”的《尚書》、“正而葩”的《詩》、“奇而法”的《易》、“浮夸”的《左傳》、“謹嚴”的《春秋》,到《莊子》之論、屈原之辭、《史記》之錄、揚雄和司馬相如之賦,無不涉獵,而且“沉浸醲郁,含英咀華”,這才有了“閎其中而肆其外”(《進學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的輝煌成就。
對于文學經典的選編,早已有了歷史的經驗。南朝蕭統編的《文選》,便是成功的一例。蕭統看到了文學的發展是“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因而希望通過“略其蕪穢,集其清英”的方式,編選一部“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的《文選》,對前代文學進行總結,同時作為時人學習的典范。此書一出,盛極一時。唐代便有了“文選學”,出現了像曹憲、李善等選學家,以及《文選》李善注、五臣注等經典注釋本,《文選》幾乎成為科舉士子的必讀書,北宋甚至有了“《文選》爛,秀才半”的說法。而《文選》既重文采、又重情思的選錄標準,詩文并重、匯聚各體的選錄原則,以類劃分、時代相次的編纂體例等等,創體開新,蔚為大觀,也為后代“國文”“語文”類教材的編纂開了先例。清初康熙年間吳楚材、吳調侯叔侄二人編選的《古文觀止》,上起春秋,下訖明末,選錄文章220篇。編者認為所選文章均為古文中的精華,因以“觀止”稱之。這個選本,當時即獲贊譽,吳興祚作《序》稱其選“簡而該”,其評“精切而確當”,能夠“析義理于精微之蘊,辨字句于毫發之間”。這絕不僅僅是長輩對“從子”“從孫”的偏袒過譽,而是揭示了它足以“正蒙養而裨后學”的價值。雖然這只是一個文章選本,但由于其選文的精粹、注釋的精當、評點的精要,使其本身就成為一部經典之作,對文章的學習與寫作至今仍有重要影響。
當然,經典的價值不僅僅在于實用,更重要的“而在文化”,所以朱自清稱之為“經典的大路”“經典的海”,號召“親近經典”(《經典常談·序》)。
啟示之三,啟發聯想是語文教育的專業特征。孔子重視啟發式教學,他曾經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述而》)朱熹注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憤,是指經過了努力、經過了思考、卻沒有完全透徹地理解的思維情形;悱,是指雖心有所悟、意有所會、卻無法清晰地表達出來的思維情形。這時候,師者一言點化,便如當頭棒喝,又如醍醐灌頂,使之豁然開朗,粲然深思。由此可見,啟發不是簡單的提示,而是思想的引領。啟發的目的是引起聯想,使之達到貫通而徹悟。“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無疑是道德修養的一個層次,但卻不是最高的層次,所以孔子引導子貢追求“貧而樂,富而好禮”的更高層次,而子貢則由此聯想到《詩》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詩句。這一段話,有的《論語》本子作“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意思更加明了。有了朋友間的切磋琢磨、相互砥礪,所以才能夠雖貧窮而一心向道,雖富貴而深明禮敬。“繪事后素”是講先有純白的素娟,才能繪出最美的圖畫,這顯然不是對子夏問《詩》的正面回答,但子夏卻由“繪事”后于“素”,聯想到了“禮”的問題,內含著有了仁的底色再加上禮的修養就達成了君子人格之意。
在《論語》的記言中,孔子經常采用譬喻的方式,引發聽者的聯想。比如:“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為政》)北斗星為眾星辰環繞與簇擁,以此為比,以德治政的顯著效果和重要意義昭然若揭。再如:“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雍也》)“輗”與“軏”是套牛馬拉車的關鍵,沒有輗、軏就無法套住牛馬,也就無從拉車;誠信于人來說正是這樣的關鍵,不講誠信,人便無法立身。再如:“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雍也》)“水”與“山”雖然不是對“知(智)”與“仁”的界定,但卻可以讓聽者在對水之靈動和山之厚重的聯想中,體悟到“知(智)”與“仁”的品格。《論語·雍也》中還曾記載,子貢曾向孔子問道:如果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濟眾”,是否可以稱為仁人?孔子回答說:不僅可以稱為仁人,甚至都可以稱為圣人了!他接著說:“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能近取譬”講的是能夠從身邊做起、從最基本的做起,就是行仁之方、晉圣之途,但如果把“能近取譬”用于語言表達中,也是讓人聯想、引人思考的一種很好的方式吧!因此,在教育過程中,孔子十分重視啟發學生聯想和想象。在《論語·先進》記載的那篇有名的《侍坐》中,孔子讓弟子各言其志,他先以不要“以吾一日長乎爾”而不言打消弟子們的心理負擔,又提出弟子平時總說的“不吾知”的話題,這種啟發既有針對性,又消除了弟子的顧慮,所以弟子們才能暢想未來,高談其志。
聯想與想象是心理活動方式,是文學藝術創作的重要運思方式。沒有聯想就無法將已有知識與經驗連點成線、連線成面,沒有想象就會使其創作缺少創造、沒有靈魂,通過聯想與想象,“籠天地于形內,挫萬物于筆端”(晉·陸機《文賦》)。
當然,聯想需要積累。可以說,積累是聯想的寶庫,閱讀、經驗和思想是積累的途徑,而背誦則是積累的重要方式。前引兩則材料中,從孔子“始可與言《詩》已矣”的話語可見,此時子貢、子夏二人尚未開始學習《詩》,但二人卻對《詩》非常熟悉,不僅記誦在心,而且可以隨時運用:子貢由孔子道德的教誨聯想到了《詩》句,子夏由《詩》句的認識聯想到了禮儀。記憶的積累,豐富了他們聯想的資源。我國古代的教育十分強調背誦,無論哪一個時期,背誦都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內容,它像一條紅線貫穿著中國古代語文教育的始終。古代的一些識字課本,像《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幾乎都采用整齊的韻語,甚至使用對偶,或者二者并用的形式,都是為了朗朗上口,方便背誦。朱熹指出:
學者觀書,先須讀行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復,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則非為己之學也。
瑞典漢學家高本漢談到中國古代教育時說:
國學生在低年級里,必須背誦幾種大部的經典,并熟記歷代名家所作的幾百篇的文章和幾百首詩歌。這種學習的課程,采用了2000多年,已經養成大家于古文書有特別的熟悉,結果,對古代的歷史和文學,又發生了一種崇視敬愛的心,這實在是中國人的特色,這種聚焦成功的大資產,以供中國著作家任意地使用,在文辭的修飾上,自然能得到有效的效果。
李白“5歲誦六甲,10歲觀百家”;岑參5五歲開始背書,9歲便能寫文章;柳宗元4歲時已經熟讀了十幾篇古代辭賦,13歲時已能寫出相當不錯的文章;李商隱5歲開始背誦經書,7歲學習寫作;司馬光,五六歲就能熟練背誦《論語》《孟子》,七歲熟讀《左傳》;蘇軾十幾歲時,就能熟讀背誦《莊子》《史記》《漢書》等。毫無疑問,背誦可以促進聯想,聯想是想象的基礎,想象是聯想的升華。中國古代許多文學家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也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
《論語》蘊涵著豐富的語文教育思想,為中國古代的語文教育提供了典范,值得深入總結與有益傳承。其實,又何止《論語》,每一部經典,都是一方寶藏,值得我們“永無止境的”“無限的”閱讀、詮釋與借鑒。
(作者系文學博士,珠海科技學院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