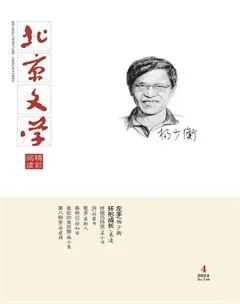終曲與即景(組詩)
谷禾
終曲
你有沒有從村子中央的水井里
看到過漫天燃燒的星光?
日晷轉過正午,從深處又浮現出另一張陌生的臉
……世界呵,你藍色天空的牧場
轉動石頭的井臺,就收攏了永恒交替的白晝與夜晚
蛛絲馬跡
是否蛛網張開的地方
必有馬跡顯形?
在柴堆下,在灶臺邊,在荒蕪的墻角
它們守拙,出奇,
有一窩光的執著,也有倦鳥的嘶鳴
但從沒有一根蛛絲
從蒼穹垂落,搭起明亮的梯子
通向救贖的天國
如同灶馬非馬,灶臺上也不聞馬蹄聲咽
一生作惡的犍陀多,死后墮入地獄
我佛慈悲,垂下一根蛛絲
他爬上去,回頭見眾人尾隨,用力猛踩……
蛛絲斷裂。……他摔下去
很快化成了灶馬饕餮的美餐和塵泥
之后,又一根蛛絲扯在那兒
若隱若現地
等待眾生領悟,伸手抓緊了
遁形的灶馬,正在虛無中磨著它的利齒尖牙
沙漠記
一滴水渴死在沙漠里。
也可以反過來——
更大的沙漠,渴死于最小的一滴水。
從數千里外,你看見它們
迎面相撞,發出咚的轟響
但沒人看得清,哪一個先倒了下去
更多的水撲過來——
以雨的形式,融雪的形式,河流的形式
消失在一粒沙子里
據說塔克拉瑪干沙漠地下
蘊藏著超過北美五大湖十倍的水
如果全部堆積在地面
地球上所有沙漠,都將變成蔚藍的大海
人類還不曾放肆,漫長的時間里
他們一直沒有想好,如何在天空中安置海洋
如同萬有引力和相對論的發現者
最后也把引力之源歸于了最高的神靈
人類也有水的屬性
隱忍,負重,一滴滴聚攏、匯集
被一粒沙子窒息了呼吸
行走在茫茫沙海中
我們領受著人的荒蕪
即景
一群人蜂擁橫穿過街口:
條紋斑馬線。紅綠燈。交通協管。
公交巴士。共享單車。電摩。
閃亮的鋼鐵長龍。招搖的紅色信號旗。
急著上班的人們,小黃帽少年,
風卷起的落葉,看不見的塵埃,
更多人加快腳步,奮勇奔向對岸,
那兩個手牽手的老人,漸漸落在了最后。
他們無所適從,左顧右盼著,
擱淺在了馬路中央——
那一瞬間,時間也停了下來,
茫茫荒原上,兩個老人,互相依靠著,
那么無助、孤單,仿佛涸轍之鮒,
定格了最后的世界圖景。
有一天,我們死去……
會有人悲傷,更多人繼續載歌載舞,
有人小心收拾好我們,交給火焰和細菌。
我們睡過的被,穿過的衣,因為留下
死者太多的氣味和印漬,一同被扔進爐膛。
我們讀過的書被收起來,字里行間
的筆跡,漸漸模糊成了遙遠的舊時光,
審判仍在到來,從起點到終點,不放過
你走的每一步——除非你是行尸走肉。
容留過我們的房子,試圖回想起什么——
它已重新修繕,家具全部更換,
成為新主的愛巢——他們想不到,
這所房子已和我們交融,墻壁里
有我們的呼吸,地板下有遠去的腳步回聲。
有人在我們身上種樹、祭祀、挖掘,
有人從遠方趕來,反復打擾和詰問,
石頭泥土里長出青草野花。你的愛與恨,
生與死的隱秘,一切都像未完成的詩
——時間終有一天會完成它。
在我們之后,人們讀到它,為觸摸到了
真理與善的微光,而深深地鞠躬。
雨,八月
雨砸著窗玻璃,碎成
珠玉,悲慟地滑落,
如一個疲憊的人,漸漸耗盡力氣。
這是云集了全世界的怨怒嗎?
帶著任性、悲欣、不甘、掙扎、沉淪,
落向屋子里凝視的眼睛。
……從前的舊時光里,更多的雨
也是這樣子,落向一個人夢里夢外。
今夜,你一人獨坐于燭光下,
看窗玻璃上波浪洶涌,
遠去的人形,在海水里游向歲月盡頭。
在兩場雨之間,是老者在等著少年;
在兩滴雨之間,一道閃電把窗簾掀開。
……這雨哦,繼續落向泥土的黑暗,
你坐在雨外,聽雨打山河,無始,無終。
湯加來信①
以巖漿的形式,看不見的
焰火的形式,濃煙貫日的形式
以海嘯的形式,潮汐的形式
無盡藏灰燼的形式——
灼燙的,余溫的,冰冷的,
海水浸泡的,噴薄的,潰散的,
無跡的……哦,不是它
在戰栗,是時空交疊,不同
星系在戰栗,海與陸,你腳下的
蔚藍星球在戰栗,跌宕的
層層波紋,恍如蒙太奇的菊蕊開花
開花進程中的漫漫白晝和長夜
而后,是杳無音訊,一滴水跌落水
安樂的死,是菊蕊開花的慢放——
在宇宙爆裂中,在一間蒼茫的屋子里
注:①北京時間2022年11月11日18時48分在湯加群島地區發生7.4級地震。
關于戰爭
活過天命,戰爭之于我
仍是源自個體的想象。
我瞻仰過重見天日的古戰場,
無非是殺戮,車馬,枯骨,皇天后土,
銹蝕的劍戟,被石頭磨礪,
再一次現出灼灼鋒芒。而熱血的河流
已尋不見蹤影,唯殺伐之聲
從時間深處洶涌而來,
家國情懷和快意恩仇,都近于
冊頁里的童話。被攝像機
和電影膠片,反復演繹。
我們置身于時間之外,
如隔岸觀火,替古人一聲喟嘆。
而不同于冷兵器的流血五步,
現代戰爭更接近瘋狂的絞肉機
在隆隆炮聲里,男兒女兒
踏著硝煙向前沖,一眨眼
化成紛飛的骨肉,血光閃亮,
戰爭的牙口張翕之間,更多的
尸體堆向星空,鮮血滲入泥土,
無邊的苦,無盡的淚,無力
搖撼銀幕一角,生出些微晃動。
人類進入算法時代,地毯式
轟炸,衛星導航,空天打擊,
遠程鎖定,精準斬首,
無人機的三體蝗蟲遮天蔽日,
核按鈕成為拇指的延長,
假正義之名,戰爭繼續
在地球上每一個角落瘋狂演繹。
那些獨裁者、瘋子、戰爭販子,
借此涂炭生靈,把自己
送上神壇或絞索。當硝煙散盡,
只留下廢墟,生出斷壁殘垣,
只留下母親懷抱一盒輕飄的骨灰,
出門找尋安魂的土地。
是的,沒有一首詩能阻擋坦克,
也沒有一滴淚能縛住作惡的臟手,
一瓣瓣野花,在新鮮的
死亡氣息中,開得更加消魂蝕骨。
球形糖果
我幾乎淡忘了童年
所有的事兒
比如你辛苦操勞,埋頭在油燈下縫補
揪緊我耳朵,敲著腦殼責罵。
又如父親趕在天黑前,從田里捉來一串螞蚱
投入柴灶后,滿屋升起撲鼻異香。
因了什么,你把父親
從屋子里推搡出來
插上門閂,站上板凳,把腦袋伸進從房梁上
垂下的繩套。我從門縫里
看著你掙扎,大哭著向父親喊“救命”
父親奮力踹開了屋門……
我安靜地聽著,仿佛在別人的故事里旅行。
但是,你把壞脾氣
傳給了我。屬于我的
灰色童年,也帶給了你的孫女和孫子。
那時我迷戀鄰居家的木殼收音機:
傍晚6點鐘。岳飛。穆桂英。
我沉浸在劉蘭芳繪聲繪色的演播里
支棱起另一只耳朵,等待著忽然炸響的喚歸聲
就像入暑后,燒完柴灶
扎入涼爽的河水,想象著一條永不上岸的藍鯨。
如果童年有快樂(那是一定的),快樂就是
我放學后奔回家,從廚屋里翻找見
半個玉米面窩頭。是洗凈鍋碗
飛跑到小學校門口,上課鈴聲還沒響起
快樂還是給生產隊撿拾麥穗交上后
獎勵給每個孩子的,那顆五顏六色的球形糖果。
哎呀,它的甜超過了,來自你的母愛
糖果在我嘴里,像地球
在宇宙中旋轉。它燃燒,擴散,照亮
向上和向下的道路
漸漸化為烏有,全部落入喉嚨的黑洞。
我伸出舌尖,在推開家門之前
又一次舔了舔
皺巴巴的糖紙。它散盡的甜
給我一個孤單的童年,銘記那甜的球形。
責任編輯 張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