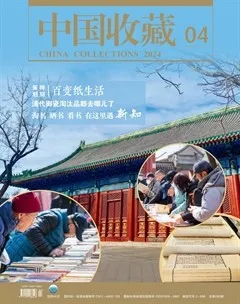“定遠齋”收藏緣何受市場追捧
張侃侃
提起“ 定遠齋”,收藏界會立刻聯(lián)想起一個響當當?shù)拿帧獜垖W良,他是民國時期收藏界久負盛名的“四公子”之一,被譽為“公子收藏家”。其雅好金石書畫藝術品收藏,而且善于品鑒,尤其是在古代書畫作品鑒定方面頗具眼力。
近3 0年來,不少“定遠齋”舊藏書畫精品現(xiàn)身市場,引發(fā)各路藏家追逐。“嗜書畫如飲食”的張學良藏品跨越宋元明清及近代,大多出自名門,陣容整齊且自成體系。因此,每有張學良舊藏書畫釋出,總能成為一時熱話并創(chuàng)下佳績。

青年張學良
轟動業(yè)界的“世紀之拍”
19 94年4月10日下午3時,在臺北新光美術館二樓,來自中國香港、臺灣以及美國、日本、東南亞等地的收藏家、古董商匯聚一堂,因為蘇富比即將在此舉行“定遠齋中國書畫珍藏”拍賣會。他們?yōu)榇艘呀?jīng)翹首等待了兩個多月的時間,不僅因為這是蘇富比進入亞洲市場后首次為一位私人藏家舉行專場拍賣會,更因為這位“定遠齋”主人正是鼎鼎大名的張學良先生。
拍賣當天,座無虛席,海內(nèi)外藏家爭相競標,盛況空前。全場拍品共有古代及近現(xiàn)代書畫作品207件(套),立軸、手卷、冊頁、成扇和扇面等無所不有。其中古代書畫作品共16 0余件,逾總數(shù)6 0 %。這些書畫精品多出自明代“吳門畫派”及其他明清書畫家、文人學者、收藏家等,當中不乏師生、父子、祖孫等成系列的作品,形成了極為鮮明的收藏特色。
此次上拍的古代書畫作品中,帶有“武英殿寶”或“乾隆御覽之寶”等內(nèi)廷印章的作品有九件。據(jù)蘇富比在《“定遠齋”中國書畫珍藏特輯》圖錄中的介紹,此次除明清作品外,最為矚目的是有8 0 0多年歷史、出自宋朝御用畫家謝元的一幅設色絹本手卷《桃花》,其兩端有“乾隆內(nèi)府舊藏”印記,證明該手卷一直由內(nèi)宮庋藏。其余八件則均為帶有“乾隆御覽之寶”印章的折扇。
最終,整場拍賣的總成交額高達1. 32 89億新臺幣,謝元《桃花》以超出估價三倍的價格——1 6 5 5萬新臺幣落槌,領銜全場。此次拍賣中誕生了當時華人藝術品拍賣的諸多紀錄,例如所有拍品盡數(shù)拍出,實現(xiàn)了1 0 0 %成交;成交價超過10 0萬臺幣的拍品達29件,占1 4 % ;成交價超過估價的約占6 0 %,超過的比例之高為歷次拍賣會所罕見。如明代王寵一件行書估價5 0萬至7 0萬新臺幣,成交價3 7 9萬新臺幣;宋代謝元《桃花》估價3 0 0萬至5 0 0萬新臺幣,成交價達16 5 5萬新臺幣;趙之謙水墨花卉估價1 2萬至1 5萬新臺幣,成交價14 8萬新臺幣,超出十余倍。
張大千的1 8 幅作品掀起了這場拍賣的高潮,當中11幅拍品成交價超過10 0萬新臺幣。《湖山清舟》估價12 0萬至150萬新臺幣,成交價達1 0 5 0萬新臺幣;《水竹幽居》和《秋聲圖》也分別以520萬、390萬新臺幣分列第二、第三名。
此次專場中的偽贗作品占全部拍品的比例極小,可以看出張學良書畫收藏的品位和鑒賞功力。這些藏品多是張學良早年購進,在中國收藏史上極為罕見。這場“定遠齋藏中國書畫”專拍也成了轟動業(yè)界的“世紀之拍”,至今猶為收藏家和拍賣業(yè)人士所津津樂道。

宋 謝元《桃花》(局部)蘇富比1994年臺北“定遠齋”專場拍品

明 沈周《春風送寒》扇面蘇富比1994年臺北“定遠齋”專場拍品
內(nèi)地屢有舊藏精品浮出
在蘇富比推出“定遠齋”專場拍賣后的2 0 年間,中國內(nèi)地拍場也曾有一些張學良舊藏書畫作品浮出水面,為中國古代書畫市場增添了不少看點。
例如2 0 1 1年,在張學良誕辰110周年之際,北京匡時拍賣于秋拍中推出了“定遠遺珍——張學良藏古代書畫專場”,在臺北蘇富比專拍的基礎上再度搜羅力作,對張學良“定遠齋收藏”查漏補缺。此次專場拍賣匯集了王紱、王原祁、王榖祥、宋懋晉、王穉登、錢榖、張靈等明清書畫家佳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錢榖的《鐘馗移家圖》。錢榖畫作傳世不多而人物畫尤少,此作品是以宋代龔開的《鐘馗移家圖》(今藏于美國弗利爾美術館)為原稿所繪。作品經(jīng)周天球題引首,黃姬水、張鳳翼、王穉登、王世懋等題跋,王世貞、汪士元遞藏,后入張學良之手,珍貴難得。此作當時以逾2 0 0萬元成交,之后又于2 019 年在西泠拍賣拍出483萬元。
2 016 年,張學良舊藏王翚《江山臥游圖》巨卷現(xiàn)身于保利華誼上海首屆藝術品拍賣會。畫中呈現(xiàn)的雖然是山水,但所繪人物眾多,從頭至尾共計65人,在山水手卷之中甚為罕見。作品上還帶有諸多鑒藏印,其中,“張學良”“毅盦”“ 霖之子”“ 臨溟張氏珍藏”均為張學良的印鑒。以時間先后為序,本卷約為王掞、景其浚、潘順之、金傳聲、張度、沈維裕、沈樹鏞、楊壽樞、張學良先后遞藏,流傳有緒。卷后還留有張大千耄耋之年的題跋,記述其三見此卷的經(jīng)過。此作最終以4 2 0 0萬元成交。
其實,這些只是張學良“定遠齋”珍藏的冰山一角,其藏品品質(zhì)高且數(shù)量可觀,又寄托著張學良本人的審美趣味,見證著一段跨越半個多世紀的不凡收藏歷程。
耳濡目染煉就一雙慧眼
張學良對金石書畫的興致,源自青少年時期金梁、白永貞等幾位老師的影響。這幾位老師學養(yǎng)豐厚,在金石書畫方面造詣頗深。受老師們耳濡目染的熏陶,張學良不僅臨池做古篆籀,而且對金石書畫漸漸地著了迷。年輕時的張學良曾經(jīng)過著揮金如土的日子,對于喜歡的藏品,他不惜花費重金購買。
張學良的古代書畫收藏始于2 0世紀2 0年代初期。他在主持軍政之余,經(jīng)常到京津地區(qū)的書畫店和古董商鋪“ 尋寶”。1 9 2 4 年秋,他在天津一家舊書店的故紙堆中發(fā)現(xiàn)一軸古畫。因年代久遠,畫面上一片污垢,但依稀可見所畫的是一松一楓,樹下有一老者,手提竹籃。其運筆嫻熟、下筆洗練、筆墨精湛,雖然畫上并未署名,但張學良根據(jù)以往經(jīng)驗,判斷其應是名家之作。店主當時可能并不認識張學良,但看他對此畫觀賞細致、愛不釋手,且有購買意愿,于是開出高價。張學良沒有跟店主討價還價,他二話不說,毅然重金買下。后來,他邀請?zhí)旖蛞晃恢臅嬭b賞家?guī)兔﹁b定,發(fā)現(xiàn)此畫作竟然是南宋著名畫家李唐的真跡,堪稱國寶。
從此之后,張學良的書畫收藏興趣一發(fā)而不可收拾。天津《益世報》主筆王益知在《張學良外紀》中記述道:“張學良鑒別金石書畫真?zhèn)危哿^佳。用贗品施其欺騙故技,是蒙混不過的。1927年張學良決定撤兵關外的時候,他在保定駐扎。有一天他和隨從們到古董店瀏覽,店主看到這班貴客來臨,將密室里深藏的寶貨,羅列面前。黑暗中,五光十色,耳目為眩。張學良買得一座鏤金塔,高有尺余,滿刻梵文,論價不過7 0萬。若在北京廠肆(即琉璃廠),不必說買,聽也未曾聽過,選擇之精,可見一斑。”
據(jù)從19 2 9年開始給張學良當了八年內(nèi)差的趙吉春記述:“對于中國傳統(tǒng)的國畫藝術,張學良有著很高的藝術鑒賞力,在沈陽執(zhí)政時期,他已經(jīng)開始從各種渠道不惜重金購買古畫。緊挨著他辦公室的那間儲藏室,主要就是用來收藏古畫。每得佳畫,欣喜若狂,簡直達到如醉如癡的程度,有時甚至獨自在畫室流連到半夜。”根據(jù)趙吉春的記述可知,張學良收藏的古畫多為山水畫,其中以松竹梅鶴為題材的為數(shù)較多,他在沈陽時經(jīng)常伺候張學良入儲藏室觀畫,得以一飽眼福。“每臨觀賞之時,張將軍都先輕手徐徐將畫展平,再細細玩味。”
對張學良的書畫收藏起到推波助瀾作用的是他的兩位好友、結拜兄弟胡若愚和周大文。胡若愚曾任張學良副官,是張學良主政期間信任的得力助手。周大文是張學良早年的結拜兄弟,不僅擅長書畫鑒賞,在京劇和烹飪方面也頗有造詣。胡若愚、周大文雖然在當時的收藏界名氣不算很大,但二人的眼光頗為精準,書畫鑒賞水平非同一般。兩人根據(jù)張學良喜歡明史的特點,幫他逐步確定了以明清書畫和明清名人墨跡為主的收藏體系,建立獨具特色的系列收藏。收藏反過來又對張學良研究明史提供了很大幫助。
名貴珍藏化作過眼云煙
張學良的藏品大多是他在東北與北平主政時期購進的,其中涉及書畫、文玩、古籍和緙絲等各個方面的文物。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湖社月刊》曾作報道:“ 張漢卿主任,近于舊畫搜羅甚富,尤注重于文沈唐仇四家,兼及清四家,一般收藏家多愿割愛,于新畫亦極力提倡,本社會員,亦有為其所賞而命畫者。”
在著名鑒藏家張伯駒編著的《春游社瑣談》中,由單慶麟撰寫的《張學良所藏書畫目錄》一文記載:
張學良將軍嗜書畫,在掌東北軍政任內(nèi)搜集頗多,“九一八”變起倉卒,其所積蓄書畫在沈陽部分陷入敵手。日人投降后,余自渝返鄉(xiāng),于沈陽冷攤購得油印書畫目錄一冊。……目中羅列張氏藏品二百四十一種,六百三十三件,末附湯玉麟所藏十件,都凡六百四十三件。其煊赫有名之跡有王獻之《舍內(nèi)帖》、小李將軍《海市圖》、董源《山水卷》、郭熙《寒林圖》、宋徽宗《敕書》、米元章《云山圖》,下至元明清(諸大家如)趙松雪、錢舜舉、吳仲圭、王叔明、文(征明)、沈(周)、唐(伯虎)、仇(英)、四王、吳惲、石濤、八大之品俱備。顧所收殊雜,若慈禧、光緒以致東瀛畫人橫山大觀、中村不折等作品亦入篋中。
單慶麟還記述說,他在沈陽友人處曾見到過張氏原藏的仇英、惲壽平、王翚等軸卷。在北京經(jīng)周大文、胡若愚為張學良所收書畫多系精品,內(nèi)有元張子正《折枝桃花》卷最為名貴。
張學良給自己的書畫庋藏處取名“定遠齋”。后人曾對“定遠齋”作過多種解釋,多數(shù)人認為是表示齋主“志向高遠”之意,也有向東漢“定遠侯”班超學習或自比之意。與那些“存莫之奪,歿則以殉”的收藏者不同,張學良認為“獨樂樂不如眾樂樂”,早在2 0世紀30年代,他曾將自家同澤館內(nèi)多年收藏的書畫精品在東三省博物館(現(xiàn)沈陽故宮博物院)陳列展出。為了賑濟災民,張學良還把自己的珍藏拿出來拍賣,善款全部捐給災區(qū)。遺憾的是“九·一八”事變后,他在沈陽舊居定遠齋的珍藏被日軍洗劫一空。入駐北京后,張學良不改初衷,繁忙工作之余,仍然醉心于書畫收藏。西安事變后,張學良開始了輾轉(zhuǎn)流遷的幽禁歲月。盡管生活顛沛流離,那些他心愛的書畫藏品一直陪伴在他左右,為他孤寂的幽禁生活平添了許多快樂。晚年他將自己畢生的珍藏全部拍賣,所得善款除了安享晚年生活外,其余捐給了慈善事業(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