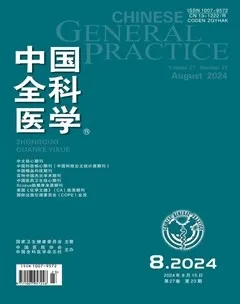基于腸道干細胞探討腸神經系統調節腸道炎癥的機制研究進展
陳思琪,肖瑾,田思雨,張佳,汪淑婷,張馨丹,朱焰,陳敏
610072 四川省成都市,成都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臨床醫學院
相關證據表明腸道干細胞(ISC)受到腸神經系統(ENS)調控,可促進ISC分化并調節腸屏障功能。ISC與ENS均與腸道炎癥存在密切聯系,其中ISC與腸道炎癥關系主要包括:ISC生態位細胞、生態位因子等通過生態位信號對炎癥產生反應[1];WAP四二硫化物核心域蛋白2(WFDC2)保持結腸上皮細胞緊密連接完整性,防止炎癥侵襲[2];ISC基因組不穩定激活Z-DNA結合蛋白1(ZBP1)-受體相互作用蛋白激酶3(RIP3)-混合譜系激酶結構域樣蛋白(MLKL)通路誘導腸道炎癥[3]。而炎癥性腸病中的胃腸道炎癥可誘發腸神經可塑性且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RAS)和腸道神經傳遞的相互作用可能導致結腸動力障礙。本文通過總結ISC、ENS與腸道炎癥三者之間的關系,探討了腸道炎癥相關的ENS損傷可能是腸道功能持續改變的基礎,而腸神經元及腸神經膠質細胞(EGC)為腸道炎癥性疾病治療提供了可行靶點,以期為ISC等多種干細胞用以治療腸道炎癥中出現的腸神經功能障礙提供思路。
本文文獻檢索策略:以“腸道干細胞、干細胞、腸神經、腸道炎癥、炎癥性腸病、潰瘍性結腸炎、克羅恩病”為中文檢索詞檢索中國知網、維普網;以“Intestinal stem cell,Stem cell,Intestinal inflammation,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Ulcerative colitis,Crohn's disease”為英文檢索詞檢索PubMed,檢索時間為建庫至2023年3月,排除相關性低、質量不佳的文獻。
1 ISC與腸道炎癥
腸道的再生能力依賴于位于腸隱窩底部的少量干細胞,研究表明ISC具有產生腸上皮的所有分化細胞類型[4],ISC必須在自我更新和分化之間保持非常嚴格的平衡,以維持組織穩態并避免干細胞耗竭或癌細胞生長的有害影響[5]。ISC與腸道炎癥關系主要包括3個方面:ISC生態位細胞、生態位因子等通過生態位信號對炎癥產生反應;WFDC2保持結腸上皮細胞緊密連接完整性,防止腸上皮屏障(IEB)破壞;ISC基因組不穩定激活ZBP1-RIP3-MLKL通路導致干細胞壞死,不可逆地破壞IEB的穩態并促進腸道炎癥(圖1)。

圖1 ISC與腸道炎癥相關性Figure 1 Correlation between ISC and intestinal inflammation
1.1 ISC生態位構成及其與腸道炎癥相關性
ISC生態位可以理解為一個由腸上皮細胞(IECs)、基質細胞、免疫細胞和微生物構成的系統。在腸道炎癥中,ISC周圍的生態位細胞(潘氏細胞、間充質細胞等)及其分泌的生態位因子(如分泌型磷脂酶a2等)可以通過生態位信號(Wnt、BMP、Notch等)促進ISC的再生,ISC的生長可以對炎癥細胞、炎性細胞因子和炎癥信號產生反應[1]。其中潘氏細胞為ISC的發育提供了生態位,在炎癥性腸病中有缺陷的潘氏和杯狀細胞分化可能使腔內微生物侵入黏膜并引發炎癥[6]。此外,IECs中的環境傳感器芳香烴受體(AHR)通路活化以保護ISC生態位以維持腸屏障的完整性[7]。而微生物群對上皮增殖的調節可以通過微生物代謝物來實現,這些微生物代謝物可以作為ISC生態位信號的信號配體,從而調節上皮增殖[8]。
1.2 WFDC2保持結腸上皮細胞緊密連接完整性,防止IEB破壞
IEB由具有多種功能的特化細胞組成,這些細胞從隱窩基部的ISC中產生。大多數上皮細胞是吸收性結腸細胞,其中散布著專門的上皮譜系,包括分泌杯狀細胞和腸內分泌細胞[9]。在腸隱窩的頂部,PARIKH等[2]發現了一個先前未知的吸收細胞BEST4/OTOP2細胞,其能夠感知pH值,并且可以通過調節鳥苷酸環化酶C(GC-C)信號通路來維持管腔內穩態,在腸道炎癥和癌癥中失調。還觀察到杯狀細胞位置重塑與WFDC2下調一致,WFDC2是一種抗蛋白酶分子,由杯狀細胞表達可抑制細菌生長。活體內,WFDC2保持上皮細胞之間緊密連接的完整性,并防止共生細菌和黏膜炎癥的侵襲。結腸上皮細胞失調,IEB破壞是腸道炎癥的基礎。
1.3 ISC基因組不穩定激活ZBP1-RIP3-MLKL通路導致干細胞壞死誘發腸道炎癥
在炎癥性腸病患者中,基因體不穩定、反應性內源性逆轉錄病毒、ZBP1上調和凋亡均可見,而ISC基因組不穩定激活ZBP1-RIP3-MLKL通路會導致干細胞壞死,進而誘發自發性腸道炎癥。實驗表明,小鼠組蛋白賴氨酸甲基轉移酶1(SETDB1)水平在ISC中的降低會失去對內源性逆轉錄病毒(ERVs)的抑制,由ERVs產生的過度病毒模擬可誘發ZBP1的依賴性壞死,通過RNA結合蛋白免疫沉淀同型互作基序結構域與RIP3結合,繼而激活MLKL的磷酸化,使之定位至細胞膜引發細胞壞死性凋亡,不可逆地破壞IEB的穩態并促進腸道炎癥[3]。
綜上所述,ISC與腸道屏障穩態維持密切相關,而IEB的破壞是腸道炎癥的基礎,且ISC可通過其生態位對腸道炎癥產生相關反應。
2 ENS與腸道炎癥
炎癥性腸病中的胃腸道炎癥可誘發腸神經可塑性且RAS和腸道神經傳遞的相互作用可能導致結腸動力障礙(圖2)。

圖2 ENS與腸道炎癥相關性Figure 2 Correlation between ENS and intestinal inflammation
2.1 炎癥誘發腸神經可塑性
腸神經可塑性包括腸神經元和EGC的廣泛結構和功能變化等[10],其中一些變化在炎癥恢復后仍可持續長時間存在,炎癥引起的神經可塑性極有可能導致活動和靜止期炎癥性腸病以及功能性胃腸疾病(如腸易激綜合征)的運動障礙[11]。
2.1.1 腸道炎癥中出現神經重排、腸神經元改變:對潰瘍性結腸炎或克羅恩病患者的組織分析顯示存在ENS異常包括神經節和神經束的肥大和增生以及神經膠質細胞的變化。在炎癥性腸病患者組織標本的超微結構可見腫脹的空軸突,腫脹的線粒體以及濃縮的神經原纖維等[12],對潰瘍性結腸炎患者病變腸道觀察顯示肌間HuC/D(+)神經元和S100β(+)神經膠質細胞的密度降低,膠質細胞、神經元比例增加[13]。BERNARDINI等[14]在斑馬魚的遠端腸道建立炎癥反應,發現在急性炎癥階段時膽堿能神經元的比例在遠端腸道中顯著降低,全腸5-羥色胺能神經元的比例顯著增加。
2.1.2 EGC是限制損傷后腸道炎癥反應的關鍵:EGC對炎癥環境的反應通常被稱為腸神經膠質反應,其被認為是體內IEB平衡所必需的。EGC在炎癥前通過產生和釋放可溶性因子來誘導腸道通透性、增加IEB細胞旁通透性[15-16];還可以分泌膠質來源的神經營養因子以保護IECs免受細胞因子誘導的凋亡,具有IEB增強特性[17]。EGC對炎癥的反應也包括受體表達的改變,包括神經生長因子受體TrkA、內皮素-1受體B、Toll樣受體4、緩激肽受體1等[18-19]。此外,迷走神經刺激(VNS)已被證明可以限制損傷后的腸道炎癥,完整的EGC需要傳遞VNS的腸道抗炎作用[20]。
2.1.3 神經肽如P物質、血管活性腸肽(VIP)等參與腸道炎癥反應:ENS和免疫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在腸道炎癥的病理生理學中起著重要作用,神經內分泌系統與免疫系統交流的機制是通過向終末器官受體釋放細胞因子和神經肽[21]。被認為與炎癥性腸病發病關系最密切的包括P物質、VIP等[22]。P物質信號可激活靶細胞中與炎癥刺激相關的轉導分子(MAP激酶等)并導致強效促炎細胞因子[白介素(IL)-1b等]的分泌[23-24],使得腸道炎癥期間神經激肽1(NK-1)受體上調[25]。NK-1受體對P物質具有最高的親和力,并且與炎癥最相關,但P物質和NK-1受體在炎癥性腸病的病理生理學中的作用研究還存在矛盾之處[26]。而VIP可促進結腸上皮細胞的分泌作用,并被證明具有抗炎作用,可下調促炎細胞因子和介質如IL-6、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IL-12、一氧化氮和趨化因子[27-28]。研究表明,VIP利于T輔助細胞分化向“Th2”表型發展,還能刺激調節性T細胞的產生,抑制巨噬細胞的促炎作用,有助于炎癥的下調[29]。雖然大量證據表明VIP參與了炎癥性腸病的病理生理學,但是也有關于人炎癥腸道活組織檢查中VIP表達的矛盾結果報道[30]。
2.2 RAS和腸道神經傳遞的相互作用可能導致炎癥性腸病結腸動力障礙
RAS參與了炎癥反應,包括胃腸道炎癥[31-32]。研究發現活動性克羅恩病患者在腸黏膜中的血管緊張素Ⅱ(Ang Ⅱ)水平高于健康對照組或潰瘍性結腸炎患者[33],而在葡聚糖硫酸鈉誘導的大鼠結腸炎中發現腸神經元參與Ang Ⅱ介導的結腸收縮[34],且Ang Ⅱ不僅直接作用于平滑肌,而且間接地干擾由血管緊張素Ⅱ受體(AT)1/AT2受體活化介導的肌間神經調節。RAS和腸道神經傳遞的相互作用可能導致炎癥性腸病結腸動力障礙,在由三硝基苯磺酸(TNBS)引起的輕度/中度實驗性結腸炎大鼠中,AngⅡ誘導的結腸收縮減少可能是由于AT1的下調以及一氧化氮和毒蕈堿受體在神經元和非神經元(如Cajal間質細胞和EGC)之間錯綜復雜的網絡通信中的改變[35]。
綜上可以推測,腸道炎癥相關的ENS損傷可能是腸道功能持續改變的基礎。
3 ENS對ISC具有調控作用,nAChR和Wnt信號協調維持上皮穩態
ENS對ISC具有調控作用,在ISC分化以及維持IEB中起重要作用。ISC上存在M3和M5毒蕈堿受體,由膽堿能神經控制,而膽堿能神經又受到黏膜傳入神經元釋放乙酰膽堿、P物質和降鈣素基因相關肽(CGRP)的影響,為ISC活體內的神經控制提供了證據[36]。BAGHDADI等[37]研究發現膠質纖維酸性蛋白(GFAP)+特異性神經膠質細胞亞群在體內平衡過程中調節干細胞的維持和自我更新,EGC與間充質細胞的聯合培養顯著改善了ISC功能,表明兩個群體協同調節ISC行為。此外,微生物叢、腸神經細胞、腸免疫細胞和ISC之間具有復雜聯系,有研究證實ISC是由微生物叢和腸隱窩壁龕內腸5-羥色胺能神經元調節[38]。
腸道中nAChR和Wnt信號協調活動的機制為上皮內穩態提供了新的見解,并可能與炎癥性腸病特別相關。有研究表明非神經元乙酰膽堿能促進隱窩絨毛類器官的生長和分化,而nAChR和Wnt信號的協調活動維持了Lgr5+的干細胞活性和平衡的分化[39]。在潘氏細胞中,炎癥引起的干細胞因子分泌通過c-Kit受體和一系列下游事件觸發信號,最終抑制糖原合成酶激酶3β并激活Wnt信號[36]。
綜上所述,ISC受到ENS調控,且可能通過nAChR和Wnt信號維持上皮穩態。
4 干細胞、ENS與腸道炎癥治療
腸道生態位周圍細胞包括腸神經元和EGC,可能是腸道炎癥性疾病治療可行靶點,而干細胞衍生ENS可用于治療多種腸道神經疾病,研究表明干細胞通過歸巢于炎癥區域表現出神經保護、抗炎和免疫調節作用。
4.1 腸神經元、EGC為腸道炎癥性疾病治療提供可行靶點
在腸道受損后EGC引起神經膠質生成,從而替換丟失或受傷的EGC來應對損傷,以快速恢復腸道屏障功能以限制持續的腸道炎癥[40]。EGC可為結腸炎引起的腸道修復提供關鍵的Wnt生態位信號,通過遺傳消除GFAP+EGC并抑制其在急性和慢性小鼠結腸炎模型中分泌干細胞生態位信號,EGC反應狀態是干細胞的腸上皮再生反應和黏膜愈合所需的[41]。腸道生態位周圍細胞包括腸神經元和EGC,可為干細胞細胞分化和ZO蛋白的表達提供信號,可能通過調節屏障功能或免疫反應為腸道炎癥性疾病的治療提供靶點[42-43]。
4.2 干細胞衍生ENS可用于治療腸道相關疾病
由干細胞衍生形成的ENS神經球或各種ENS組分被用于治療多種腸道神經疾病(如先天性巨結腸病等)[44]。多種類型的干細胞,包括ENS干細胞、胚胎干細胞衍生的神經前體、誘導多能干細胞等均能夠轉化為神經和神經膠質譜系[45-46]。HOTTA等[47]實驗證實腸神經干細胞可以從具有先天性巨結腸病的小鼠結腸神經節中分離,并且具有在離體和移植后產生神經元和神經膠質的能力,可形成腸神經元網絡。移植自體患者來源的腸神經干細胞消除了其他細胞來源引起的免疫和倫理問題,挖掘了使用自體來源干細胞治療先天性巨結腸病和其他腸神經病變的潛力。CHANG等[48]將分化的腸道神經冠細胞(ENCC)引入發育人腸類器官衍生的組織工程小腸植入物,導致增殖性遷移性神經元和神經膠質細胞(包括多種神經元亞型),并在收縮性測定中顯示功能。此外,骨髓間充質干細胞也在腸道培養基誘導下能夠分化為腸神經元并表達腸神經標志物,為基因治療ENS相關疾病提供了實驗基礎[49],預處理同種異體骨髓間充質干細胞在治療腸神經疾病方面可能具有治療價值[50]。
4.3 干細胞通過歸巢于炎癥區域并表現出神經保護、抗炎和免疫調節
近年來關于間充質干細胞治療炎癥性腸病的研究較多,但對針對其治療腸道炎癥引起的腸神經功能障礙的研究相對較少。ROBINSON等[51]實驗表明間充質干細胞通過歸巢于炎癥區域可表現出神經保護、抗炎和免疫調節特性,為減輕神經退行性疾病提供了治療益處,可有效減輕炎癥引起的結腸運動障礙,防止炎癥對ENS的損害,并減輕由TNBS誘導的結腸炎引起的腸道功能不良。STAVELY等[52]研究則發現在TNBS誘導的結腸炎活體內模型中,骨髓間充質干細胞比脂肪組織間充質干細胞在減輕體質量、結腸組織損傷、白細胞浸潤黏膜和奧氏神經叢方面相對更有效。兩種來源的間充質干細胞在腸神經元丟失和神經元亞群的神經化學改善改變方面具有同樣的神經保護作用,兩種來源的間充質干細胞均分泌轉化生長因子β1從而在體外發揮神經保護作用,但其體外特征不能外推到治療效能。
綜上所述,腸道炎癥相關的ENS損傷可能是腸道功能持續改變的基礎,而多種類型干細胞衍生ENS有望用以治療腸道炎癥中出現的腸神經功能障礙。
5 結語
雖然相關證據表明ISC受到ENS調控,但其具體信號通路調控的分子機制還有待后續進一步研究。ISC與ENS均與腸道炎癥存在密切聯系,但二者在腸道炎癥發病過程中相互之間的調控機制尚且不清。炎癥性腸病患者的癥狀與ENS的不良影響有關,與腸道炎癥相關的ENS損傷可能是腸道功能持續改變的基礎,對腸神經元的保護可以降低炎癥的嚴重程度[53-54],故腸神經元是新療法的可行靶點。由干細胞衍生的ENS可用于治療多種腸道神經疾病,并通過歸巢于炎癥區域表現出神經保護、抗炎和免疫調節作用。
目前雖有將ISC移植到對服用生物制劑無效的患者炎癥腸黏膜以重建IEB的報道[55],但尚無將ISC用于治療腸道炎癥引起的腸神經功能障礙的研究報道,因此ISC移植以治療腸道炎癥引起的腸神經功能障礙或許是將來的研究方向,且腸神經干細胞等多種干細胞在未來有望用于治療腸道炎癥以改善腸道炎癥中出現的腸神經功能障礙,其中干細胞類型、劑量、給藥方式、干預時間等均為臨床試驗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內容,同時研究者還應思考如何解決干細胞療法治療腸神經功能障礙中可能出現的免疫、倫理、安全性問題。
作者貢獻:陳思琪、肖瑾、陳敏提出文章寫作思路;田思雨、張佳、汪淑婷進行文獻/資料檢索、收集及撰寫中英文摘要;張馨丹、朱焰進行文獻/資料整理;陳思琪撰寫論文主體;陳敏負責論文修訂、文章的質量控制及審校、對文章整體負責,監督管理。
本文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