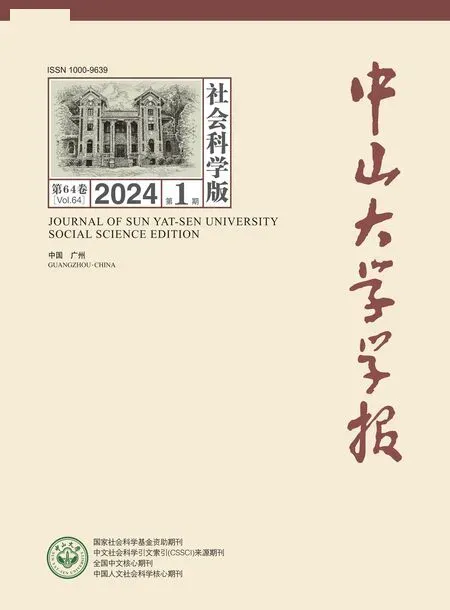晚清中外防疫交涉及其影響 *
杜麗紅
晚清中國被迫打開國門,在成為世界貿易網絡一員的同時,也受到全球疫情的影響。由于中國與西方在何時防疫以及如何防疫問題上存在著巨大差異,當發現疫情時雙方開始圍繞如何防疫的問題展開交涉,防疫就此成為外交議題。中國一般認為,防疫遠沒有治疫重要,主要在疫情暴發之后采取治療的措施;西方各國重視的是如何通過清潔衛生預防疫情的暴發,疫情暴發之后不以治療為主,而是將染疫者與健康者隔離開來。在中外人士共同生活的口岸城市出現疫情的時候,外國勢力會就采取何種防疫措施與中方進行交涉和爭論。概言之,疫情是防疫交涉的催化劑,而防疫交涉的基本內容則是列強以外交手段強迫中國按照西法防疫,中方則堅持傳統防疫,采取各種策略進行軟對抗,即表面上采取相似的組織和制度,但拒不接受西法防疫的措施,而將之化解為相似之道。
“西法防疫”并非簡單的防疫方式,而是建立在西方醫學知識體系之上,由一系列組織和制度構成,并受到國家法律規章的保障。以西法防疫為中心的防疫交涉,引發了中外間政治沖突和文化觀念之爭,不但關系到制度和組織層面的衛生行政,而且與醫學知識和文化習俗密切相關,結果促使西法防疫傳入中國,進而影響到中國在一些開放口岸建立衛生行政機構。晚清防疫交涉的參與者眾多,不僅有力主西法防疫的各國駐華外交人員、外國商業組織和租界當局,還有既排斥西法防疫又懼怕外來壓力的中央和地方官員,以及完全排斥西法防疫的地方士紳和普通民眾。故而防疫交涉涉及面廣,既有國家層面的外交斗爭,也有地方社會層面的交涉和文化抵制。
中外防疫交涉實質上是中西之間的碰撞,源自西方列強強制要求清政府采取西法防疫,由此引發中國官民對此舉的反思和應對,由于這一碰撞是在有著豐富抗疫經驗的中國社會進行的,須面對中華傳統醫學和文化觀念的挑戰和質疑,經歷了復雜的歷史過程。本文擬通過考察晚清中外防疫交涉的演化過程,分析其前因后果,揭示出中華文化在面對防疫交涉時的韌性,即使被迫采納西法防疫,各方仍設法維持中國的行政主權、人道主義精神和醫學理念。需強調的是,近代中國衛生防疫如其他事務一樣難以擺脫列強的干涉,以迫使清政府推行西法防疫為目標的防疫交涉,展現出列強通過強權外交對若干開放口岸的衛生防疫施加影響的側面,這是晚清衛生防疫史研究中不可忽視的內容①近代中國衛生防疫制度建立的問題早已為學界所關注,形成了不盡相同的理解、解釋和判斷。有的采用近代化研究視角,聚焦于具體衛生制度的形成。見Kerrie L. MacPherson, A Wilderness of Marshes: The Origins of Public Health in Shanghai, 1843-189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日]飯島渉:《ペストと近代中國:衛生の制度化と社會変容》,東京:日本研文出版社,2000 年;[美]羅芙蕓:《衛生的現代性:中國通商口岸衛生與疾病的含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有的側重西方各國尤其是日本的影響。見劉士永:《“清潔”、“衛生”與“保健”——日據時期臺灣社會公共衛生觀念之轉變》,《臺灣史研究》2001 年第1 期;劉士永:《武士刀與柳葉刀:日本西洋醫學的形成與擴散》,臺北:臺灣大學出版社,2012 年;杜麗紅:《近代中國地方衛生行政的誕生:以營口為中心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19 年第4 期。余新忠從防疫機制強調了疫情和觀念傳播對近代衛生行政體制的重要影響。見余新忠:《清末におけtf「衛生」概念の展開》,《東洋史研究》2005 年第3 期;《清代江南的衛生觀念與行為及其近代變遷初探——以環境和用水衛生為中心》,《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清代衛生防疫機制及其近代演變》,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
一、背景:西法防疫的擴散
19 世紀以來,人類交往和遷徙的增多為傳染病在全球的傳播提供了便利,霍亂和鼠疫交替流行。在帝國主義國家殖民擴張的加持下,西法防疫成為通行全球的瘟疫應對方法。然而,此時所謂的西法防疫不過是15世紀以來形成的一套以隔離、檢疫為主要內容的防疫措施②15世紀以來,在對抗鼠疫過程中,歐洲各國在西方醫學文化理念的支撐下,形成了一種長期有效的防疫措施,如給船只發放健康證和建立隔離所,政府監視來自被傳染的地中海港口的船只,將它們隔離開,或拒絕它們進港。見Paul Slack, “Responses to Plagu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The Implications of Public Health”, Social Research, Vol. 55, No. 3,1988, pp.441-442。。
早期,各國在傳染病來源和性質方面少有共識,應對傳染病的預防措施很簡單。1825年,英國海港檢疫隔離法案通過,要求船只離港或到港時,必須持有政府發給的健康證書(Bill of Health),對于發現鼠疫、黃熱病、瘟熱及其他傳染病的船只,由海關負責檢疫隔離。此后,檢疫成為航運大規模擴張時代跨國海運的一項重要措施,各大港口紛紛配備了高效而簡便的檢疫設施,以博取旅行者和商人們的信任。面對傳染病,人類只能將希望寄托于物理性防御:隔離和封鎖③[德]于爾根·奧斯特哈默著,強朝暉、劉風譯:《世界的演變:19 世紀史》I,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年,第373頁。。然而,這些措施實際讓人們感到害怕與憤恨:健康的乘客害怕與染疫病人共處一室,商人們則憤恨于船只延誤帶來的巨額貿易損失。海港檢疫隔離政策花費昂貴,且與英國自由主義信條相沖突,被人們指責為“野蠻的負擔、干擾商業、妨礙國際交往、威脅生活以及浪費大量公帑”④Krista Maglen, “‘The First Line of Defence’: British Quarantine and the Port Sanitary Authorit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15,No. 3, 2002, pp. 413-428.。到1860 年代,英國實行包括檢疫、隔離、消毒和監測在內的新檢疫規則,并取得了顯著成功,被稱為英國模式。與此同時,為縮短隔離的時間,整個歐洲大陸都轉向了檢疫、通報、隔離和消毒等新檢疫技術,用檢查和治療無癥狀乘客取代簡單檢疫,并對病患及其財物和居住地進行清潔和消毒。此后,政府設立一系列檢疫站,負責檢驗人群,焚燒尸體,收容染病者⑤Peter Baldwin, Contagion and the state in Europe, 1830-19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pp.151-188.。
隨著病因學的發展,對傳染病的應對出現了跨國界的預防戰略趨同。19 世紀中葉起,由于蘇伊士運河的開通、蒸汽輪船和鐵路交通技術的發展,世界各國成為聯系日益密切的整體,而傳染病的傳播隨之速度更快、范圍更廣。為此,歐洲各國加強了衛生領域的國際合作,自1851年開始就防治霍亂的傳播召開了8 次國際衛生大會,在“文明歐洲”和“東方”之間增加了國際主義、信息技術、現代科學以及現代行政機構等新的文化鴻溝。這種現象正如學者們揭示的那樣,海港檢疫實際上代表的是以對抗疾病(Against Disease)的全球聯合取代通過疾病(By Disease)的全球聯合①Emmanuel Le Roy Ladurie, “‘A Concept: the Unification of the Globe by Disease’”,The Mind and Method of Historian, Brighton, 1981, pp. 28-91; Valeska Huber, The Unification of the Globe by Disease? The 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ferences on Cholera, 1851-1894, 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 49,No.2, 2006, pp. 453-476.。
在歐洲帝國野心勃勃地進行政治、軍事和商業擴張的過程中,疾病及其傳染被視為最根本的危險,所以醫學不僅是帝國的“工具”,而且是歐洲殖民統治的一種實踐形式。疾病預防的需求倒逼帝國建立起更加系統的衛生和醫學制度,“衛生秩序”成為帝國政治秩序的一個重要側面②Roy MacLeod, “Introduction”, Disease, Medicine and Empire: Perspectives on Western Medicine and The Experience of European Expans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pp. 3-4.。西法防疫雖然并未成熟,卻是人類混合使用醫學和傳統手段,對一些歷史上曾給人類帶來嚴重危害的傳染病展開的阻擊。盡管這些措施未能使傳染病徹底絕跡,但基本遏制住了其迅猛的傳播勢頭③[德]于爾根·奧斯特哈默著,強朝暉、劉風譯:《世界的演變:19世紀史》I,第350—351頁。。從某種意義上而言,西法防疫成為殖民擴張的工具,成為一種殖民政治話語,成為區分“文明”與“野蠻”的標志,成為構造歐洲自我同一性的工具。
19世紀70年代起,科學醫學介入防疫,西法防疫方式被賦予了科學的內涵。然而,科學的進步是緩慢的,直到二十多年后,各界在科赫研究的有效性基礎上,才基本實現了新檢疫原則的國際趨同④Peter Baldwin, Contagion and the state in Europe, 1830-1930, p190.,但人類仍在繼續尋找對抗傳染病的有效工具。如艾伯斯指出的那樣:“盡管在第三次鼠疫大流行中,人們在識別鼠疫致病細菌和傳播方式方面,取得了新的進步,積累了新知識,但無論在印度還是中國,現代醫學權威真正采取的防疫措施還是傳承自歐洲的健康委員會,也就是和15世紀和17世紀第二次鼠疫世界大流行時一致。”⑤[美]約翰·艾伯斯著,徐依兒譯:《瘟疫:歷史上的傳染病大流行》,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20年,第85頁。
受西法防疫全球傳播的影響,清政府開始在個別開放口岸對來自世界各地的船只進行檢疫。1870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考慮,在港口疫情暴發的時候,像中國香港或日本那樣,設立檢疫制度⑥R. Alex Jamieson,“ Memo.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Yang-King-Pang and Hongque Settlements at Shanghai”,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Mar. 22, 1870.。直到傳染病來襲,海港檢疫才真正得以執行。1873年,暹羅和馬來半島出現嚴重霍亂,將中國置于疫情的威脅之下。由于大量中國苦力往來于廈門與暹羅和馬來半島,廈門稅務司休士(Mr. George Hughes)預感到有必要預防霍亂從廈門港傳入。為此,他制定了三條簡單的衛生規定,要求來自新加坡等霍亂流行港口的船只必須在指定地點下碇,等候海關醫官的檢查,且規定沒有海關同意禁止卸貨和卸客⑦“Circular No.4304 (Second Series)”,吳松弟整理:《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未刊中國舊海關史料》第248 冊,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影印版),2016年,第597—598頁。。同年8月29日,上海領事團會議討論通過了上海海港衛生規則,得到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的批準⑧“Meeting of Treaty Consuls”,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Sep. 6, 1873.。根據中外合作的原則,上海制定出《上海口各國洋船從有傳染病癥海口來滬章程》,其中規定:道臺任命海關醫官負責港口衛生事宜,在征得道臺和領事團的同意后海關醫官可以征收檢疫費用①《上海口各國洋船從有傳染病癥海口來滬章程》(1874 年7 月),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公共租界工部局檔,U1—16—2877。。對清政府來說,此時的海港檢疫不過是在海關任職稅務司的外人要求舉辦的一項海關業務,并不代表國人認可其是有效的防疫手段。中國人一直將瘟疫視作是上天的懲罰,“凡疫癘之作,其起也無端,其止也亦無端,大抵天意使然”,故往往求神拜佛,打醮修齋或請神巡游②《論防疫之禁令》,《新聞報》1894年5月24日,第1版。。無論是精通醫術的江湖郎中,還是各地官僚,沒有人相信疾病是由傳染所致,更無人意識到對感染者和疑似病患采取隔離措施的必要性③[德]于爾根·奧斯特哈默著,強朝暉、劉風譯:《世界的演變:19世紀史》I,第362頁。。
因而,港口的衛生規則并未得到有效的執行,時人指出:“這些規則是被沒有經驗的人草擬的,是無效的。即使被采用,也提供不了保護。”④“Sanitary Precautions”,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April 15, 1879.1882 年12 月21 日,一位名為Audax 的讀者在給報紙的一封信中,控訴上海港并未對載有天花患者的船只采取任何的防疫措施。雖然船長遵從規則,給吳淞港發了電報,報告天花患者的狀況,但是沒有收到任何回電或信號,客貨都如常卸載,好像什么也沒有發生。這表明在上海這個重要的貿易中心,衛生規則就是一個笑話,對那些執行港口衛生規則的人來講,掛黃旗幾乎沒有效果⑤Audax, “A Serious Accusation”,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Dec. 27, 1882.。此后情況并未好轉,1887年上海的英文報紙感慨道,上海從來沒有采取任何措施建立一套檢疫制度⑥“Quarantine and Shanghai”,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Feb. 2, 1887.。
在西法防疫擴散的背景下,中國海關在海關稅務司和各國領事們的主導下雇傭外國醫生,開始辦理海港檢疫。然而,海港檢疫不過徒有其名,敷衍了事,基本未對中國人產生直接影響。直到1894年香港鼠疫暴發,港英當局堅決采取西法防疫措施,引起英國人對華人抗拒西法防疫的不滿,也讓中國官民感受到西法防疫的嚴苛,進而正式開啟了中外防疫交涉。
二、香港鼠疫與防疫交涉的開啟
香港鼠疫期間,西方列強除在管轄范圍內嚴格執行西法防疫外,開始采取外交措施干涉中國的防疫事務,防疫上升為中外政治交涉的議題。防疫交涉開啟的原因在于,列強意識到中西處理疫情的態度和方式不同,希望通過交涉促使清政府按照西法進行防疫。清朝官員則認識到西法防疫的種種弊端,并積極應對列強防疫交涉,盡力避免其強制性隔離消毒措施給中國社會帶來混亂。
當香港發現鼠疫后,列強在亞洲勢力范圍內采取嚴格的防疫措施,預防疫情的蔓延。1894年5月11日,香港潔凈局頒布《防疫章程》,明確規定潔凈局有權將染疫者遷徙隔離在醫船或專處,對患疫者的居所進行消毒或焚燒,埋葬患疫斃命者,以及患疫者應向差館或官署申報⑦《香港治疫章程》,《申報》1894年5月22日,第10版。。5 月底,澳門要求潔凈溝渠、保持衛生,并派醫生對所有來自廣州或香港的乘客進行檢驗,“發現有疔瘡疫癥,或疑其患此癥者”,或不準其登岸,或用火船拖帶出埠⑧《澳門防疫》,《申報》1894年6月1日,第9版。。越南的法國殖民當局頒布章程,規定如有輪船由香港駛抵西貢,“須照例泊于禁界內6日,方準客貨登岸”⑨《選錄西報》,《申報》1894年5月31日,第9版。。
港督威廉·羅便臣(William Robinson)出示曉諭:“患疫者特歸一所,斃命者迅速掩埋,并將房屋水洗藥熏,不許撓阻潔凈。各總差入屋巡查,并遷徙病人或死者,及灑掃房舍,熏除穢氣等事。”港英當局強硬執行的這些西法防疫措施與中國人習俗相去甚遠。尤其是諸如隔離病人、消毒或燒毀患者所住房屋之類的措施,引起了生活在當地中國人的不解和恐慌,進而激發了強烈的反對意見。香港紳商高度關注防疫事務,與港英當局商議改進之策,改由東華醫院分局收容華人染疫者,并由華醫療治。不過,總督并未批準不許潔凈局人員進屋查搜的請求,也未同意將醫船上的病人搬往東華醫院分局①《港疫續述》,《申報》1894年5月28日,第2版。 上海市檔案館編:《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第1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33頁。。結果,嚴苛的防疫造成大量人口逃亡,6 月初香港回粵者每日不下千余人,有攜眷來者,有結伴來者,有肩挑負擔來者,有拖男帶女來者,老的、幼的、貴的、賤的,紛紛逃避②《遷地避瘟》,《新聞報》1894年6月22日,第2版。。
時人在觀察和經歷香港防疫的基礎上,形成了對西法防疫的基本認知。時任兩廣總督李瀚章在給總理衙門的電報中明確表示,西法防疫不適用于中國人,“香港以洋法治華人,闖入船內,飲以藥酒冰塊,熏以硫磺,以致死者日眾”;更明確反對“封倉禁人,不許來往”的隔離措施③《函復粵督查復香港瘟疫逐漸減輕瓊州丹教士已飭保護》(1894 年5 月26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檔案館藏,總理衙門檔,01—37—001—03—003。下文所用總理衙門檔案均出于此,不另注。。在時人看來,防疫不是政府的職責,而是社會的公共事務,一般應由善堂、同鄉會等組織以施藥和祈禱的方式應對,只有在疫情嚴重時才由地方官府主持拜神儀式。1894年3月,廣州發現鼠疫后,地方官府與士紳合作,“凡祈驤醫治之法無不舉行”④《為廣州瘟疫已減輕香港改用中醫治法以本土流行事》(1894年5月28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電報檔,2—02—12—020—0287。下文所用軍機處電報檔均出于此,不另注。。鼠疫暴發后,上而官憲,下而士民,“或誦佛經,或燒香藥,不一而足”⑤《焚香肇禍》,《申報》1894年5月7日,第2版。。5月1日,廣州府知府張曾敭督同南海縣令楊蔭廷、番禺縣令杜友白在城隍廟設壇祈禳致齋3 日,不理刑名,并示諭各屠戶不許宰殺⑥《時疫未已》,《申報》1894年5月21日,第2版。。稍后,督撫司各員札飭南海、番禺兩縣令開釋獄中百余犯人歸家⑦《遇災而懼》,《申報》1894年5月4日,第9版。。可見,西法防疫與中國傳統防疫格格不入,遭到了官府和社會的集體抵制,被斥之為不人道。恰如“傳統與現代化是水火不相容的,前者代表著人性,而后者代表著非人性”⑧[美]艾愷:《持續焦慮:世界范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2年,第5頁。。
然而,列強并不理會文化上的差異,反以保衛在華外人健康的名義直接對清政府防疫進行干涉,將之升級為外交層面的交涉事務,由此引起朝野上下對其可能引發內亂的擔憂。香港鼠疫期間,中外防疫交涉主要集中在中央層面,外國駐華大使僅僅要求清政府采取措施防止疫情蔓延,尚未強迫其采取西法防疫。5 月25 日,駐華各國大臣領袖俄國公使喀希呢(A.P.Cassini)致函總理衙門,要求告知“所得之病如何情形”,“貴國設有何法,或欲行設法之處”,從而“勿使瘟病布散華境”⑨《廣東時疫流行請為設法》(1894年5月25日),總理衙門檔,01—37—001—03—001。。次日,總理衙門將李瀚章防疫辦法告知喀希呢,“已飭局散藥醫療,官紳合力,凡醫治之法無不舉行”⑩《函復粵督查復香港瘟疫逐漸減輕瓊州丹教士已飭保護》(1894 年5 月26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檔案館藏,總理衙門檔,01—37—001—03—003。下文所用總理衙門檔案均出于此,不另注。。此外,各國駐滬領事團和租界工部局直接跟上海道臺交涉,要求采取防疫措施?。
面對升級為外交事務的防疫交涉,無論地方政府還是中央政府,都不得不開始關注防疫。由于,西法防疫遭到廣大民眾的堅決反對,官員們更擔憂可能由此引發排外內亂。由于香港嚴苛防疫,廣州善堂紳董憤懣地表示,“再燒香港民房,即焚省城、沙面以圖報復”。李瀚章密飭文武員弁,嚴拿造謠之人,禁止張貼,并添派兵勇保護租界,以期無事①《為香港瘟疫情形事》(1894年6月18日),軍機處電報檔,2—02—12—020—0384。。軍機處電知此事后,致電李瀚章,“港官焚民房逐疫,省城騷動,欲與洋人為難”,明確表示“港疫不息,民心總不能清”,令其加意預防保護②《為香港瘟疫設法派船接回內地醫治事》(1894年6月16日),軍機處電報檔,2—02—12—020—0377。。
然而,對于洋人的交涉不能不有所回應,于是官紳提出了華洋分治的策略。其實,華洋分治是中外雙方的共同選擇,兩者在這點上有著驚人的共識,但其背后所遵循的邏輯卻各不相同。清朝官民在經歷或見證過嚴苛的防疫措施后,切實了解到西法防疫的具體內涵,指責其毫無人道,違背基本的人倫天理,明確提出“華人用華法,洋人用洋法”。李瀚章表示:“香港時疫,洋官用洋法醫華人,豈能不斃?”③《為香港瘟疫設法派船接回內地醫治事》(1894年6月16日),軍機處電報檔,2—02—12—020—0377。與之相對,外國人在見證清朝官民的防疫舉措后,雖然指責他們的愚昧落后,但同意了“華人用華法,洋人用洋法”之方案。港督羅便臣批準了東華醫院紳董有關香港民眾要求回省城治病的稟請,并表示“自后如有患疫之人遷往玻璃局,由華醫調理,不復舁赴醫船醫”④《香港疫信》,《申報》1894年6月2日,第2版。。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亦采取華洋分治的措施,同意不信西法者轉而就華醫,“樂就西醫者,則有西醫診治,樂就華醫者,則有華醫診治”⑤《繼防患未然說》,《申報》1894年6月8日,第1版。。自此,中外雙方在防疫交涉中的策略基本形成,清政府視西法防疫為洋人專用之法,不適合中國社會,西人則意識到必須采取外交措施才能強迫清政府執行西法防疫。防疫交涉迫使清政府提出采取華洋分治,華人用華法也就意味著當疫情發生的時候,清政府必須與洋人共同采取措施應對疫情。至于采取何種措施,則在此后的防疫交涉中日漸明晰。
三、交涉深化與自辦防疫
香港鼠疫之后,揮之不去的鼠疫和霍亂交替威脅著中國沿海及陸地各口岸。與此同時,科學醫學快速發展,列強愈加堅信西法防疫能夠很好地控制疫情的蔓延。更重要的是,甲午戰敗后,列強加深了對華侵略的深度與廣度,直接干涉地方防疫事務,要求地方官推行西法防疫。因此,防疫交涉的范圍和深度都得到增強,各地領事要求地方官府遵照西法防疫,各地官員雖嚴詞拒絕,但迫于自上而下的政治壓力,又不得不遵辦。為應對列強的交涉壓力,清朝官民力主自辦防疫,堅持中西有別,要求洋人用洋法、華人用華醫。由于列強在各地的影響力不同,這些策略在各地有著不同的運作形式。
19 世紀末,列強屢次要求清政府在港口和陸地邊界地區采取檢疫和防疫措施,防疫交涉成為列強對華外交的重要事務之一。1897年2月18日,俄國公使巴布羅福(Pavlov Aleksandr Ivanovich)照會總理衙門,指出英屬印度暴發瘟疫,為防瘟疫傳入喀什等地,要求中國仿照各國進行西法防疫,在中印交界處留驗入境人員,“不準驟入華境,俟過一定日期確知并無瘟疫,方準入境”,對其所帶物件進行消毒,“應量力煙熏,或用他法,以除瘟萌”⑥在電文中,俄公使明確了各國采取的防疫之法,即:“以防瘟疫傳入各國境內,并在各口岸暨交界處安設查瘟疫局,由凡有印度說來之人在該局暫行留住,以便確驗有無瘟疫,所帶之物用藥除瘟。”見《印度瘟疫盛行宜預防傳入喀什噶爾希示復由》(1897年2月18日),總理衙門檔案,01—37—001—04—001。。總理衙門22 日電知新疆巡撫饒應祺照辦⑦《照復喀城設局防瘟已電疆撫照辦》(1897年2月22日),總理衙門檔案,01—37—001—04—002。。同年7 月8 日,駐廈門、福州的各國領事致電總理衙門要求頒布檢疫規則,聘請西醫檢查船只。東海關道錫桐、東海關稅務司賈雅格與各國領事議定章程7 條,于8 月4 日開辦⑧《東海關呈送廈門各處奉行檢疫規則經費清折》(1897年10月6日),總理衙門檔,01—37—001—05—001。。1908 年7 月,廈門、福州、臺灣惡疫流行,各國領事致電外務部要求實行檢疫,規定自此三口到煙臺船只必須請西醫檢查,每艘船收取25兩醫費,由關道籌款付給①《為廈門等處檢疫用款可否由俄商碼頭地價內動支事》(1897年7月9日),軍機處電報檔案,2—07—12—023—0295。 《衛生施醫》,《申報》1899年11月25日,第2版;《營口衛生所來函》,《申報》1900年1月2日,第3版。。從內容來看,這些交涉僅僅要求海關和陸關按照西法防疫的程序進行防疫。
隨著西法防疫的施行,中國官民對其利弊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認識。首先,時人意識到中西對于疫的認知是不同的。華人多將疫氣視為時癥,但并非不可治,而西人則“以此種癥候皆名為疫,見之甚畏,防之甚嚴”②《與客論驗疫》,《申報》1902年8月5日,第1版。。其次,中國人認為西法防疫非但不是善政,反而是一種虐待③《論爭回西牢押犯事》,《申報》1905年8月13日,第2版。。再次,時人對西法檢疫多持懷疑的態度。兩廣總督陶模認為不僅不能以西法治華人,而且質疑禁止運柩回鄉的防疫措施④《據廣東各善堂稟請旅港華民染病者準其回鄉調理》(1901年7月3日),總理衙門檔,01—37—001—03—006。。御史張元奇質疑“僅以行步、面色為憑”的驗疫之法,指出“死后更將尸身焚化拋棄,不許本人眷屬領回,稍與辯論,便遭毆辱”的做法不人道⑤《御史張元奇奏近年輪船進口驗疫請咨各國領事變通辦一折奉旨外務部知道欽此》(1903 年7 月31 日),“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外務部檔,02—14—014—03—009。下文所用外務部檔均出于此,不另注。。考慮到中西防疫的差異,為應對來自交涉的壓力,清朝官員提出華洋分治和自辦防疫的策略。張元奇提出國人應由華官派醫自檢,不能授權于洋醫。工部尚書陸潤庠在給外務部的公文中提出:“與西人分段辦理上船驗病、入院調治,西人歸西醫經理,中人則歸中醫經理。”⑥《函送汪麟昌等稟訴吳淞驗疫情形由》(1902年8月8日),外務部檔,02—26—002—02—002。
那么,防疫交涉的具體狀況如何呢?營口是列強通過防疫交涉,強迫地方官采取西法防疫的典型案例。1899 年7 月,營口暴發鼠疫,當地外國領事通過外交途徑向地方官府施加壓力,強迫地方官府接受西法防疫章程。領事希望各國能給總理衙門聯合施加壓力,“因為沒有這些壓力,中國地方當局無疑將像過去證明的那樣頑固且故意阻礙”⑦“The Plague at Newchwang”,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Sep. 11, 1899.。事實證明,各國領事的擔憂并非杞人憂天。8月17日,各國領事團公共會議擬定《營口防除疙瘩瘟疫章程》,提交給山海關道明保,結果被拖至9月8日才被婉拒⑧“Dr. C. C. De Burgh Daly’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Newchwang”, Medical Reports, 58th Issues, Shanghai: The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00, pp. 20-23.。此舉引起各國領事的不滿,他們通過各自駐華使館向總理衙門施壓,要求其電飭營口地方官府按西法防疫章程防疫⑨《議定防疫章程請山海關道籌辦由》(1899年9月12日),總理衙門檔,01—37—001—07—006;《請電飭牛莊地方官會同各國領事妥定清潔章程以免厲疫流行由》(1899年9月12日),總理衙門檔, 01—37—001—07—005。。接到總理衙門督飭其與各國領事妥籌辦理的電令后,明保態度有所緩和,會見各國領事,“允妥定禁章”⑩《咨送各領事所擬防疫章程由》(1899年10月9日),總理衙門檔,01—37—001—07—021。。
各國不僅要求中國嚴格按照西法防疫,而且要求中國政府直接辦理,不能由舊有地方社會組織代辦。根據章程,營口設立衛生局,由10人組成的衛生委員會控制,采取西法防疫:派醫挨戶查找病人,將患疫者送往醫院收治;對患疫者房屋進行消毒;在土圍各門派兵查驗有無病人通過;要求各義莊、義地的暴露棺木一律瘞埋,不準再厝,患疫死者只能經揚武門送五臺子義地瘞埋?。對此,營口商人表示堅決反對,提出國人自辦防疫的主張,并得到了明保的暗地支持?《營口各號商欲仿照防疫章程自置買義地并開設醫院以免外強干預請為立案由》(1900 年2 月21 日),總理衙門檔, 01—37—001—08—001。。然而,在外國人看來,中國人以寄存棺木處理尸體的辦法,事實上便利了鼠疫的擴散①“The Plague”,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2, No. 2032, Dec.9.。中東鐵路公司董事璞科第(D.D.Pokotiloff)呈文總理衙門,要其命令明保遵照西法防疫,協助俄國醫生開展工作,說服那些堅持要修改條文的當地頭面人物②《中東鐵路沿革史》,[俄]謝·阿·多勃隆拉沃夫著,劉秀云、呂景昌譯:《一個俄國軍官的滿洲札記》,濟南:齊魯書社,1982年,第2頁。。營口自辦防疫的主張就此被防疫交涉打壓了下去。
不過,這一狀況并未持續很久,自辦防疫逐漸成為東北地方官應對日俄防疫交涉的重要策略。自日俄開始在東北進行侵略,衛生防疫就一直是當地中外交涉的重要內容。無論在營口還是在哈爾濱,地方官和社會組織遇到外國人干涉時,往往仿照日俄成立相應組織,采取一些類似的簡單衛生措施,但都未真正大規模采用隔離和消毒的防疫方式。在鼠疫剛剛出現的時候,鐵路附屬地周邊的城市仍然采取舊有策略應對日俄那些早已耳熟能詳的外交措辭,早早成立防疫會,與日俄醫官合作辦理防疫。1910 年11月初,哈爾濱東清鐵路公司與濱江關道于駟興聯系,要求派俄醫到傅家甸查驗,將接近疫病患者的人都送交醫院③《俄員擬派醫士在道外驗病》,《遠東報》1910年11月11日,第2版。。于駟興立即成立濱江防疫會,其組織形式和規章與道里十分相似。于是俄國輿論認為,傅家甸官廳及自治會留意防疫,不僅通飭商民一律遵守衛生章程,而且“組織衛生局十分完全,如巡警局、自治會中外各醫士,以及道里衛生局代表等皆參預其事”,因此“傅家甸不致盛行瘟疫”④《預防瘟疫之要》,《遠東報》1910年11月24日,第1版;《濱江防疫之效力》,《遠東報》1910年11月21日,第2版。。
然而,如俄醫卜得白爾哥所指出的,濱江防疫會各種措施不過是一種形式上的模仿,由于對鼠疫有不同的認知,防疫會骨子里不愿意、也事實上無能力按照西法防疫。事后,于駟興在總結辦疫經驗時亦承認未嚴格執行防疫章程:“此間調查、消毒、檢驗諸法,早經照章實行,惟小民安于自便,檢查太嚴,輒相反對。紳商亦每稱不便,辦事員遂不免因此顧慮。”⑤《哈爾濱于道來電》(1910 年12 月31 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檔案館藏,錫良檔,甲374—15。下文所用錫良檔案均出于此,不另注。可見,地方社會自辦防疫的策略在于,仿照外國人設立相似的防疫機構,卻仍然恪守傳統防疫辦法,其目的在于既抵制西法防疫的非人道之處,同時也避免列強對國家主權以及人民生命造成侵害。
與之不同的是,上海由各行政機構共同參與建立起一套海港檢疫體系,基本實現了華洋分治。1899年前后,江海關開設崇寶沙防疫醫院,并頒布海口檢疫章程,建立了以崇寶沙醫院為中心的海港檢疫體制,不僅有了專門的醫院,而且有了一套消毒、隔離、治療的機制。1899年,崇寶沙醫院中分設華人和洋人養病所,并有專門婦女房間,由華醫之妻照料。1901 年5 月后,上海口岸的檢疫均由中國醫士隨同洋醫前往驗看⑥《上海驗疫事據好稅司復稱辦理情形并道署派員查看回報事妥協等語布達由》(1902 年8 月27 日),外務部檔,02—26—002—02—027。。
直到1910 年11 月東北鼠疫暴發初期,華人才爭取到了在公共租界自辦防疫的權力。當月初,工部局因發現鼠疫斃命者而采取嚴苛的防疫措施,命令毗連鋪面及周邊的居民一律搬出,將房屋封閉,進行消毒和滅鼠⑦《工部局防衛鼠疫之舉動》,《申報》1910年11月5日,第2張第1版。。結果引發了嚴重的風潮和騷亂:“毆西人,傷華捕,閉交易,一二人倡之,千百人和之,其勢岌岌,殆不可以終日。”⑧《論英界檢疫與華人治安》,《神州日報》1910年11月14日,第1頁。工部局全體董事邀請華商領袖、上海商務總會協理召開特別會議,很快就檢疫問題達成協議,決定由國人自設中國公立醫院,選派執有西醫文憑的華醫辦理⑨《中西紳董議決檢疫事宜之捷報》,《申報》1910年11月19日,第2張第4版;《工部局宣示防疫辦法》,《申報》1910年11月21日,第2張第2版。。自此上海公共租界的華人防疫交給國人自辦,但工部局衛生處仍負責租界內查疫的職能①《檢查鼠疫之善后談》,《神州日報》1910年11月25日,第4頁。。雙方達成妥協的基石在于遵循西方醫學原理,無論是任用有西醫文憑的華醫,還是成立防疫醫院,都采取以檢疫、隔離、消毒為核心的西法防疫措施處理疫情。
香港鼠疫后,中外防疫交涉在口岸城市日漸擴散,其核心內容是明確要求清政府采取西法防疫。無論是中央級別的外交,還是地方級別的交涉,基本都圍繞著具體防疫方式展開。面對來自列強的外交壓力,清朝官民堅持中外有別,或主張華人由華醫治,或自辦防疫。這些應對之策反映了國人抵制外人干涉的思想,也成為外人不得不依靠防疫交涉迫使國人采取西法防疫的動因,結果造成防疫交涉日漸頻繁。
四、東北大鼠疫期間的交涉與防疫
歷時半載之久的東北大鼠疫,沿鐵路線從哈爾濱蔓延開去,在很短時間內傳至長春、奉天、天津、北京及華北各地,死亡相繼,引發各界的恐慌。由于東北特殊的地緣政治環境,防疫交涉貫穿整個防疫過程,清中央政府不得不面對來自公使團的外交壓力,東北地方政府則面臨來自同城的日俄勢力的干涉,正如錫良所言:“防疫一事,主權民命攸關,辦法稍未完全,貽害無所應止。”②《飭各道府廳州縣電》(1911年2月17日),錫良檔,甲374—26。清政府堅持以避免干涉為第一宗旨,要求各級政府把握防疫的主動權,處于領導防疫的核心地位,避免防疫主權的旁落。因此,避免外國直接干涉成為清政府在防疫交涉中的核心原則,而這一策略客觀上起到了促使清政府采納西法防疫的效果。需指出的是,避免干涉并不是東北大鼠疫過程中清政府才有的政策取向,而是晚清從中央到地方在處理涉外事務時所采取的一貫政策。無論是中央政府在處理涉外事務時,還是東北地方官府在處理相鄰鐵路附屬地事務時,都將避免干涉作為重要目標。
在東北,防疫交涉一直是中外日常交涉的事務之一,日俄勢力自然習慣于通過交涉強迫清政府重視防疫。究其原因,仍然在于中西醫學和文化觀念的不同。中醫認為鼠疫并非不可治愈,或服藥,或針灸,都可起到防疫的效果。西醫則認為無法醫治,必須采取積極措施,通過隔離、消毒、檢疫等手段將疫情控制在特定范圍內。無論是以錫良為代表的清政府官員,還是普通中國人,都對西法防疫持懷疑的態度。錫良對中國不能厲行西法的原因有著清楚的認識:“查各國防疫以斷絕交通,嚴杜傳染為要,著我國素無防疫之法,商民狃于習慣,對官府之禁阻交通,則以為虐政,每遇實行隔離消毒,百計抵制,謠諑繁興,甚至疫斃之尸藏匿不報,以致蔓延未已,傳染甚烈,實堪浩款。”③《致軍機處電》(1911年2月16日),錫良檔,甲374—46。施肇基在萬國鼠疫大會致辭中描述了國人對于西法防疫的不滿之處:“執行如此明顯的粗暴工作,即盡快地把鼠疫患者與他們的家屬分開,并移送鼠疫醫院或其他隔離營等等,給政府的工作帶來了巨大的壓力。”④國際會議編輯委員會編輯,張士尊譯,苑潔審校:《奉天國際鼠疫會議報告》,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 年,第7頁。
官員們心里非常清楚社會對西法防疫的抵觸,“至以衛民之良法,疑為賊民之苛政”⑤《民政司張貞午司使親臨防疫會演說詞》,《盛京時報》1911年1月20日,第3版。。此外,在疫情結束后撰寫的疫事報告書中,防疫官員對社會各界反對西方防疫措施的根源作了深入分析,指出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在于,西法防疫措施與中國人習俗不合,人民很難從內心深處接受。首先,焚化疫尸的舉措與傳統喪葬習慣不符。其次,強制診治及隔離染疫者與民間忌醫習俗不符。再次,斷絕交通的舉措與民間返鄉過年的鄉土觀念不符。最后,隔離和消毒舉措與人們的倫理觀念相沖突①[清]奉天全省防疫總局編譯,吳秀明、高嵐嵐點校:《東三省疫事報告書》,載李文海、夏明方、朱滸主編:《中國荒政書集成》第12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305頁。。由于這些因素的存在,列強在面對嚴重的疫情時,必然會展開防疫交涉,給清政府施加壓力,強迫其采取西法防疫。
鼠疫暴發后,日俄兩國遵循國際醫學界對鼠疫的診斷標準和治療措施,在鐵路附屬地、租借地厲行防疫。與此同時,日俄積極與東北地方官府進行交涉,要求重視疫情,并采取相似的防疫措施,以避免疫情的蔓延。哈爾濱疫情逐步惡化后,俄國認為地方交涉方式已經無法迫使地方官紳遵照其意見辦理,轉而通過俄使與外務部的正式外交途徑解決問題,即以武力干涉為手段威脅清政府,由中央政府以命令的形式讓地方官府遵照辦理。日本人則指責:“華官所管各處,防疫事宜毫不仿文明辦法,惟裝飾外面之形式而已,絕無實行,以致鼠疫日熾一日。”②《奉天防疫之與各國領事》,《泰東日報》1911年2月11日,第2版。在整個疫情期間,日本一直通過外交施壓的方式試圖攫取并控制中國的防疫主權,甚至將臨時防疫本部從大連遷至奉天,旨在直接跟東三省總督進行交涉,并干預中國防疫指導工作。
由于疫情未得到及時控制,鼠疫從哈爾濱沿著鐵路線蔓延到京師,威脅到外國人的安全,各國一致采取自上而下施加外交壓力的方式,與外務部交涉,要求清廷命令東北督撫厲行西法防疫,“中國政府雖在中國土地自有高上主權,然瘟疫之危險奚止關乎中俄兩國,故不得不共起謀之”③《瘟疫與中國政府》,《遠東報》1911年2月16日,第1版。。在外交壓力下,清政府堅持以避免干涉為原則,要求各級政府一方面積極防疫,避免落人口實,另一方面注意把握防疫的主動權,避免主權旁落。
來自外國的干涉壓力和清廷的政治壓力日增,以施肇基、錫良為首的官員們不得不認真對待防疫事務:一方面慎重對待日俄等列強的要求,主動采取西法防疫,將防疫的領導權掌握在清政府手中,盡力避免外國對防疫工作的直接干涉;一方面主動舉辦萬國鼠疫大會,避免日俄攫取中國防疫的指揮權和主導權。簡言之,清政府維護防疫主權的方式是,以聽從西方要求的方式換取不干涉,從而將防疫的領導權掌握在自己手中。錫良在對待日俄具體交涉時非常慎重,嘗試做出有理有節的回應,盡量通過中國自己的力量解決問題,避免外國插手,“本大臣于此次防疫不少寬假雷厲風行,無非欲使疹癘早除,以杜外人干涉,但救一分民命,即保一分主權”④《昌圖議事會日前條陳防疫事宜》,《吉長日報》1911年2月24日,第6版。。他非常在意是否讓外國人滿意,將避免干涉作為一種追求。在給外務部的電文中,錫良寫道:“奉省防疫辦法不敢謂無暇可指。惟始疫至今,一意進行,實已不遺余力,英德美各領事及來奉醫員尚無間言,足資印證。近與日領會議,尚無顯然干涉情形。”⑤《致外部電》(1911年3月9日),錫良檔,甲374—46。
在防疫交涉進行的同時,外務部派伍連德前往哈爾濱領導防疫,實現了國人自辦西法防疫。他經過調查研究后決定厲行西法防疫,在傅家甸建立了防疫體系,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防疫措施。通過中俄交涉,解決了道里、道外斷絕交通和火車停運問題,斷絕了鼠疫向外擴散。在醫務人員和軍隊的援助下,防疫局的觸角延伸到城市的每個角落,保障防疫措施落實到每條街道、每個房屋、每個人。隔離、消毒、焚化尸體和接種疫苗等措施得到有效執行,疫情在30 天內得到了控制,每日死亡人數從二百余人降到零⑥國際會議編輯委員會編輯,張士尊譯,苑潔審校:《奉天國際鼠疫會議報告》,第315頁。。哈爾濱有效的防疫客觀上使俄國人干涉的聲音消失了,得到了錫良的肯定,要求“各屬亟應斟酌情形,仿照辦理”⑦《致軍機處電》(1911年2月16日),錫良檔,甲374—46。。
此后,清政府將這一成功經驗在整個東北乃至全國廣泛推行。1月25日,錫良在給軍機處的電文中表示,必須“病者治療,生者隔離,死者消毒掩埋,非西醫不辦”①《致軍機處電》(1911年1月25日),錫良檔,甲374—46。。奉天民政使司韓紫石表示防疫之法“首以遮斷交通為第一義,次以撲滅微菌為第二義”②《韓紫石司使復關東羈客論防疫行政書(續二十三日)》,《泰東日報》1911年2月26日,第1版。。錫良在通飭地方官的電文中,特別指出鼠疫無完全療治方法,注重預防,以消毒、隔離,遏其傳染③《通飭三省各道府廳州縣電》(1911年2月9日),錫良檔,甲374—26。。需強調的是,雖然采取了西法防疫,但東北地方官員仍然采取一種調和的態度,試圖維系整個防疫處于一種動態平衡的狀態,既要保障防疫效果,杜絕外人干涉之意,又要關照地方官民心理,以防社會反抗之舉。錫良在給吉林巡撫的電文中指出,西醫視受病之人必死,因此西法防疫注重于預防生者的傳染。這一做法“誠非民情所愿”,因此主張一方面從西醫預防,一方面仍設法療治,“盡我心力”④《致陳簡帥電》(1911年1月29日),錫良檔,甲374—15。。
除了自辦防疫避免干涉外,清政府還當機立斷,決定舉辦萬國鼠疫大會,掌握鼠疫研究和討論的主動權,避免日俄利用醫學優勢攫取醫學發言權。1 月20 日,俄國駐華公使廓索維慈(I.J.Korostovetz)照會清政府,要求“派各國專門醫生,前往該各處考察最重之地及致疫之源,并報告瘟疫流行之情形,已通告各國政府矣”⑤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12082376900(第246畫像)、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一件/一般的防疫施設(B—3—11—4—85)(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部擔心俄國人喧賓奪主,指出“此事關系主權,礙難聽彼干涉”,應當由清政府設法倡辦。于是,外務部決定給清政府駐外使節發電報,照會各國駐京大使和公使,請各國政府選派醫生前來中國討論致疫緣由和防救方法。清政府決定提供各國醫生到京后旅費,并令吉林、黑龍江兩省巡撫妥善招待到東北考察的各國醫生⑥《外部來電》(1911 年1 月25 日),錫良檔,甲374—46;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12082376900(第245畫像)、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一件/一般的防疫施設(B—3—11—4—85)(外務省外交史料館)。。事后,時人對舉辦萬國鼠疫大會的決策評價頗高:“蓋早懸一發起召集萬國會議之志望,卒如其所志望,而召集萬國會議。中國人居發起人之榮名者,以是為權輿噫?是寧得以尋常戰績相提并論乎?”⑦旁觀者:《戰勝北方鼠疫之二杰》,《青年》第14卷第8期,1911年9月,第166頁。
東北大鼠疫初期,西法防疫措施因與中國防疫方式相悖,受到中國民眾的抵制。列強藉此干涉中國防疫內政,防疫交涉成為影響清政府決策的重要因素。為避免列強侵害中國國家主權,尤其是日俄借機侵略東北,清政府任命中國醫生領導防疫,主動大規模推行西法防疫措施,避免了直接干涉。與此同時,為減輕推行阻力,避免因此引起的民變,清政府也不得不多加變通,兼顧民眾的利益與情緒。更重要的是,在萬國鼠疫大會上,清政府明確表達了對西法防疫及科學醫學的接受。施肇基表示:“從今以后,我們決心用所能獲得的最先進的科學知識武裝起來,去戰勝所面臨的鼠疫。”⑧國際會議編輯委員會編輯,張士尊譯,苑潔審校:《奉天國際鼠疫會議報告》,第8頁。與會的外國專家贊賞了清政府采取“文明途徑”(即西法防疫)應對鼠疫蔓延,肯定其“御疫之策,尤稱適宜”⑨《萬國鼠疫研究會始末記》,《中西醫學報》第13期,1911年5月,第4頁。。
結 論
近代以來,外國人多聚集在新興貿易口岸城市,繁忙的海外貿易潛藏著來自世界各地疫情的威脅。為保障僑民在華的健康,西方各國需要促使當地中國人重視疫情與衛生,接受西方防疫觀念,并推動清政府建立符合國際規范的衛生行政機構,采納西法防疫作為國家政策。在此過程中,防疫交涉在晚清中外關系中逐漸興起,承載著制度、文化、權力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具有歷史偶然性和結構必然性①此處的結構是理解事件發生的關鍵,具體而言就是“經濟、軍事、意識形態和政治競爭以及相應的社會權力都有著不同的結構性特征,而分析這些結構性特征則是理解時間/歷史的結構的關鍵所在”。趙鼎新:《時間、時間性與智慧:歷史社會學的真諦》,《社會學評論》2019年第1期,第9頁。。這種偶然性體現在,疫情是無法控制的,暴發是難以預測的,空間是隨機的,而每次疫情中的交涉及訴求基本圍繞著列強督促清政府采取西法防疫而展開,體現出結構性的特征。
疫情暴發是防疫交涉的導火索,但防疫交涉的過程主要受制于文化和政治因素。從醫學文化層面來看,以檢疫、隔離、消毒、遮斷交通等措施為內容的西法防疫,旨在將健康人與染疫者隔離開來,與中國傳統的以散藥治療為核心的防疫措施有著天淵之別。那些親歷西法防疫的國人,無論是香港居民,還是出國淘金的勞工,并未體會到西方醫學文化的優勢,反而遭受的是帶有種族歧視的非人道的強制性隔離和禁閉。這些經歷必然引起國人對西法防疫的強烈反感。因此,承載著現代制度文明理念的西法防疫,遭到了國人的堅決抵制,沒有得到絕大多數中國人的認同。這種文化上的不認同成為中外防疫交涉產生最直接的原因。
防疫交涉深受中外關系的影響,是強權政治壓迫下的產物。近代中外關系是由不平等條約和治外法權所塑造的,因此防疫交涉是不平等的,實際上是一種“文明”強加于“他者”的過程。由于醫學理念差異過于明顯,列強在處理衛生事務中形成了必須通過外交干涉才能迫使清政府接受西法防疫的認知。無論是租界當局,還是各開放口岸的外國領事,對于各口岸時有發生的疫情都非常關注,往往通過交涉迫使清政府采取西法防疫。可見,防疫交涉是近代中國不平等外交的產物,列強所主張的西法防疫自然帶有西方政治霸權的色彩。
基于中外之間政治不平等和文化差異,晚清中外防疫交涉經歷了從無到有的過程。19 世紀70 年代,廈門、上海設立海港檢疫,由海關稅務司和領事團的外人辦理,尚未涉及中外交涉。香港鼠疫期間,如何防疫成為中外都不得不面對的問題,由此開啟的防疫交涉仍停留在要求中方采取防疫措施的層面。經此一疫,中國人真正認識到強制性防疫造成的社會混亂和危害,更加傾向于采用傳統方式對待瘟疫,外國人則強烈感受到中國人對檢疫、隔離、消毒措施的堅決抵制。最終,中外雙方采取華洋分治方式實現了彼此的共存。此后十余年間,疫情頻發,加之帝國主義侵華程度日深,列強通過強推西法防疫干涉中國內政,中外防疫交涉得以深化。對此,營口、哈爾濱、上海等口岸城市的官民采取自辦防疫的應對策略,形式上接受了西法防疫。及至東北大鼠疫,防疫交涉迫使清政府主動實行西法防疫,以維護國家主權,避免受到列強的直接干涉。可見,中外防疫交涉促使清政府逐步接受西法防疫,國人則顯示出對西法防疫的辯證態度,政治上接受而文化上拒絕。
在中外防疫交涉過程中,國人自辦西法防疫成為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形式。此舉通過認可西法防疫的合理性,保障了中國防疫主權,避免因文化隔閡而產生的矛盾上升為外交事件。在接受西法防疫形式的同時,官府往往堅持中西有別論,采取既接受西法又堅守傳統的“洋人用洋醫,華人用華醫”的策略,力圖在博弈中維護中華文化傳統,在固有文化中調適異文化的措施。當東北大鼠疫疫情嚴峻,防疫交涉力度驟增,清政府才完全自主施行西法防疫,接受科學醫學,在東北各地建立起防疫組織和制度。換言之,晚清中外防疫交涉是現代衛生防疫進入中國的重要動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