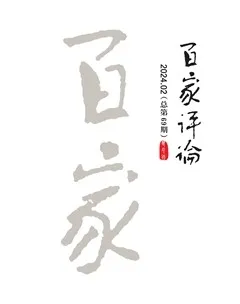涌動的“青潮”
溫奉橋 張波濤
內容提要:近年來,青島的長、中、短篇小說創作皆迎來了一個豐收期、拓展期,特別是涌現出了以《雪山大地》《觀相山》為代表的多部重量級作品。青島近年小說創作以其開闊的時空視野構建出了以“青島”為重心的立體文學時空矩陣,在多元的人物畫廊中初步突出了“青島人”的核心形象,關注處于存在困境之中的“斗爭”與“突圍”,并體現出一種以現實主義為中心、富有“青島味”的美學風格。
關鍵詞:青島作家? 小說? 述評
近年來(2021—2023),青島小說創作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勢頭,涌現出了一大批具有標志意義的作品。青島作家們不僅沿著歷史的足跡逆流而上追溯“青島”文化與歷史,思考“青島人”多種生存境遇,同時,又放眼更寬廣的空間,探索更廣范疇、更具多樣性的人生圖景,進一步拓展了青島文學的表現域、穿透力,用小說對“存在”展開了更深刻的銘記與思辨。大處著眼、細處落筆,既描繪了“大時代”的陣陣波濤,又牽掛著“小人物”的層層浪花,講述了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人、事、情各自的軌跡及其辯證關系,形成了中國當代文學海洋中的一片美麗海灣。
具體來說,在青島近年小說創作最具里程碑意義的是楊志軍長篇小說《雪山大地》榮獲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而阿占的異軍突起,則成為青島近年最重要的文學現象。就長篇小說創作而言,青島近年代表性作品主要有艾瑪的《觀相山》,瑛子的《如果河流會說話》(發表時名為《江河有聲》,出版時改為此名),連諫的《遷徙的人》《你好,1978》《流年》,余耕的《金枝玉葉》《做局人》等。中篇主要有艾瑪的《柚林深處》,阿占的《墨池記》《后海》,方如的《雪花白》,余耕的《我是夏始之》,瑛子的《當雪花遇上梅花》等。短篇小說代表性的有高建剛的《陀螺大師》《太平角》,艾瑪的《看不見的旅程》《島》《在閣樓上》,劉濤的《老逃》《戰傷》《嬗變》,阿占的《貓什么都知道》《殘鳩》,于欽夫的《茶館客人》等。兒童文學領域,除了劉耀輝、張吉宙繼續捧出《尋找艾米》《爸爸的菜譜》等佳作之外,以于瀟恬為代表的青島本土新生代兒童文學作家迎來了創作噴發期,《你在冰原》《冷湖上的擁抱》《海上飄來你的信》等長篇小說逐漸展示出更為成熟的寫作風格。此外,楊志軍2022年出版的《三江源的扎西德勒》,也試水兒童文學,從兒童視角延續或重構了自己的青海書寫。
一、立體的“文學矩陣”:立足青島放眼
開闊時空
小說是時間的藝術,也是空間的藝術,對小說空間的選擇、營造,故事結構的建構,都是對空間的使用。時間、空間往往不只是故事的背景,也會深度參與故事的發生,體現作者的用心。整體而言,青島近年小說創作表現出了非常開闊的時空視野,形成了一個立體時空文學矩陣,彰顯了“存在”的時空痕跡。
在時間維度上,青島作家近年來的創作展現了更為開放的歷史視野。楊志軍的《雪山大地》、阿占《墨池記》跨越新中國成立以來各個歷史階段,余耕的《金枝玉葉》展現了新中國半個多世紀來的發展與變遷。連諫的《遷徙的人》故事發生在民國初期至解放初期,《流年》的時間線從20世紀50年代延伸至今;艾瑪的《觀相山》、高建剛《陀螺大師》等,時間跨度都很大,體現出了作家強烈的歷史意識。
同時,也體現出了開闊的空間寬度。《墨池記》《后海》《觀相山》《你好,1978》《太平角》《陀螺大師》等作品以青島城區為主要空間背景;《遷徙的人》是從高密到青島,《最后的農民工》是從梅林渡、三十里鋪到青島,《尋找艾米》是從農村到青島;以上作品均與地理上的“青島”有關,某種程度上可以歸納為一種“島內敘事”“內窺視野”。除此之外,青島作家還關注了更廣闊的“島外世界”。《雪山大地》讓故事在遼闊的青藏高原上展開。《我是夏始之》涉及到了繁華的北京、遙遠的藏區、臺灣地區甚至異國他鄉(法國)。于瀟湉的《你在冰原》《海上飄來你的信》等則立足青島放眼深海遠洋和萬里之外的南極。青島作家的這些“空間偏好”體現出了守正創新、守土開放的創作姿態。
對于青島小說創作,“海”是不可繞過的重要空間要素。近年來,青島作家的“海濱書寫”已成為其最為顯著的特色,呈現出從“物理空間”向“心理空間”“文化空間”的進階,并且在某些作家那里沉淀為了一種美學風格。在這方面于瀟湉是一個鮮明的代表,她的多部兒童文學作品都發生在海上甚至海底,不僅有近海還有遠洋,將“海濱書寫”升級為了“人-海”互動更為密切、激烈的“海洋書寫”,深入了海洋本體,這在中國兒童文學創作中是比較少見的。在青島作家近年來的“海洋書寫”中,“海”越來越多地被寄予了一種民族轉變、社會轉型、文明轉向的歷史哲學色彩。就此而言,對于空間的自覺不僅反映出青島作家的心態、視野具有全球時代的現代性、開放性,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青島作家的創作成熟。
由作品的時空營造可以看出,青島作家近年的小說創作在縱向上跨越了百年歷史,有歷史縱深感,在一定程度上“聯手”貢獻了一部雖然不夠全面豐富但時間線索清晰連貫的“青島百年成長史”。這種不謀而合,反映出“青島作家”是一個真實的概念,這個集體正不約而同地試圖用手中的筆穿透歷史、洞察青島,努力“凝視”“諦視”乃至“審視”青島這座年輕城市的作用形態和存在方式。
二、“青島人”的“崛起”:人物形象營構的多元與重心
立足于青島而望向世界的時空視野,決定了青島作家近年來的創作展開了“青島人”的構建。這個過程中,多元的“非青島人”形象不乏亮眼的“光點”,但以青島為背景所塑造的一大批鮮活的“青島人”形象實際上是多元中的重心,形成了一條“光帶”,他們年齡性別不同、性格氣質各異,來自多個階層,生活在不同領域,合在一起就勾勒出了一組以“青島人”為核心概念的人物群像。“光點”與“光帶”構成了一片耀眼的“光域”,照亮了“存在”的價值維度。
這其中有耀眼的時代英雄。楊志軍的《雪山大地》選擇了一個對讀者而言相對“陌生”的描寫對象:青藏高原的藏族牧民,著力塑造了一個漢族干部“強巴”的光輝形象。對藏區牧民來說,“強巴”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式現代化”偉大進程啟蒙與建設力量的人格象征。《最后的農民工》生動地描繪了改革開放之后膠東半島上一群青年農民在青島創業的壯麗畫卷。這些農民工沖破觀念、家庭、情感的束縛,懷揣夢想來到城市創業。在楊志軍筆下,“城市”和“農民工”的關系模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他們不再是“城市”的“附庸”,“城市”只是他們發現自我、升華自我、實現自我的一個舞臺。這種逆向的觀察具有一種顛覆性的深刻。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辯證的“深刻”在《雪山大地》中同樣得到了延續和深化。《最后的農民工》和《雪山大地》觀察的空間方向貌似“相反”,但思考模式非常相似、思考線索一脈相承,兩部小說堪稱“姊妹篇”。
如果以思想傾向為考察維度,可以把近年來年青島作家筆下的“青島人”劃分為守舊的老一代青島人形象和開放的新一代青島人形象。這方面連諫的《你好,1978》、阿占的《后海》等小說是值得重視的考察對象。《你好,1978》中的杜建成、趙桂榮夫婦是老一代青島人的典型代表:樸實但守舊。新一代青島人有兩個“支流”,一個是老一代青島人的后代(或可稱之為“青二代”),另一支流則是改革開放后進城務工并創業定居的青年農民工(或可稱之為“新市民”)。《你好,1978》中的杜滄海是“青二代”的杰出代表,《最后的農民工》中的常發財、馬離農、罩子等,則是“新市民”的典型。兩條來自不同“發源地”的“支流”在很多性格特質與人生經歷上實現了“合流”:成長環境艱苦、創業謀生艱難,放棄舊的生活道路往往都是生活所迫,都是各自環境中的“不安分者”,都有著勇氣、頭腦、毅力,在創業成功之后也都不約而同地把更多目光轉向了精神世界,遇到了精神上的重重困惑。他們是新時代的弄潮兒、新青島的建設者,代表了改革開放、開拓進取的發展方向。這些不同思想的代表形象化地記錄了青島人的精神蛻變過程,構成一座城市的集體記憶。
綜合來看,這些形象還可以構成一個完整的人物譜系,連綴成一幅“人物長卷”。《遷徙的人》《你好,1978》表現了“外地人”從逃難苦力到城市小人物再到商界大鱷的傳奇過程。《最后的農民工》則描繪了一種新型的“外地人”——改革開放后主動流入城市的外地農民——逐漸在青島立足扎根,在改革大潮中同時開始了新的創業。如果把劉耀輝《尋找艾米》中的艾米、張吉宙《爸爸的菜譜》中的谷雨納入視野,這個“外地人家族”甚至可以延伸到第四代——新世紀兒童。“葛晉頌—杜建成—杜滄海/常發財—艾米/谷雨”在某種意義上可視為青島外來移民(一種特殊但又具有普遍性“青島人”)的“家族世系”,它相對完整地記錄了外來的青島建設者們在青島扎根、發展的奮斗歷程,其中凝結的認知、品質組成了“青島精神”的重要版圖。這個“家族世系”是城市發展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些作家把“鏡頭”放低、把眼光放在了并不波瀾壯闊的普通人身上。通過對這些人生活的描寫,作家們對普通青島人的日常生活狀態投去了有力的一瞥,使得近年來青島小說更具概括力、代表性。余耕的《金枝玉葉》寫了一對農村姐妹的成長。兒童文學《尋找艾米》《爸爸的菜譜》,將視角對準了普通的城市外來務工人員。在描寫日常生活方面,艾瑪是一個重要代表,她一貫喜歡關注平凡人的平常生活,其《柚林深處》選取了村民作為表現對象,《看不見的旅程》寫到了保安隊長、四處游走的養蜂人,《島》寫了物業保安夫婦和老漁夫夫婦。長篇小說力作《觀相山》延續了艾瑪的文體風格和取材習慣,她選取居住在青島老城區的一對中年夫妻的日常生活作為“探針”,切入了整個青島普通市民的生活日常。或許從人物的社會身份上來說,這對夫妻并不那么“普通”,丈夫是中學特級教師、妻子是社科學術雜志的副主編,他們更像是一對城市知識分子夫妻。但兩人的生活卻并無多少“知識”的“超脫”色彩,他們在衣食住行、育兒養老、工作事業、家庭經濟等生活各方面的煩惱完全是一般市民的生活常態。借著作者之“觀”,這部小說所展示出來的乃是凡俗人間之“相”。
此外,近年來異軍突起并迅速引起文壇關注的阿占在《墨池記》中還一如既往地關注“化外之人”,塑造了一個精通中醫、武術和書法,并能融會貫通自成一家的國學奇人李可真。阿占通過對李可真一生修煉的回溯,表達了作家對傳統中庸哲學的認同和敬意。普通人是一座城市數量最多、類型最駁雜的居民群體,青島普通人的日常舉動構成了最豐富、最生動的城市生活,他們的精神面貌組成了青島整座城市的整體精神風貌。所以,這些對于普通人的描寫,是寶貴的形象化史料,這種“低姿態”也反映出了作家們的平民立場。
可見,在近年的創作中,青島作家對“青島人”的關注是比較全面但又參差有致的:一是既關注橫向上的多種類型特色,關注到“青島人”是怎么樣的,又有意考察縱向上的歷史演變軌跡,關注到“青島人”是怎么來的;二是既努力去抓主流弄潮的“英雄”,又念念不忘時代角落的“凡人”,關心無人“代言”的市井百姓;三是既關注成人世界的蕪雜,也關注到了兒童世界的復雜。這些刻畫體現了作家們對于“人”的理解和把握非常全面、不拘一格,有著現實主義精神和記錄時代、 探索人生的責任感。
三、“困境”中的“突圍”:深刻的人文關懷
青島作家在跨越百年的歷史視野中觀照“青島”,有家庭/個人奮斗、國家/時代發展、人生困境等多個主題。在眾多主題中,作家往往會聚焦“碰撞”或曰“困境”這種普遍的人生和社會處境,描寫劇變時代人的感情和思想波動,對人的生存境遇表現出了深刻的人文關懷。在此過程中,作家們不僅描繪了一幅“青島人”或者“人”的精神譜系圖,并且給出了自己關于超越或者駕馭“困境”的生存哲思,以正面展示或側面暗示的形式指出了“存在”的“救贖之路”。
傳統與現代的碰撞所造成的困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式現代化偉大實踐本身就是一場劇烈而漫長的“碰撞”,反差越強烈的地帶碰撞越強烈,《雪山大地》寫的是發生在“雙重邊緣”——相對于傳統中原或東部地帶的地理邊緣、文明邊緣——處境中的殊為震撼的文明碰撞:漢族與藏族、內地與邊疆、城市與鄉村、神圣與世俗、外國與中國、歷史與現在和未來。類似的碰撞在東部沿海地區也在發生,而青島尤具代表性。青島是一座開埠較早、土洋交匯的海洋型城市,“舶來”的現代文明與封建傳統的碰撞在這里格外猛烈,人的精神世界遭受嚴峻考驗,或者開悟蛻變,或者崩潰異變。在《遷徙的人》中,魏世瑤關于收音機的玩笑在村民中制造了恐慌,進而引起了貫穿整個故事的巨大悲劇。《島》中,老朽頑固的“父親”固守小漁村,不愿離島上岸,最終被動地變成獨守老屋的孤家寡人。《看不見的旅程》中,吳教授夫妻與兒子兒媳存在溝通障礙,教授夫婦名為浪漫“隱居”,實則無異于孤獨“留守”。傳統與現代的百年“碰撞”,在這些小說中有的體現為城鄉“錯位”,有的體現為代際或族群“鴻溝”,有的體現為空間“偏見”,反映出這種碰撞的普遍性與多樣性,也可看出作家們對社會生活掌控的全面性。
個體與環境的碰撞所造成的困境。所謂“命運”,往往是“個體”與“集體”、“個人”與“環境”的互動軌跡,這些軌跡也進入了青島作家的視野,并表達了自己關于“救贖”的生存哲思。“松濤”是一個雖未真正出場但卻貫穿《觀相山》的悲劇人物,艾瑪通過他的遭遇著重表現出了如“山”般命運的無常、無理與個體的無奈、無力,松濤的“幽靈”在邵瑾夫婦的生活中始終揮之不去,給整部小說蒙上了一層“灰色”。在《墨池記》中,父親用“練字”來磨李可真的“野性”,這是一種“碰撞”;其后,在向師傅松菴、廬老學藝過程中,原有的認知不斷被豐富重塑,又是一種“碰撞”;同時,李可真還要小心翼翼地面對變動的時代環境,又是一種碰撞。在層層碰撞之中,李可真學會了書法、醫術、武功,漸漸體悟到了“甘草”的精神,變得通達平和,成就了自己的中庸圓融之道。《我是夏始之》聚焦當代社會小市民的生存境遇,描寫了他們的窘迫糾結、無力掙扎與苦心孤詣,寫出他們被戲弄的無辜與無奈。兒童文學中,描寫“碰撞”往往是為了烘托“成長”主題。《尋找艾米》沒有選純粹的“農村兒童”或“城市兒童”,而是選擇以從農村進城的“過渡兒童”作為主人公,找到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寫出她在城鄉二元對立碰撞中逐漸成長。于瀟湉的《你在冰原》《雙橙記》《冷湖上的擁抱》《海上飄來你的信》多是雙層結構:表面的探險救援故事是一種現實意義上的“碰撞”,其實深層寓意則是在此過程中主人公與自然、情感困境的搏擊與成長。
理想與現實的碰撞所造成的困境。《觀相山》最著“力”之處便是以不溫不火、毫無“力度”的語言寫出了人對生活的理想向往與難以把握的現實之間的錯位,無論是愛情、工作還是兒女的培養上,女主人公邵瑾的人生就是不斷“退而求其次”、不斷向生活本身妥協。年近半百之際,面對接踵而來的意外沖擊,她表面上與世無爭、隨和的人生態度,實際上不過是在以一種“自我隔離”的方式來維護脆弱的人生的“力學平衡”。理想與現實(道德追求與物質利益)的激烈碰撞突出體現在《最后的農民工》中的常發財身上。從某種意義上來看,常發財可以視為一個“出淤泥而不染”的“圣徒”,他出身悲慘、物質匱乏,但這沒有讓他變成一個唯利是圖的小人。他不止一次“舍利取義”,堅守自己內心純潔無瑕的道德理想并為之作出了生命的獻祭,可能這也是作家最初給這部小說命名為《雪白》的原因。常發財的選擇,可能也是作家本人的選擇;而常發財偶然的悲劇,可能也是現實社會必然的悲哀。
在這些小說中,主人公都在努力追求一種幸福生活,但卻沒有人能夠安穩順遂、問心無愧地得到幸福。這些故事里即便會有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也都擺脫不了濃郁的悲劇色彩。深入地看,這些“碰撞”在很大程度上是“前現代”與“現代”甚至“后現代”的碰撞,或者以之為背景,這些碰撞意味著動蕩、疼痛、破壞,讓身處其中的人在“前進”和“退守”之間徘徊不定,精神無所歸依、肉體無所安放。所以,《島》中提到了父母圍繞宗教信仰而發生的激烈沖突;《看不見的旅程》出現了退休的吳教授夫婦,不僅身體處在沒有煙火氣的城市邊緣別墅區,更重要的是精神也被“邊緣化”了,陷入了孤獨。但辯證地看,這些碰撞同樣意味著交流、改變、新生,所以青島才會吸引大量外來人口尋找機遇,青島人就在百年不斷的碰撞中變得越來越成熟、沉著、包容、“現代”。在一定程度上,“山東”是中國的“縮影”,“青島”則是“山東”的“樣本”,所以青島作家對“青島人”精神浪濤的關注其實也是對“中國人”精神海洋的關注。
四、開放的美學追求:現實主義的“青島味”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現實主義是長盛不衰的洪流,也是近年來文學創作的一股熱潮。在創作中,現實主義既是一種思想傾向,也是一種審美選擇。在青島作家近年來的小說創作中,體現出了以現實主義為中心、富有青島“味道”的多種美學風格,讓“存在”升華為一種美學景觀。
以《雪山大地》為代表的一些作品體現出了一種充滿詩意的現實主義。邊疆奇特的自然環境和少數民族濃郁的文化氛圍讓這部小說在現實主義美學風格基礎上增加了更多詩意的“神光”。以鋪陳、曲折隱喻為特征的藏族式日常對話,穿插全書的藏族民歌和藏地風情,以及隱秘而深入的民族文化影響,使得這部小說厚重的主題和“堅硬”的現實主義變得更為靈活生動而富有浪漫氣質。這種氣質與宏闊的歷史視野、深邃的倫理考辯、高昂的理想主義結合在一起,讓小說成為一部“史詩”。
高建剛在《陀螺大師》中營造出一種神秘莫測、似真似幻的氛圍,以“回憶”的名義回避了對“真實性”的質疑,在虛實參半的敘事中表達了對于“父”的執念和遺憾。與《陀螺大師》的魔幻現實不同,《太平角》所觸及的則是堅硬的現實,它通過一個中年守壩人的不幸經歷與自我重建,表達了對生命意義的理解。在這兩篇小說中,高建剛選取島城人的故事,小切口、大氣象,主人公和故事都不是重大事件,但卻寫出了深度和氣勢。他筆力千鈞,把像海一樣濃郁深厚澎湃的情感和哲思壓縮在精當克制的文字、簡約從容的情節之中,敘事節奏舉重若輕、飽含張力,體現了扎實的浪漫主義美學功力。
楊志軍和于瀟湉的作品指出了海洋敘事的兩個路徑、海洋美學的兩種視角:“陸地上的海”與“海洋中的海”。如果說,從青海遷居青島的楊志軍在一定程度上是以一個“游客”的身份來寫海,他筆下的“海”是“站在陸地上看過去的”海、“海”作為一種“觀賞物”、一個“他者”得到呈現,“觀滄海”讓人-海之間帶有一些審美距離的話,那么于瀟湉的涉海寫作則是以一種“家人”的身份來呈現融入自己成長經歷的“生命成分”,她的海是“深入海中的海”、“自我”的一部分,“探深海”極大弱化了人-海之間的隔膜感。
楊志軍的海洋美學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敘述中大量的海洋風景描繪,作家在書中以非常欣賞的筆觸描寫海洋,海洋風景描寫或者優美活潑,或者沉穩壯闊,但都是可愛、可敬而非可惡、可怕的;二是在情節上的海洋敘事力學,海洋風景描寫中往往夾雜著大量的情感和哲思,這些“借景抒情”展露了主角們的心路歷程、影響了故事的發展,而且海洋還會直接介入來影響情節走向;三是在思想層面體現了一種“由陸向海”的文明認知,加深了海洋美學的思想深度。一個有趣的視角是,如果考慮到土生土長的青島作家于瀟湉的《冷湖上的擁抱》是以高原戈壁為背景的話,則會發現這兩個作家之間形成一種奇妙的對話:于瀟湉以海濱子弟身份(“海的女兒”)寫西部高原,楊志軍以高原子弟身份(“雪山之子”)寫東方大海。彼此眼中的“大海”與“高原”可以形成復雜的對話:“高原”“大海”到底意味著什么?“高原”“大海”可以有什么樣的美學可能?這種交互凝思的對比視角,也許可以進一步打開海洋敘事美學的思考空間。
阿占在不同風格之間游刃自如,反映出她良好的文學感覺和深厚的語言功力。《墨池記》略帶古樸澀味,體現出幽雅神秘而又端莊高妙的古典傳奇美學;《孤島和春天》的語言細膩而利落,密集的短句營造出一種生動的“講述感”“現場感”,文字的“情緒含量”高,屬于一種雅化了的“說書”風格,有雅俗共賞之效;《貓什么都知道》有鮮明的女性視角敘事特色,語言雖然生動,但整體氣氛卻偏于壓抑、煩躁,有現代、后現代都市文學的影子;《后海》則著眼更為廣闊,有明顯的家族敘事、城市史敘事傾向,吐露出進一步拓寬自己文字表現域的跡象。
艾瑪的《島》《柚林深處》《看不見的旅程》《觀相山》語言和故事一樣樸素、尋常,情感平和節制,敘述節奏舒緩自然,體現出古樸沖淡的美學風格。余耕的《我是夏始之》全書雜糅了優雅裕如的古典、冷靜深刻的現代、狂躁荒誕的后現代、回環往復的懸疑等多種美學風格。此外,像余耕的《做局人》聚焦騙局,從一個新奇的角度反思了社會的病癥,《最后的地平線》則從他自己的從警經歷中汲取素材靈感,這兩部小說角度新奇、可讀性強,也體現出了一種現代都市通俗美學。連諫的《遷徙的人》《你好,1978》《昨日之謎》敘事節奏明快,故事性強,情感糾葛復雜而充滿戲劇性,體現出輕快刺激的通俗市民美學。
米蘭·昆德拉說,現代小說“探索人的具體生活,保護這一具體生活逃過‘對存在的遺忘,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a。近年來青島作家以小說的方式凝視、諦視、審視腳下的土地、身邊的人民,在創作中表現出了開闊的時空視野、搭建了多彩的人物畫廊、表達了深刻的人文關懷、體現了開放的美學追求,“照亮”了一片多維多層的“生活世界”。如果將中國當代文學比作海洋,那這些作品就像“在天風海水的浩蕩中迸躍出一線青潮”(王統照),既有大情懷,可以跳出自身觀國族歷史(整體式存在),又有小悲憫,能夠關注小人物的小人生(個別化存在),就像是“波濤”和“浪花”,反映著中國式現代化大潮的波瀾壯闊。
注釋:
a[捷]米蘭·昆德拉著,董強譯:《小說的藝術》,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6頁。
(作者單位: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