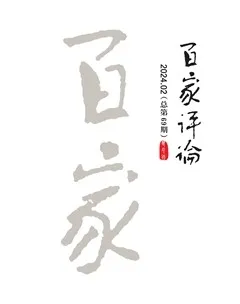喬洪濤創作藝術論
程相崧
內容提要:喬洪濤是活躍在山東乃至全國文壇的一位實力作家,近年來一直保持著穩定而旺盛的創作力。他擅長小說和散文創作,并且兩種文體的作品都數量大,質量高。他思考深邃,筆觸細膩,敘述風格借鑒西方技巧又不失傳統文學的厚重大氣。本文試圖以喬洪濤受到廣泛關注和贊譽的部分小說、散文文本為例,梳理他20多年的創作歷程,分析其在所擅長的小說和散文兩種主要文體上,藝術方面所做的探索和所取得的成績。
關鍵詞:喬洪濤 散文 小說 敘事藝術 人物塑造 自然文學
喬洪濤自世紀之初步入文壇之后,一直保持著穩定而旺盛的創作力,以其高質量的小說和散文作品,已經成為活躍在山東乃至全國文壇的一位實力作家。他思考深邃,筆觸細膩,敘述風格借鑒西方技巧又不失傳統文學的厚重大氣。在經過對自然、社會、人生的深刻觀察之后,創作出了像小說《少年兩匹馬》《騎白馬,扛梅花》《蝴蝶》《一家之主》《一個人的盛宴》,散文《湖邊書》《大地筆記》《紙與字》等一大批深受讀者喜愛,又在文學圈和評論界引起一定反響的精品力作。這些作品,有的在敘事上獨具匠心,有的在人物上頗具功力,有的顯示出作家對于平庸生活、復雜人性的深刻洞察,呈現出深刻而獨特的思想內涵,并取得了較高的藝術造詣。
喬洪濤跟很多年輕作者不同的是,自從步入文壇之初,即以小說和散文兩種文體引起了不同類型讀者的關注。他的創作,可以在兩種不同的文體之間自由跳躍。從早期發表在《散文》上的《鐮刀的婚禮》、入選《散文選刊》《散文海外版》的《蘆葦》《緩慢》等散文開始,到近期發表在《福建文學》的《紙與字》;喬洪濤的散文起點高,質量優,在名家輩出、流派紛呈的山東散文界,也因為其呈現出的自然文學、非虛構、哲思風格和文化含量而風格鮮明,十分扎眼。他的小說,從早期發表在《清明》上的《尖子生》、《中國作家》上的《老師、老師》,到近年創作發表的短篇小說《飲鴿記》《騎白馬,扛梅花》、收入小說集《一家之主》《一個人的盛宴》中的諸多篇什,以及長篇小說《蝴蝶谷》,都顯示出喬洪濤作為一個小說家,不僅高產,而且高質;并隨著生活閱歷、閱讀積累的逐漸深入,已經能夠熟練掌握小說文體,創作風格逐步形成,創作狀態也漸入佳境。
本文試圖以喬洪濤受到廣泛關注和贊譽的一些小說散文文本為例,梳理他20多年的創作過程,分析他在所擅長的兩種主要文體上藝術方面所做的探索和所取得的成績。著名作家張煒有一個觀點:“一個糟糕的小說作者不太可能會是一個高明的散文家,反過來也一樣。”所以,本文也試圖對作為兩屆“張煒工作室高研班學員”的喬洪濤能夠熟練掌握小說和散文兩種文體,這一當代文壇并不多見的現象,探討兩種文體趨近求同的途徑和一個作家具備兩種能力的必要。
一、小說論
喬洪濤作為生長在齊魯大地上的作家,他剛剛步入文壇時的創作,多取材于兒時生活過的鄉村留下的深刻記憶,寫作方法也繼承了這片土地上老一輩作家身上的厚重樸實。他早期獲得關注的作品,例如小說《西北望蒲葦》《鄉村火槍手》《紅鯉》《吹豬》《賽火車》等,大多取材自己熟悉的鄉村生活,文字洗練,風格樸實。他善于通過細節描寫,來展現人物的性格特點和心理變化,使得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躍然紙上。另外,他還擅長通過對人性復雜性的挖掘,使人物形象更加全面、立體。
當然,小說是敘事的藝術。自從西方小說敘事學傳入中國之后,小說寫作在眾多作家的眼里,“怎么寫”的重要性一度遠遠超過了“寫什么”,成為寫作水平高低、寫得高級不高級的衡量標準。在喬洪濤剛剛步入文壇的時候,雖然有批評家指出,其小說當時寫得還顯太過“老實”,但在敘事上,他也已經在傳統的基礎上,試圖做出種種嘗試,并形成了保持多年的藝術特點。
他那時的小說,在敘事上開始多用第一人稱的敘事視角。這不僅增強了敘述內容給人的真實感,還便于傳達出小說中人物隱秘的內心世界,能夠增強小說人物與讀者心靈之間的同頻共振。這種敘述習慣,一直延續到后來的《三個男人》《我家的電視機》《鯨》等小說。第一人稱的敘事視角將讀者帶入的,不管是充滿生活氣息的家庭環境,還是有些荒誕變形的虛擬世界,都給人一種撲面而來的真實質感。
在第一人稱敘事的同時,喬洪濤的小說往往又喜歡采用童年視角。這一視角的使用,讓讀者看到一個新奇別樣的世界,容易獲得非同尋常的閱讀體驗。在《少年兩匹馬》和《騎白馬,扛梅花》中,喬洪濤便是通過幾個少年的成長經歷,來探討人生的意義和價值。這兩部小說中的少年形象都充滿了活力和朝氣,他們在大自然中奔跑、嬉戲,感受著生活的美好和純真。然而,隨著年歲的增長,他們不得不逐漸面臨著生活的壓力和挑戰,開始思考人生更深層次的意義和價值。
如果說喬洪濤的小說在敘事上前后最大的變化,則是由宣泄變得更為克制,擯棄了鋪張的敘述而轉為極簡的刻畫和呈現。我們在讀他前期的小說時,不論是《西北望蒲葦》中如詩如畫故鄉風物的描寫,還是《故鄉謠》《捕鯉記》中農村風俗的交待,都不吝筆墨,讓讀者眼前似乎緩緩展開一幅生機勃勃、草木豐茂、人歡馬跳、民俗獨特的鄉土畫卷。那個位于魯西北黃河岸邊的小小村莊留在作家腦海中的記憶,似乎不由地就要進入作家的小說世界,成為人物活動,故事生長的強大背景。這種寫法給喬洪濤當時的小說帶來一種濃郁強烈的生活氣息,使其作品風格厚重大氣,閱讀體驗莊重震撼。這也讓他當時的一些小說尤其是中篇小說,比如《空地》《每一個人的秘密》《鵝鵝鵝》等脫穎而出,在讀者和文學圈獲得了一定的反響。
但是,隨著作家生活環境的變化和寫作興趣逐漸轉向短篇小說創作,面對新的寫作題材,面對小說創作領域審美趨向的不斷變化,這種敘事方式日漸顯露出其“短板”。著名小說家劉照如在2018年前后就曾經指出:喬洪濤的一些小說在對所寫題材的“控制能力”上,稍顯無力和疲態。那個時期的喬洪濤,在創作上一度陷入難以逾越的苦惱“瓶頸”。但是很快,他就突破自我,完成了其在敘述風格和方式上的嬗變過程。從《湖水冰涼》《百年好合》《潛水家》和《在山上捉野雞是一件危險的事》開始,喬洪濤的短篇小說給讀者帶來的閱讀體驗大變。這些小說不僅削減了作家之前為之著迷的不節制的景物描寫和情緒宣泄,場景的呈現替代了曾經得心應手的敘述和交待,在情節切入時也往往單刀直入。在這些小說中,作家善于用簡潔明快的句子來描繪場景,刻畫人物,使得整個故事節奏緊湊、引人入勝。讀者的閱讀體驗也為之一變——如同看一個招數日漸嫻熟的武者左右突擊,奪敵兵器,取敵首級,如入無人之境。
喬洪濤后來的很多小說,不論是中短篇還是長篇,情節往往充滿張力,故事發展緊湊,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不得不保持著精神的緊迫感。他的長篇小說《蝴蝶谷》中的白冰初到蝴蝶谷所受到的熱情款待,便讓讀者心生疑竇,并為后面情節的發展埋下伏筆。他的一些短篇小說,又擅長利用“突轉”的手法,讓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感受到強烈的戲劇性和張力。這些轉折往往出人意料,但又合情合理,使得故事更具吸引力。例如在小說《潛水家》中,寫了一個不擅長農活卻擅長游泳的農民父親熱衷鄉村游戲比賽最后遁入湖底消失的故事,通過突轉,隱藏在人性中的微妙細節得以呈現。例如在《一個人的盛宴》中,寫了一對貧窮的鄉村夫妻在兒子入獄后的精神崩潰,把當今鄉野極端生活中人們的生存困境和男人的精神危機和盤托出。例如《少年兩匹馬》中的白馬自殺而死,紅馬失蹤消失的結局,而小說《我家的電視機》的結尾出現的小紅點和朝著我走來的電視機,則更是以一種真實與魔幻結合的出奇方式,崢嶸突起,意外之中,帶給人的心靈一種震撼的力量。
喬洪濤曾經一度推崇美國作家海明威的冰山理論,并為小說《白象似的群山》而著迷。近年來,短篇小說大師卡佛的作品,也因為其極簡而被很多作家和讀者追捧。其實,極簡也是中國傳統美學所崇尚的風格特色。中國的詩和畫一向講究留白,藝術大師往往都是留白的大師,方寸之地亦顯天地之寬。這種有意的“留白”,也大大拓展了喬洪濤小說的敘述空間,讓他的小說變得更加耐人尋味,更有嚼頭。
例如其小說《風雨二題》《被雪覆蓋的男人》,作家對小說中主人公的經歷和遭遇,有意進行了淡化和模糊化處理,甚至大量留白。這樣不但豐富了小說的意蘊,還讓讀者不得不參與其中,獲得非同尋常的閱讀體驗。當然,喬洪濤深諳留白的魅力,所以他的小說,有的地方描寫密不透風,有的地方又疏可走馬。他在小說《鯨》中對于主人公生存困境,對于他生活小區庸常瑣屑生存環境的描寫,又不吝筆墨,故意地鋪張到了極致。
讀喬洪濤近年來的小說創作,很難用傳統的“深度”“廣度”概括其寫作追求,他似乎正在一次次挑戰小說尤其是短篇小說創作的“難度”。他在很多小說中開始運用意象、隱喻、象征等修辭手法來深化主題,使得作品具有更加豐富的內涵和意蘊。其短篇小說《蝴蝶》中的“蝴蝶”、《風雨二題》中的“風雨”,《被雪覆蓋的男人》中的“雪”、《鯨》中的“鯨”,還有《騎白馬,扛梅花》中的“梅花”,作為一個個意象,無疑都超出了現實的層面,而具有了象征與隱喻的意味。再例如長篇小說《蝴蝶谷》中的“蝴蝶谷”,作為一種意象和隱喻,無疑暗示了現代社會中人們心靈的困境和追求自由的渴望。這一意象的選用,也深化了小說的主題,將讀者引入關于人性和自然的哲學思考。正如古人所說,言不盡意,語言在現實的無限豐饒面前,往往表現出其有限性。喬洪濤在處理這些題材的時候,就會借用一些意象,委婉含蓄,也是舉重若輕地把心中的意思表達出來。這些手法的綜合運用,拓展了作品的思想內涵,也讓作品在藝術上,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喬洪濤早期的小說重在寫實,近年來則多寫得輕靈飛動,舉重若輕,并呈現出更多的當代性和實驗性。他的兩篇短篇新作《鯨》和《我家的電視機》,語言簡練,敘述風格冷峻;以略顯破碎的情節、濃得化不開的細節、蒙太奇的剪接、意象的象征與隱喻和奇崛有力的結尾處理,深刻揭示了當代人的生存困境。其小說人物身上所透露出的那種精神的孤獨,絕望;親情、友情、愛情和人際關系的那種疏淡,隔膜,無不給人以震撼的力量。
小說作為一種古老但也在不斷成長的文體,可以一板一眼地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可以將八分之一的冰山露在水面以上。當然,也可以通過對有韻律與節奏的語言的把握,對環境、氣氛的釀造,甚至通過對情感的看似廢話連篇的宣泄,使其表現嚴肅的主題,揭示生活的真相,并呈現出獨特的形式。正如奈保爾所言:“如果把小說寫得太像小說,只能將小說寫作推向一條羊腸小道,甚至逼上一條絕路。”而作家喬洪濤作為永不滿足的探索者,正在以自己的不斷探索,將小說寫作這條路越走越寬。
二、散文論
如果說喬洪濤的小說運用多種藝術手法,以其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復雜多樣的內心世界、動人心魄的矛盾沖突來反映幽微的人性、多樣的生活;那么他的散文則多以細膩的筆觸描寫鄉村和山野的風物,描寫四季的物候和身邊的尋常事物,展現出一幅幅充滿生活氣息的畫卷。他的散文有鮮明的“自然文學”特點,又富有場景的代入感,能夠讓讀者暫時拋開城市生活的喧囂,進入一種寧靜的世界、一個充滿詩意的世界,與山川草木同呼吸,共命運。作為散文家的喬洪濤,不僅僅是一個自然的講述者,更是一個思想者。他通過對大自然和身邊事物的深入挖掘,探討了生命的意義、人心的變化、社會的變遷等深刻主題,富有哲理性和思想性。他的散文作品相對小說,雖然數量少很多,但都能夠啟迪讀者,引發人們對生活和社會的深度思考。
在喬洪濤早期的散文《蘆葦》《聽秋》《雨水與驚蟄》等篇什中,出現在作者筆端的是鐮刀、蘆葦等鄉村司空見慣的器物、植物;還有雨水、驚蟄等季節和節氣。那時候的喬洪濤,像一個雙腳踏在齊魯大地上的歌者,對這片土地充滿了眷戀和感恩。在這些散文里,他的語言優美而富有詩意,擅長運用比喻、擬人等修辭手法,來逼真地描繪記憶中的事物,富有感染力。在對自己熟悉的農村生活場景和農人勞動場面的細膩描寫間,常常表達對鄉土生活、鄉村生活習慣的思考,對自然與人關系的思考,并對昔日的鄉村,由衷地流露出熱愛與眷戀。
喬洪濤這一個時期的散文,雖然已經呈現出“自然文學”的特征,但畢竟還有些表面化、浮淺化。“自然文學”作為一個學術名詞,雖然來自西方學界,并因為《瓦爾登湖》等作品在中國的暢銷而為人熟知,可它在中國卻是古已有之,源遠流長。唐宋之后久盛不衰的山水田園詩當然是幾近成熟的“自然文學”,如果要向上追溯的話,還可以追溯到陶淵明和《詩經》中大量寫到山野和鄉村的詩歌。作為“自然文學”,僅僅去描寫甚至復制自然是不夠的,僅僅是贊美和眷戀自然也是不夠的。如何與大自然相擁生活,如何從大自然中獲得滋養,如何把在自然中得到的感悟轉化為精神的升華,自然要成為作家們思考的一個課題。
在散文寫作方面,喬洪濤自然也不甘心一直描寫一些瑣碎的鄉村風物、山石物候,他是把自然當作一種隱喻的神性存在來看待的。所以,他的散文到了《大地筆記》和《湖邊書》系列,再次發生了一次飛躍,無論是思想和藝術方面,都明顯地上了一個臺階。在《大地筆記》中,喬洪濤將筆觸延伸到了更廣闊的大地之上。他所描寫的對象,并沒有超越大多數散文家,甚至也沒有超越他以前散文所涉及的范疇。可是,在這兩個大部頭中,大地和湖泊已經不單單是一個現實的存在,他們既是四季輪回、生生不息的現實世界,又成為一個精神的隱喻和寄托。喬洪濤作為大地和湖泊的觀察者、記錄者和思考者,正試圖透過真實逼人的現實世界,去揭示大自然的奧秘和人生的真諦,去表達對生命的熱愛和對人生的獨特見解。
在《湖邊書》中,喬洪濤的語言簡潔而富有詩意,平實而不失感染力。他以湖為背景,通過細膩的筆觸描繪了湖水的波光粼粼、湖岸的草木蔥蘢,極具畫面感和視覺效果。他的描寫,常常讓人想起理查德·杰弗里斯筆下的英格蘭鄉村,或者蘇珊·庫珀的《鄉村時光》中描繪過的場景。而跟他們兩個稍有不同的是,喬洪濤的散文更加注重情感表達和哲理思考。《湖邊書》中的一些片段,往往以日常生活為背景,通過抒發對自然、人生和社會的感悟,傳遞出一種深沉而真摯的情感。這讓我們在字里行間,不僅可以感受到作者對生活的熱愛和對自然的敬畏,也可以領略到他對人生的獨特見解和對社會的深刻洞察。
跟梭羅筆下的“瓦爾登湖”和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一樣,在喬洪濤的筆下,大地、湖泊、風暴早已經超越了自然的存在,而成為一個充滿哲理和詩意的象征。收入《湖邊書》中的一篇《荒野風暴》,就寫了蒙山腳下、云蒙湖邊的風景和人們的生存狀態。一群“都市人”在湖邊扎上帳篷,釣魚,打鳥,生火,做飯。最后,當他們喝了從城里帶來的白酒、葡萄酒之后,感到“睡在大地上,比睡在床上的踏實感來得強烈得多。”他們逃離了城市的喧囂,逃離了工作的煩惱,甚至感覺自己的耳朵比任何時候都靈敏,甚至想象著“一只屎殼郎推著糞球走過,一只螞蟻悄悄爬過,一條蚯蚓在身子下輕輕蠕動,一只田鼠在五米開外躡手躡腳,一條魚兒跳起偷瞧過來的眼波,還有鳥雀半夜的囈語,鳴蟬振翅的微顫……”
這些遠離自然又向往自然的“都市人”似乎已經融入荒野,完全成了這個曠野的一部分。可散文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噼里啪啦的雨水滴落下來”之后,這群孱弱的“都市人”卻收起帳篷,逃入湖邊的木屋。這些人回到木屋之后,感到“一點困意也沒有了,都感受到了自然的威力——”隨之,他們又本性復燃,開始矯情地擔心起風雨中的鳥雀、田鼠甚至螞蟻。但是,“沉沉的困意襲來”, 這群渴望著親近自然的人,卻終于“倒在木板床和椅子上又睡去了……”
喬洪濤的散文元素是多元的,在《湖邊書》中,既有寫實性,又有寓言性;既有都市人孤獨心靈的囈語,又有人與自然歡欣的互動。這也是喬洪濤的《荒野風暴》和常見散文不一樣的地方。散文的開頭,看似一段并不簡潔的鋪墊,但是,風景是動人的,抒情也是動人的。令人驚喜的是,這些風景和抒情,又不是簡單的風景和抒情。散文中的人、鳥、魚、荒野、云蒙湖,這些在作者的筆下,都具有了神秘性、符號性,都成了一個個鮮活靈動的“象征”。在作者的筆下,萬物是有靈的,作者的主觀世界無限地接近了客觀世界;他筆下的山川、溪流、鯉魚、麻雀、甚至一只屎殼郎,都具有了人的主觀意志和生命體驗。這些元氣淋漓的生命符號,將都市人的焦慮、無助、弱小、卑微、瑣屑映照得無處遁形。
散文《荒野風暴》對當代都市人的生存困境,有著入木三分的認識,并懷著深深的憂慮。這些游走于大自然中的“都市人”,已經不是屠格涅夫《獵人筆記》中所寫的俄羅斯大地上行走于西伯利亞莽林中的那些健美、自信的農夫和獵手。他們仿佛被都市文明閹割了,也被都市生存法則完全打敗了。他們對于自然的親近,也不再是那種威猛精進,而是帶著一種隔靴搔癢、顧影自憐和自欺欺人。
作者對傍晚湖邊的“我”,曾有過這樣的心理描寫:“在城市里,我們害怕火。但也離不開火。為了驅趕寂寞,帶來生命的安全感,每個人嘴上都叼著煙卷,四處走。”在散文的末尾,作者又借“我”之口,發出了這樣的批判:“這就是荒野的法則。一個人對荒野的渴慕,就是對變幻無常的法則的渴慕,就是對人類過分秩序的厭倦。”
喬洪濤作為一位遠離世態喧囂的寫作者,在對中國傳統鄉村生活長期關注的同時,又在有意識地體察都市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局。在以《大地筆記》和《湖邊書》為代表的一組“大散文”中,他善于運用象征、隱喻等手法,通過形象的比喻和巧妙的構思,增強了作品的藝術性和感染力。當然,在這類題材之外,喬洪濤也有一些以悲憫情懷反映底層人生活的散文,多是通過他們的生活經歷和命運波折,展現出人性的善良與悲涼。其人性的關懷和悲憫的情懷,讓人感到溫暖和感動。
總之,喬洪濤的大多數散文,結構嚴謹而不失靈活性,語言質樸而不失詩意;綜合運用了象征與隱喻,展現了他獨特的藝術探索和深刻的人文思考,贏得了廣大讀者的喜愛和文學界的認可。
結語
著名作家張煒曾經說:“就小說家而言,他所倚仗的最基本能力,還是從小時候學習的散文寫作的能力。因為小說中的大多數篇幅都在敘述事情,這就需要一種生動簡約的表述功夫。”在喬洪濤的創作中,小說與散文并不是截然分開的。雖然在小說與散文創作方面,他分別進行了不同的探索和嘗試,作品也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和風格,但它們之間卻有著密切的聯系和交融之美。喬洪濤的小說中融入了散文的抒情性和哲理性,使得小說更加具有詩意和深度;他的散文中則融入了小說的情節性、敘事性和故事性,運用小說設置人物和場景的技巧,使得散文更加生動形象、更加抓人。
喬洪濤曾經一度關注“非虛構”這一文體,并極為推崇;可在他的散文中,卻也有時借助甚至“虛構”一些人物的親身經歷,通過人物的“所見所聞”,來抒發情感、表達思考。這種敘事方式,不僅增強了散文的感染力,也使得散文更加具有可讀性和趣味性。就像《荒野風暴》中的那些城里人和他們的荒野經歷,因為借鑒了小說的寫法,常常讓人聯想到屠格涅夫的小說《獵人筆記》中的人物。
有趣的是,喬洪濤的《湖邊書》系列,和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一樣,有著寫實的油畫質感;但不同的是,在云蒙湖邊的木屋里喝著葡萄酒的這群城里人,已經再也不能跟屠格涅夫筆下打松雞、打野豬的獵人那樣,跟風景真正地融為一體。這些在物質生活上無憂無慮的都市人,心靈卻是蒼白的,生活卻是單調的,他們幻想著融入自然,融入荒野,具有像大自然一樣的蠻荒之力,但最終卻在大自然的威力下,一個個顯露原形。這大概也是喬洪濤在這個文本中所要表達的焦慮和洞察。
總之,無論是那些以鄉土為背景、以人性為主題,注重人物形象塑造與內心世界挖掘的小說,還是那些以大地和湖泊為對象、表達對自然的敬畏和對人類命運思考的散文,都無不包含著作家喬洪濤對于自然、人生、社會問題的思考,也無不體現出他對各種藝術手法的嘗試和探索。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朝著文學高峰不斷攀登的作家喬洪濤,在將來一定會創作出具有更加豐厚文學底蘊和獨特藝術魅力的文學作品,奉獻給讀者。
(作者系山東省作協第六批簽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