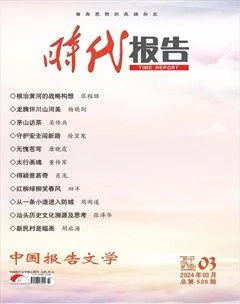太行畫魂
何海闊端坐在壁立千仞、蒼茫孤寂的青峰頂上,手握畫筆,眼睛俯瞰著綿綿延延、起起伏伏的太行山脈,像一臺精密的透視器,像一只目光敏銳的鷹,穿越太行山的肌體,尋覓太行山的魂魄。
倏地,他覺得眼前的山體在晃動、在行走、在漂移,那高高聳立的山峰在藍天白云下揮舞,錯落有致的山體露出了燦爛的微笑,長在山崖間的松柏樹林、花花草草、根根系系,每一個紋理、每一瓣花香、每一根脈絡,越來越清晰靈動、越來越親切鮮活,太行山突然活起來了。
何海闊瞬間有了神機靈感,有了神秘的力量,拿起畫筆唰唰唰,時而緩緩有序、韻墨思量,時而行云流水、濃墨著筆。隨著山峰舞動,隨著山體微笑,太行山隨著他的筆韻而生色,隨著他的思想而鮮活。
“那山那水那座峰,那花那草那棵樹,仿佛變得有情有感,有血有肉了,我仿佛找到了太行山之魂。”
數小時后,何海闊終于創作完成了后來被命名《南太行看山》的中國畫。
那時那刻,他汗流浹背,氣息粗促,久久不能平靜,激動地說:“那一刻,我與太行山融在一起,在太行山的血脈里奔騰流動……”
何海闊是一個癡迷于畫太行的畫家,一個與太行山融在一起的畫者。
游心太行
何海闊出生于開封杞縣,一望無際的豫東平原,承載著黃河古道的厚重和曠達。他從小喜歡涂涂抹抹、寫寫畫畫,經常亂寫胡畫些花花草草、山川河流,顯得笨拙自然,童心逗趣。
何海闊到河南師范大學美術系之前,準確地說,在來到太行山腳下的新鄉之前,何海闊并沒有見過山,眼的世界里裝滿了遼闊空曠的田地,奔騰不息的黃河,四通八達的公路。
此時,他根本不知道山在哪里,山的模樣,山的性格。
何海闊對山的尊崇和向往,源于五代后梁的著名畫家、太行山水畫派之祖荊浩。
上大學期間,何海闊被荊浩“有筆有墨,水暈墨章”的畫風韻味深深吸引,尤其是荊浩在太行山隱居時,所作的傳世之作《匡廬圖》展露出的雄偉氣勢最讓他著魔。
那是一個深秋時節,何海闊背著行囊和畫筆,孤身一人出發了,他要去攀登那座山,在他心中醞釀很久、珍藏了很久的那座山,于是,他帶著敬畏和朝圣般的心出發了。
他說:“山,是畫者的領地;山,是畫家的歸宿。”
那時候,他還不懂得山,不知道山的方位,山的方向。他到汽車站怯怯地問乘務員:“太行山在哪兒?我想去。”
年輕漂亮的乘務員看著冒冒失失的小伙子,背著畫夾和背囊,笑著說:“先坐輝縣的車,到那兒再打聽吧!”
就這樣,何海闊擠上了一輛破舊的公共汽車,向西,向西,向著太行山的方向,一路灰塵,一路顛簸,一路問路,到達離太行山最近的鄉鎮——上八里鎮,已是下午兩點。
此地,公路已是盡頭,要想上山,必須乘坐農用三輪車。何海闊有點饑餓,有點沮喪,望著眼前高高的太行山,他只有一個信念:登上太行山,看山的風景。
何海闊在鎮上小飯店里點了一碗湯面條,把從學校食堂買的饃饃,掰成塊泡在碗里,囫圇吞棗地吃了起來。
吃完飯,背著行囊,夾著畫夾,坐在當地人叫“奔奔”的三輪車上,沿著崎嶇的羊腸小道,左拐右拐,前擁后顛,穿梭在懸崖峭壁間。
何海闊第一次進山,行走在陌生的太行山里,顯得恐慌緊張,提心吊膽,雙手牢牢抓住車幫,隨著車身顛簸晃動,像在車上“扭秧歌”。
車到回龍村時,太陽已西下,何海闊仰頭遙望恰是五指的山峰,山體遮蔽了太陽,五彩的光線穿過云霧直射在另一座山峰上,秋色染成的七彩花草樹木,在太陽光的照耀下熠熠生光、美輪美奐,構成無與倫比的太行風景圖畫,這一圖景一直定格在他的心中。
“走,還是不走?爬,還是不爬?”何海闊在欣賞美景,陶醉之時,他猶豫了,有種停下來的想法。
熱心的山民們說:“太行山最精彩的地方在老爺頂,最高的地方在十字嶺,去這兩個地方最少得爬5個多小時山路絕壁,太行山黑得早,爬山走夜路很危險……”
“作為一名畫者,一個將與山水畫相伴一生的畫者,就意味著要堅持與攀登,這次也算對自己意志的考驗吧!”
何海闊猛抽兩口煙,把煙蒂朝鞋底一撮,下決心獨登太行山,夜走懸崖路。
“山再高,高不過我的意志。天黑了,我就點起心中那盞燈吧!”
山,代表著某種高度;山,考驗著何海闊的意志。
何海闊沿著卵石橫亙、溪溪潺流的河道行走,深一腳淺一腳,左顧右盼,蹦蹦跳跳,像太行獼猴那樣。
走過回龍小村,穿越河道就是崎嶇的羊腸小道,彎彎曲曲沿著山體溝壑順勢而上,3尺寬小道已踩出路的模樣,腳下的巖石已折射出光影,旁邊的小樹已被拽歪,樹皮已油光發亮。
何海闊驚訝不已,山里的樹咋長這樣?
后來,他驚奇發現,這是時光的打磨,山民的生活。
他沿著小道延伸的方向,彎著腰,蹬著腿,一手抱著畫夾,一手拽著樹藤,手腳并用艱難爬行,每走一步氣喘吁吁、咳嗽不止。累了,躺在巖石上稍歇一會兒;渴了,就趴在小溪旁喝口山泉水。
不知不覺太陽落山了,天色暗淡下來,空曠的大山里只有何海闊在行走,借著夜光,加快步伐,頭頂的烏鴉“哇哇”叫得瘆人,遠處的野豬“嗷嗷”叫得令人恐慌,腳跟前的野兔松鼠四處亂躥,何海闊頓覺汗毛豎起,后背發涼……
他拿出手電筒,朝著天空晃動幾下,大聲地吼了幾聲,唱著歌聲繼續爬行,他為自己壯膽,也告訴野生動物,這里有人,請為我加油。
漆黑的夜晚,何海闊一路驚恐,一路摸索,一路爬行,跌倒了自己爬起來,臉被樹枝刮出血……
3個多小時后,何海闊看到懸崖絕壁處有一處燈光,頓時激動起來,順著燈光的方向匆匆跑去。
“有人嗎?”
他來到絕壁下的山龕,見是一座寺廟,就急忙敲門喊人。
“孩子,你怎么半夜來燒香啊!”
一個守廟的老人打開門,端詳著滿臉是血的何海闊說:“孩子,你咋成這樣了,快進來廟里吧!”
得知何海闊第一次進山,是來畫畫的,老人急忙生火做飯,做了一碗熱騰騰的湯面條,早已饑腸轆轆的他,狼吞虎咽地吃了起來。
第二天,天剛蒙蒙發亮,何海闊繼續爬行,這次要爬越200多米的懸崖絕壁。善良的老人害怕何海闊從“3尺寬”的天梯摔下,主動陪他爬天梯、走絕壁、穿隧洞、行天門,跨青峰關,登千臺階,翻山越嶺,攀上青峰頂,一路護送,一路攙扶,一路講述著太行山的故事。
中午時分,何海闊登上了海拔1570多米的天界山。
這是一座孤零零的山峰,叫紫團巍,或青峰頂,建于隋朝,興于明朝。相傳,道教祖師玄武曾在山頂修行,乘紫色云團在太行隱居行走,42年后成仙,故稱“老爺頂”,是著名的道教圣地,因與武當山南頂相對峙,故有“南金頂,北鐵頂,南頂在武當,北頂在太行”之說。明萬歷年間,吏部尚書李戴修天梯,建道觀,萬歷皇帝曾贈真武廟道藏經。
何海闊站在天界山極頂,仿佛進入人間仙境,眼前一片空曠,深不見底的峽谷,飄著朵朵白云,四周遠眺,群峰壁立,峰巒疊嶂,山山依偎,峰峰拱手,有一種“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感覺,如一幅幅如詩如畫的卷軸極為震撼。
他不顧饑餓疲憊,支起畫架,弄好筆墨,攤開畫夾,變換著不同姿勢,環視遠山與群峰,揮舞畫筆唰唰地畫了起來,一小時、兩小時、三小時……忘記塵俗、忘記時空、忘記一切。
他像一個精神極度饑餓的孩子,毫無顧忌地汲取著天地間的精華和營養,讓山的魂魄、水的感覺、他的思想,融化筆墨,融入畫中,融合藝術。
在天界山峰上,如饑似渴地畫了3天,10多幅“杰作”掛在真武廟的大殿,認真端詳、自我欣賞,然而,他張張不滿意、筆筆不如意,從入墨勾筆到水暈染墨,從山水景象到構造意境,從畫風畫面到氣韻氣勢,畫中沒有想象中的太行風骨、山水風韻,藝術風格。
老僧人走過去仔細閱讀后,搖搖頭微笑著說:“你的畫,畫山是山,畫水如水,沒有畫出太行風骨、太行之魂。”老僧人拍拍他的肩膀,風一樣地走了。
老僧人一句話點醒了何海闊。
何海闊愣住了,心中有那種山,但畫不出那種山的樣子,找不到魂的感覺。
望著層層疊巒的太行山峰,他自言自語說:“難怪有一種參悟不透、讀不懂太行山的感覺。”
太行山之魂在哪兒?
覓魂太行
太行覓魂,魂在何處?
何海闊從太行山歸來,仿佛大病一場,那是一場精神虛脫,從信仰崇拜到喪失自信,從癡迷追隨到失望絕望,甚至懷疑自己沒有畫畫的天賦,不是畫太行的料兒。
“應該像山那樣思考。”美國作家利奧波德說。
當何海闊讀到這句話時,頓悟了,醒了。
像山那樣思考,像太行山那樣存在,像太行山水畫派之祖荊浩那樣的畫風思想,那就是太行之魂,那就是太行畫魂。
何海闊背起行囊又出發了,這次是朝圣之旅、覓魂之行。
荊浩,五代后梁畫家,被后世尊為北方山水畫派之祖,因避戰亂,常年隱居太行山的林濾山洪谷,畫出了傳世名畫《匡廬圖》《雪景山水圖》等,著有《筆法記》山水畫理論經典之作。何海闊在臨摹畫作時,被他的畫風氣韻,構圖筆墨,山峰雄偉,山脈氣勢,煙云縹緲所吸引,尤其是荊浩隱居太行山,自號“洪谷子”,樂在山水,每日耕種,吟詩作畫,意氣風發。這種生活狀態,讓何海闊羨慕向往。
他行走的第一站是太行山的林濾山洪谷。何海闊乘汽車、搭摩托車,到達了位于林州市的洪谷山。
洪谷也是中國山水畫家的朝圣之地,尤其是北方的山水畫家。這是一個極其隱蔽的地方,三面環山,山清水秀,景色絕妙,河水從山谷中流出,清冽可人。緣溪而上,谷幽林茂,靜如太古。山徑兩側石壁參差,有石窟佛造像,因年代久遠,造像已殘缺不全,但仍依稀可見昔時香火之旺。
北宋郭熙在《林泉高致》中寫:“太行枕華夏,而面目者林慮。”金元詩人元好問在《寶巖紀行》中寫到:“太行有谼(洪)谷,絕勝無出右。”他們稱贊太行洪谷山的絕美景色。
何海闊走進洪谷約三五里,有一巨石形成的山洞,石洞前有石碑刻曰:荊浩隱居處。他朝前跨一步撲通跪在香臺前,虔誠地行跪拜禮。
轉回頭,何海闊驚訝地發現對面的太行山酷似荊浩所繪之山水,由遠及近,左右山峰,前后錯落,極為相似,但荊浩之畫之山,峰巒兩面起,墨淡野云輕,運轉變通,不質不形,是山非似山,此山非此山。這就是畫之魂、山之魄。
何海闊望著群山,品味《匡廬圖》畫風運筆藝術的味道,那一點一橫筆墨,那一撇一捺繪畫,仿佛是隔著時空襯托與映照,隔著千年的教傳與對話。再看自己的畫作,差距在哪里?
荊浩的畫是可望可行、可游可居全景式山水畫格局,意、象、形、色融入含蓄筆墨圖式構建,絕妙之處是遠景近景,氣脈相通,看山似山,看水似水,山水相依。
然而,何海闊覺得自己功夫笨拙,畫出來的畫感覺枯燥乏味,是山的“實景圖”,毫無藝術生氣,意境氣律。
從洪谷山回來臨摹宋元諸家的山水畫,期待能在畫的臨摹中,參透讀懂,學深悟通。然而,幾年間,始終不得要領,畫太行還是覺得如隔靴搔癢,不能盡意。
其間,何海闊走遍了太行山的山山水水、溝溝壑壑,游山走山,觀山畫山,讀山泡山,從山峰俯瞰太行,從溝底仰望太行。瘋狂時,一天能爬3座高峰,行走40公里;癡迷時,獨自一人在太行山農家一住就是40多天。在山林下、小溪旁、山頂峰、絕壁間,尋找著太行山的靈魂,尋找著太行畫魂。
“從來沒有一座孤立的山、孤獨的山峰,有的我能看見,更多的是我看不見的,但山山相連,系系相通。”
后來,何海闊悟出了這個道理,但是想把這種理解和領悟變為一幅高深回環、大山堂堂、氣勢恢弘的畫卷,總覺得讀不懂的山,參不透的道,畫不像的畫啊!
那個階段,何海闊陷入了藝術盲洞,像太行山一個深不見底、走不到頭的巖洞,空曠巖洞,漆黑如墨,沒有一絲光亮,辨不清方向,找不到出口,與其在這里苦熬等待藝術的死亡,倒不如掙脫枷鎖,爬出巖洞尋找光亮。
在那些為畫畫癡迷的日子里,他為了去中國美術館看畫展,時常連夜扒上火車去北京,那個時候他什么也沒有,唯有一腔熱情。兜里就揣幾十元錢,一個煎餅果子,在美術館一待一整天,被困過北京站,睡過長安街,寒冬酷暑,沒覺苦過,內心總是激蕩著莫名的喜悅和亢奮。
何海闊憑借機緣說服單位領導到中國美術學院進修深造。
這座美麗的學院坐落在杭州的西子湖畔,這是藝術的世界,藝術的天堂,在這里,何海闊如饑似渴地學習,學習理論,臨摹名作,潛心研究。他研讀了《中國山水畫史》《極品山水——中國古代山水畫論及畫法圖釋》《畫引》《奚鐵生山水樹石畫法》《筆法記》《林泉高致》等大量書籍。
讀《畫筌》時,何海闊從總論“山川氣象,以渾為宗;林巒交割,以清為法”,到論山水關系的“山脈之通,按其水境;水道之達,理其山形”, 他含淚而讀,激動不已,仿佛又走進太行山,感受太行山的氣象豪氣和山脈雄壯。
讀《林泉高致》山水訓篇,尤其是精辟敘述,“謂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畫凡至此,皆入妙品”。品評山水畫,漫步山水間,登高望遠、寄心暢游、足以安居,有這樣的境界,皆山水畫精品。
合上書本,何海闊閉上雙眼,從氣、韻、思、景、筆、墨等方面,品味書畫理論描述的真諦,尋找山水畫的靈魂。
為了尋求山水畫之魂,何海闊到杭州附近的莫干山體驗生活,這是他第一次踏足于南方的山,莫干山的山水清秀,草木蔥蘢,花正盛開,姹紫嫣紅,處處都彌漫著濃郁的詩意,他坐在山巔,凝望著廣袤的綠色山脈,云霧繚繞的風景,清澈溪溪的瀑布,靈感如泉,思緒萬千。
何海闊覺得南方的山過于清秀和矯情,總感覺自己的畫風和性格與南方的山,尤其像莫干山這樣的山,有一種心理上和視覺上的差距,相比較他更喜歡恢宏大氣、壯美雄壯的太行山。這或許是北方的畫家的共同感受吧!
從莫干山回到美院,何海闊開始臨摹,從宋人小品開始,然后是宋元的十幾張大畫,包括范寬的《溪山行旅圖》、郭熙的《早春圖》、王蒙的《青卞隱居圖》、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等等。模本都是日本二玄社印刷的高仿真作品。
當時班上都是全國各地來的畫家,有大學教授,有畫院院長,年齡大的都70多歲了。
老師講,不管你以前畫得怎么樣,有多大名氣,來這里就得放下你過去的東西,老老實實臨摹、踏踏實實練功。
何海闊納言敏思,勤奮好學,每次集體評畫,他拿出的作品都能讓人眼前一亮,畫面都有新的感受和內容,形式和筆墨也在不斷地變化和進步中。
有一位同學用了10天時間,臨摹了一張《富春山居》,自以為臨摹得惟妙惟肖、形象逼真,興沖沖地拿給老師指導,老師瞄了一眼,微笑著地說:“你臨摹得筆法,沒有一處正確,沉下心、好好用心臨摹吧!”
何海闊就在現場,覺得自己臉上發燙,他知道,自己有時臨摹浮躁,難以靜心。于是,他下決心一筆一劃臨摹,一絲不茍讀畫,一天天盯著一幅幅名畫,臨摹了大量的傳統經典,從宋元到明清,正本清源,諸家筆墨,心無旁騖,默默地讀,靜靜地思考。晚上,他細心揣摩,勤于摹寫,太晚就睡在臨摹室,夜深人靜時與先輩名家面對面交流,隔時空討教,研究名家的筆法,貼近原作臨摹,接近思想思考,琢磨精髓用筆,有時一張畫畫一兩個月,不吝精力筆墨,反復磨練,直到皴擦到位、筆墨精準,自己滿意才算罷休。
臨摹太久,何海闊總覺得臨摹名家名畫,永遠不會超越藝術造詣,也永遠成不了名家,可以學筆墨用色,畫風畫勢,可以形似,但不能神似,畫山畫骨畫不出魂啊!
一次中國美院老師帶同學到上海看藏畫展覽。從第一個展廳開始,按順序宋元明清,名家大師,驚世名畫,應有盡有,全是精品真跡。
何海闊很是激動,一件作品得全神貫注地駐足觀看,認真揣摩,仔細端詳,從立意布局到著墨運筆,從邏輯構思到筆畫構置,看著看著,腦袋“轟”的一下,突然開竅,豁然開朗,有一種醍醐灌頂的感覺,他看到了中國畫發展的那條主脈,像一條河從古到今流淌過來,歷經朝代更迭,時空打磨,形成了一脈相承的中國文化精神。
展廳里那一幅幅畫仿佛有了靈魂,他分明看見畫面背后的那一位位畫者,靜靜地與他交流,畫面里那種高貴典雅、純凈出塵、悠然自在的氣息籠罩著他,兩眼發光,渾身通透。
中國畫的內核是中國哲學思想,是中國文人理想化的生命狀態。畫只是作者品節、學問、胸襟、境遇等綜合修為的載體,傳達那種不可言說的道。
以一管之筆,擬太虛之體,應目會心,畫萬事萬物,融萬趣神思。畫的不是此山此水,而是畫者的學識思想和世界人生,追求的是景外之意,話外之音,意外之妙。
要想真正畫好山水畫,就得深入到自然山川中,不為世俗干擾,認真觀察,細致體驗,游藝于心術精神之間,這樣的山水畫,才能“得山之骨,與山傳神”“畫山畫水更畫魂”。
畫魂太行
“外師造化,中得心源。”
唐代理論家道出了中國畫寫意的真諦,成為千百年來中國畫創作的準則。
杭州學習結束,回來以后重新面對太行。
如何參古酌今,予以心意,提煉出屬于自己的畫語和畫風表達,創作出屬于太行山的作品,他一直在探尋,在行走,在畫,在思考,在與太行山對話。
何海闊喜歡晚上看太行山,尤其經過沉淀和深思之后,他把夜晚太行、遠處黛色平移在畫板上,把影影綽綽、重重疊疊的山峰山脈山脊山谷,用畫筆表達出來;他把一石一木、一花一草、一丘一壑的山的細節和微妙,用畫風表現出來;只是畫板上的太行,多了一些色彩、多了一些靈動、多了一些生命存在,有一種體味造化、生活氣味貫穿于其中。
何海闊用心創作的《南太行看山》的山水畫,生動展現于此,從海闊的筆墨中,遠觀則博大壯美,近看則精微細致。用高遠的這種構圖,突出山峰的險峻巍峨,畫出了山峰氣勢、山脈磅礴,高大雄偉、逶迤縱橫,表現得淋漓盡致,應染盡染。
《山花爛漫》是何海闊的經典之作,入選全國畫展的畫。那是一個春暖花開日子,他背著行囊,迎著春風,從一個山頭下來,走向另一個山頭,眼觀太行,四處花香,置身其中,體味生活。
坐在太行山巔喝茶觀景,一副驚艷境色映入眼簾,他取出畫筆,一壺茶、一包煙、一碟墨、一管筆,獨坐山巔,對景寫生,眼前繁花似錦,藍天空凈如洗,喝杯小酒一臉陶醉,與山川對視,天人合一,物我兩忘,一待就是一天。
第二天,尚是如此,他手拿畫筆,像是被施了魔法,心游太行,靜看繁花,眼觀云起,筆起筆落,墨重墨淡,心中自有一瓣馨香和世界。
《山水習靜系列》是太行山的小品畫,一個人放下所有的行囊,坐在群山之間,聽山風呼嘯,看野嶺莽坡,天地洪荒,感受太行四季,春天如笑,夏日如風,秋季如畫,冬山如龍。山谷清幽,水漫過雙腳,群山無語連在夜里,鳥語琴鳴,從亂云中飛過,浩瀚夜空,寂靜世界,與山水一同呼吸,與畫者一起共鳴,如同太行的心思,如同海闊的情書。
何海闊獨自沉醉其中,像鉆進了山的抒情詩里,撂倒自己,枕著山的野風、山的景色、藍天白云釀成最美的畫夢。
那一刻,他仿佛自己成了一張畫,一張有生命、有靈魂、有情感的太行山水畫。
蘇軾說“山水以清雄其富,變態無窮難”,畫家必須走入真山真水,懂得山水之魂。
何海闊的《山水習靜系列》,就是太行山的“神與物化”相融,他獨守太行,日夕臥起其中,領略太行山川煙云風雨,感受太行山山水水,草草木木,溝溝壑壑,反復觀察,日日思考,久而久之,自然了然于胸,取之精粹。
這就是山之魂,魂之魄。
這些年,畫者何海闊先后在全國性畫展中多次入選獲獎,多次參加全國大型寫生創作活動,《野坡春暉》被中國美術館收藏,在全國山水畫界,頗有造詣,聲名鵲起。
中國藝術研究院碩士生導師、中國水墨畫院院長滿維起評價說,何海闊的作品都能讓人眼前一亮。他深居太行,靜心讀書畫畫,不為風動,不為時擾,實在是難能可貴的一種繪畫狀態。看他的畫,靜心品讀,總覺攝人心魄,如盛夏清風,沐之舒懷。
從何海闊的筆墨中,可以看出他扎實的傳統功力。他的畫大到丈許,小到盈尺,或鐵壁大壑,繁皴厚積,或田園屋舍,淡墨漫寫,都透著一種鮮活的郁勃之氣,讓人強烈感受到他對太行山的熱愛和精神領悟。
特別是他近期創作的《太行看山圖》《太行清暉》《關山記游》等幾幅大作,尤為明顯。他放棄了以前畫法中細節的描寫,放筆直取,大刀闊斧,松弛有度,用筆更為自由生辣,丘壑更顯豐富沉厚,意趣更為幽遠空凈,這些都更加準確的體現出太行的蒼茫萬象,讓人觀之精神振奮。
中國《書畫研究》主編師界弘說,最近看到他的太行山寫生,古橋流水,群峰聳立,氣象萬千。或云起如幻,或絕壁千仞,或飛泉瀑吼,或有煙火氣息撲面而來的崖上人家。雖是寫生作品,但畫面平淡中求奇險,重山復水,開合有序,繁密而疏朗;結構嚴謹,沉穩而機變,生動地傳達出太行山茂密、厚重、蒼茫、滋潤的情調氣度。
如他的作品《花溪闌珊》,運用積墨法,渲染出大壑大丘的雄渾蒼潤,突出太行的雄偉壯闊;運用皴擦點染的變化,尋找與自然節奏的契合點;運用靈動的筆法,酣暢的墨色,映襯以略施淡彩的桃花,相得益彰。海闊山水蒼古淳雅的唯美畫面,透射出的是中國傳統的“山水質有而趣靈”的山水精神。
青島畫院院長張風塘觀海闊山水畫有感曰:“氣壓太行一張紙,抖擻筆墨起風雨。”把激情揮灑、凝聚在太行山山水畫創作中,即把山的詩情畫意,思通妙悟,使筆墨姿態,美學韻致,精神氣息,用畫筆描繪而出,有形有勢,有神有韻,讓太行山有了生命、有了靈魂、有了生機。
新鄉美術家協會主席李曉雷說,何海闊癡心畫藝,大學畢業后又曾游學西湖,問道京華,交游多為當代畫壇翹楚。他的作品不求獵奇,也不囿于固定的模式,每每墨隨心動,境由筆生,以自己獨特的技法,讓宣紙承載著蒼潤厚重、沉酣蒼勁、幽深壯闊的美妙意境,讓觀眾感受到現實與心中之景相結合的山水性情,主觀的情感性靈與客觀的景物意境互相感應、交融,使其作品景真情切,狀物與抒情為一體。海闊畫里濃濃的禪意和靜氣,一如他本人身上那種疏離而又散淡的靜,著重表現山水的靈動和潤澤,山水本身的風韻,那就是何海闊山水畫的魅力所在。
太行山,從來不是一座孤立的山,有的能看見,更多的是看不見;太行山,從來沒有一個單個的人,有的遇見了,更多的沒有遇見。
太行山從古至今,雄奇壯美、氣勢磅礴、層巒疊嶂、峰險流急,造就了多少畫家,造就了多少有靈魂的畫家。
我想,何海闊是其中之一吧!
作者簡介:
董傳軍,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河南省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曾任新鄉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新鄉市文聯主席等職,現供職于新鄉市人大常委會。曾策劃宣傳過張榮鎖、耿瑞先、楊強等全國全軍重大典型。已發表新聞、散文、紀實文學等作品200多萬字。出版新聞集《走出太行》、長篇報告文學《麥者》《口罩的力量》(合著)等著作。其中,長篇報告文學《麥者》、短篇報告文學《大國口罩》分別獲河南省報告文學一、二等獎,《口罩的力量》獲中國工業文學獎長篇報告文學二等獎。
責任編輯/董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