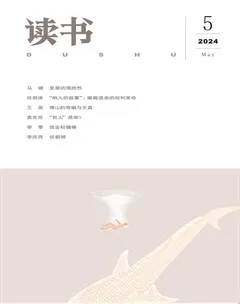“民人”是誰?
袁先欣
“人民”是現代漢語中的常用詞語。若將次序顛倒,“民人”二字,雖對今天的普通讀者稍顯陌生,對熟讀古代典籍者,應該算不上一個生僻字眼。它常常出現在皇帝或官員對臣民的稱呼中,粗略地說,也即被統治者的一個統稱。進一步,“民間”也自然意味著民人起居之處所與空間。
不過,有清一代,“民人”一語卻發展出一些特殊的釋義和指向。大而言之,這也關聯到清代特殊的政治制度和統治方式。近年來,以北美的“新清史”研究為濫觴,研究者越來越多地注意到清代作為一個統御龐大疆域的多民族復合型帝制國家的特質。美國學者柯嬌燕(Pamela A. Crossley)曾言,清代皇權具有“共主性”(simultaneities),皇帝作為普遍、超越性的存在,也是多重人格面貌的集合體,他既是滿人的首領,也是中國的天子,還是可汗之可汗,甚至是佛教中的轉輪圣王。這些不同的面相,每一重都面對著他統治的不同區域,從而,皇權的普遍性又制造出在空間和文化上有所區分的被統治者。正是在這種多元的統治結構之下,“民”也被賦予了一種極為特殊的含義和范圍。另一位新清史的重要學者路康樂(Edward Rhoads)在追蹤滿漢畛域的歷史時,注意到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我們今天熟悉的滿漢之別,其實是在十九世紀末才真正形成的,在此之前,貫穿整個清代的核心區分其實是“但問旗民,不問滿漢”。這一觀察毋寧提示我們,在清代多重又多元的統治框架之下,“民”似乎不再是所有被統治者的統稱,而成為其中某一部分的特指名稱。
那么,有清一代,“民人”到底是誰?界定清代的“民”或“民人”的,首先是“旗民分治”的制度。“旗民分治”是維系清代統治的核心,作為其結果,旗人和民人成為清代社會成員的基本分野。在今天的學術研究地圖中,八旗的歷史,以及旗人身份的界定與構成獲得了大量關注,相形之下,“民人”則似乎成了一個不言自明的范疇:排除掉旗人,剩下的皆為民人。然而,考慮到清代治下的廣大版圖和多元族群,“民人”真的就是“旗人”之外的所有人嗎?
從語言的角度來看,清代文獻中的“民人”,對應的是滿語 irgen。根據王鐘翰等學者的研究,在早期滿語中,irgen是一個較為寬泛的概念,指“百姓”“屬民”之意。這個詞既可指與女真貴族相對的平民、自由民,也可指女真新降伏的漢人屬民,有時也用來指稱其他政權如明朝、朝鮮的屬民。在滿人入關后,隨著“旗民分治”制度的建立和成熟,旗人與不隸旗籍的民人,在基層行政管理、生產生活居住地、入仕途徑與官員職缺等不同方面,都有了分別。由于“旗民分治”制度創設的基本出發點,是要應對入關后新增廣土眾民的同時,維系“首崇滿洲”的國家根本,與旗人相對的民人,因此很大程度上就與原明朝治下、沿襲了明代省府州縣之制的漢人群體重合。從這個角度來看,現有關于旗民分治或旗民關系的研究往往在滿/漢的框架內來展開討論,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滿語學者長山注意到,至清代中期,滿文irgen已經具有了“漢人”之意,這也表明,至遲于康熙朝,“民人”已經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族群性的色彩。但這里仍然有一個尚未觸及的問題:irgen或“民人”是如何從百姓、屬民的原始釋義,逐步與“漢人”聯系起來的呢?在滿漢之外的其他群體,是否也可被稱為“民人”?
翻閱《清實錄》《清會典》等史料,我們可以發現,清代前中期,“民人”逐步從普遍的百姓、屬民之意開始縮小到某一具體群體,這一過程不僅是通過區分旗民,而且也經由民人與蒙古、苗、番等群體的區分。如康熙五十一年五月諭中說:“山東民人,往來口外耕地者,多至十萬余……不互相對閱查明,將來俱為蒙古矣。”順治十五年三月諭:“今念貴州等處,民苗雜處……爾等帥領大軍,經過府州縣及土司蠻峒等處地方,當嚴行約束官兵,凡良民苗蠻財物,及一草一木,毋得擅取。”康熙五十年的實錄也記錄了四川番人羅都等“搶奪民人妻子,會集番人,拒敵官兵,殺死參將周玉麟”的案件。
民人與旗人、蒙古、苗、番等群體的區分,當然使得“民人”越來越清晰地與漢人關聯在一起,但值得注意的是,將民人區別于蒙古、苗、番的依據,并非各異的族群特質,而是統治方式上的不同。清代針對其治下的不同區域和不同群體,設置了互相隔離的多樣性統治方案,如旗人統歸八旗,蒙古隸盟旗札薩克,民人屬省府州縣,西南苗蠻轄于土司土官,各自對應不同的制度法令,不可混淆。“民人”因此更多的是因應于管理和法律上的分類。同時,這一分類一定程度上又與固定的空間區域相關聯,“民人”與“漢人”的對應關系從而更多的是經由某一空間區域(原明朝統治下的省府州縣之地)而非血緣或文化來確立的。
如果說隨著清代多元統治格局的建立,“民人”逐步經由府州縣制而與“漢人”關聯在一起,那么清代前中期同樣可以觀察到,在另一些場合,“民人”或“民間”仍然維持了其“屬民”“百姓”的原始釋義。康熙二十四年要求俄羅斯人撤出雅克薩時說:“前屢經遣人移文,命爾等撤回人眾,以逋逃歸我。數年不報,反深入內地,縱掠民間子女,搆亂不休。”這里俄羅斯劫掠的,當然不是關內漢人,而是雅克薩附近的中國各族居民。
隨著康雍乾三朝相繼收服外蒙、套西、青海蒙古各部和西藏、新疆,在南方平定三藩、收復臺灣,大行改土歸流,至乾隆中期,清廷的控制領域和疆土達至巔峰。新歸附的西北邊疆向無省府州縣之建制,亦少見漢人居民,在涉及這些地區時,“民人”往往指向籠統的臣屬關系,而不定于某一特殊的族群或統治模式。如《實錄》記康熙五十九年平定西藏,定西將軍噶爾弼所上疏奏中說:“次日進取墨竹工喀,賞賚第巴頭目,安輯民人。”又錄在西藏當地之宣示,其中有“圣主拯救西藏民人”。這里的“民人”顯然指藏民。雍正十年諭中也有:“朕聞西寧北川口外白塔地方,出產石煤,系附近漢土番回民人,挖取販賣,以為生計。”“民人”成為包容了該地漢土番回不同人群的概稱。乾隆三十二年,大臣阿桂奏稱,喀什噶爾回民交易哈薩克牲畜,欲行禁止并扣留貨物。乾隆回復:“回子系朕臣仆,即與內地民人相等。今民人各處貿易,獲利豐盈,生計饒裕,豈不甚善。……總之伊犁回子,俱隸版圖,大臣辦事,務持大體,不可存畛域之見。”(《乾隆實錄》卷七七七,一三)雍正要求湖南桑植保靖改土歸流諭中也說:“朕撫有四海,內地苗疆,皆朕版圖,漢土民人,皆朕赤子。”在此,將不同人群納入“民人”,更多地展現出清代帝王增強對其臣屬土地人民控制的愿望。
隨著清帝的武功開拓,納入“民人”同樣指示著某種親緣性的統屬關系。乾隆年間修撰的《皇清職貢圖》,其漢文圖說將伊犁厄魯特、哈薩克、布魯特三部之屬民稱“民人”(滿文圖說中,哈薩克、布魯特部均有irgen字樣,厄魯特相關段落則只稱部落名ulet)。拔達克山、安集延、安西廳哈密稱“回民”,滿文圖說作hoise irgen,而烏什、庫車、阿克蘇、伊犁塔勒奇、察罕烏蘇等僅稱“回人”,滿文圖說中無irgen字樣。《皇清職貢圖》開始修撰時,準噶爾部及其轄下回疆、伊犁周邊尚未納入清朝版圖,繪入厄魯特部顯然是為了夸耀平定準噶爾之功。哈薩克、布魯特、拔達克山等則在第二次平定準噶爾的過程中相繼主動投附,盡管按照乾隆朝《大清會典》規定,這些部落屬于“外藩朝貢”,與承擔賦稅輸役的哈密回民迥然有別,繪制者選擇以“民”或“irgen”來對之加以稱呼,實際上是為了顯示嘉獎,而并非指對其實際控制已經與哈密乃至內地民人一樣。
如此看來,我們或者可以這樣說,“民人”經清代中前期的發展,逐步形成了一個雙重性的釋義結構。在宏觀的層面上,它是清朝皇帝對其子民的泛稱,尤其在面對外國或新入版籍之地區,此時一體視為“民人”,是為了彰顯其“一視同仁”的帝制意識形態。同時,在清代的統治格局內部,所謂的“一視同仁”并非通過行政和法律制度來實現,而是以區隔為前提設置了“各安其宜”的多樣治理模式,在這一框架下,“民人”往往指不在八旗、蒙古、回部、土司土官等制度下,而直接受省府州縣管轄之人。長山注意到康熙朝所編滿文辭書《御制清文鑒》中有關irgen的詞條有二,一泛指天下之人,二指漢人,或可與此對應。這也正是清代特殊的統治秩序的體現。
清朝皇帝中,對此種雙重性的統治秩序最有自覺的大概是乾隆。他曾多次夸耀,“朕為萬方共主,當使群生皆得其所”;“朕為天下共主,罔有內外,一體撫綏”。與此同時,又極為講究內外各部之名色分別。乾隆十四年諭曰:“蒙古漢人,同屬臣民,如有書寫之處,應稱蒙古內地,不得以蒙漢字面,混行填寫,已屢經降旨。今馬靈阿奏折,猶以夷漢二字分別名色。可見伊等全未留心。且以百余年內屬之蒙古,而目之為夷,不但其名不順,蒙古亦心有不甘。將準噶爾及金川番蠻等,又將何以稱之?”此后也多次降諭申飭,要求大臣文書中不得稱蒙古為“夷”,不可將滿洲、蒙古簡省為滿蒙、蒙漢、蒙民等語。如乾隆五十六年諭:“刑部進呈陜西省秋審情實黃冊內,蒙古旺楚克毆傷瑪寨身死一案,敘述該員外郎原報,有管理蒙民字樣。率意減省,轉至不成文理。從前各省章奏于滿洲蒙古等字,有摘用滿蒙及蒙民二字者,屢經降旨飭諭。今駐扎寧夏員外郎,系管理蒙古民人交涉事務,乃刑部輒將蒙民字樣,敘入冊內,并不留心檢點,殊屬疏忽。”
事實上,在雍正朝乃至乾隆朝前期,以夷漢來稱蒙漢關系者并不乏見。雍正八年,大將岳鐘琪奏稱“陜省延安府屬榆林、靖邊、神木三廳,管轄沿邊三十堡……現今夷漢雜居,必須大員彈壓”,雍正從之。乾隆二年,吏部等部議覆大學士管川陜總督查郎阿疏稱“陜西府谷縣麻地溝地方,為秦晉關鍵,夷漢門戶,商民雜處,最易藏奸。請添設巡檢一員”,乾隆從之。如果說,乾隆在其統治的中后期逐步強化意識,堅持不可以“夷”目之蒙古,是欲糾正漢人大臣及深受漢文化影響的滿臣心中的華夷偏見,那么他對滿洲、蒙古之名不可率意減省的堅持,毋寧是在面對已經深刻介入到清王朝日常行政運轉中的漢文書寫傳統時,刻意做出區分,堅持唯有滿蒙文字名號才是清帝國意識形態的核心。
這樣一個雙層式的理解“民人”的釋義結構,連同其對應的統治模式,在后續的歷史中留下了深遠的影響。由于清初幾代承平帶來的經濟和人口增長,大量內地居民向邊疆地區遷徙,沖擊了以區隔為基本前提的多元治理框架。前文所引康熙五十一年諭,已經提到往口外耕種之山東民人達十萬有余。康熙的處理方式是歸之于原籍管轄,飭令山東巡撫“查明年貌姓名籍貫,造冊移送稽查”,而避免直接調整蒙古當地制度。此后雍正在應對“直隸山西民人往口外種地”情形時,也沿用了康熙上述措施,在要求原籍官員監管遷移民人的同時,又于古北口等地添設同知,處理“寄居民人”事宜。定宜莊注意到理事同知這一清代獨有的官職設置與旗民分治政策之間的關系,理事同知的職能是負責旗人與民人的交涉、訴訟案件,最初設立于八旗駐防地方,后來推廣至東北、內蒙古的旗民、蒙民混居之地。事實上,清代在廣東和湖南也陸續設立了專門的“理瑤同知”,主要負責在瑤民中防奸、緝查、聽訟、化導等。如此看來,同知在清代成了一種應對族群混居或少數族群事務的靈活制度設置。與同知通判的任命相關,清代在西北和西南邊疆地區還大量設置“廳”,“廳”從而成為藩部、邊疆與內地的過渡地帶,承擔了復雜的治理功能。但總的來說,盡管同知、廳制體現了清代統治者在面對族群混雜狀況時的高妙手腕和政治技巧,同時也有邊疆向內地州府縣制的過渡色彩,其設立和存在的目的,仍是在不徹底改變多元治理框架的前提下進行局部調整和靈活應對。在這個意義上,清代持續的人群分類和多元統治模式,最終為后續不同族群形成民族意識提供了基礎。
歐立德(Mark Elliot)曾提出,依靠八旗、國語騎射等機制,清代前期已經形成了某種滿人的“族群意識”。與此相對,柯嬌燕則認為,十九世紀中期的太平天國運動才是形塑滿人身份認同的關鍵。不同族群到底在何時產生了對自身身份的自覺和認同,是一個極為復雜同時纏繞著許多爭議的話題,但可以觀察到的是,清代對于不同人群的差異化統治,一定程度上成為制造族群認同的場所—尤其在清末西來的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之下。紀若誠(Patterson Giersch)認為,十八至十九世紀遷徙到云南邊疆地區的內地居民最初并未形成超越省籍的“漢人”認同,而恰恰是云南當地官員對于民人與少數族群在管理和律法上的區別對待,催生了整體性的“漢人”意識。清末民族主義話語中甚囂塵上的“平滿漢畛域”訴求是另一個鮮明的例子。如果說如歐立德所言,滿人通過八旗、國語騎射等制度維持了有別于漢人的身份感覺,那么他們在仕途、經濟、法律上的特殊待遇,也從反方向上刺激和強化了漢人的民族意識,現代的民族主義則為這種感覺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被言說出來的語言。一九〇七年,楊度率先提出以“漢滿蒙回藏”五族來看待中國的民族構成,盡管楊度本人此時是君主立憲的支持者,“五族”之說卻在辛亥革命之后被革命黨人接過,被改造為著名的“五族共和”口號。而對比一下《皇清職貢圖》中復雜的人群分類,與新中國成立后經由民族識別最終認定的五十六個民族,此處“漢滿蒙回藏”的五族分類,明顯是有清一代滿族、蒙古、回部、西藏和民人的基本統治結構,借由二十世紀民族主義話語的重新表述。
近來的研究多注意到,中華民國在辛亥革命之后長期面臨邊疆地區的分離危機,論者多認為,這顯示建立在“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基礎上的中華民國未能繼承清王朝與其藩部之間的親密關系,或暗示以漢人為主體的新政權對這些地區的主權宣稱未能得到當地的充分支持,伴隨著作為“共主”的清帝皇權的結束,使得這些不同地區和人群可能共處于一個國家和政權下的統合力量也消失了。上述敘述中隱含著一個前提,即清是一個少數民族王朝而中華民國是漢人國家,前者的領土和人民從而難以順暢地轉化為留予后者的遺產。但需要注意的是,盡管如前所述,清代的多元統治模式制度化了其治下不同人群的差異,在十九世紀以來民族主義浪潮的席卷下,這些差異又被轉譯為不同的民族意識,有清一代“民人”的另一種理解方式的持續存在則提示我們,與此種已經受到廣泛關注的多元統治模式相對應的,不僅僅是作為“共主”的清朝皇帝,同時還有一個包容性的、總括性的“民人”概念。
汪暉曾指出,中俄雅克薩之戰后簽訂的《尼布楚條約》中,關于國界和人口管理的條款內容已經很大程度上符合了現代有關“主權”的界定,從而,大陸性帝國之間的接觸和交往,也有可能生發出某種前現代的、與主權相類似的觀念。從這個角度來看,康熙以“民人”來稱呼雅克薩周邊屬中國管轄的各族人眾,也構成了一個有意味的起始,它既是蒙古-滿洲政治和文化傳統的延續,同時預示著,伴隨近現代不斷升級的邊疆摩擦和帝國主義威脅,這一總括性的“民人”概念也將成為某種與國家主權相關聯的現代國民或公民觀念雛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