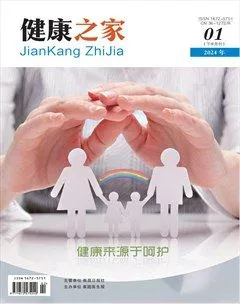滋陰養血、寧心安神法治療室性早搏
陳楠 陳曉虎
摘要:室性早搏(以下簡稱室早)是臨床常見的室性心律失常之一,病情易反復,病程多綿延,因此積極控制室早具有重要意義。中醫學根據其癥狀以及體征將歸屬于“心悸”“怔忡”等范疇,陳教授概括其病機總體屬本虛標實,虛者注重陰血兩虛,從脾腎論治;實者注重情志問題(尤重氣機郁滯),從肝入手,雙心同調;臨床治療時主張在辨證論治的基礎上,將滋陰養血、寧心安神二者貫穿其治療始終,臨床療效顯著。
關鍵詞:室性早搏;臨床經驗;陳曉虎;雙心同調
偶發的室早通常不會引起任何癥狀,因此容易被忽視。頻繁的室早可能引起心慌、胸悶、乏力、心跳停搏感、氣促、出汗、頭暈等癥狀,重者甚至影響心功能,并發阿斯綜合征。此外,因其病情易反復,病程遷延,容易產生不良情緒,如焦慮、抑郁等,從而加重患者心理負擔,同時焦慮、抑郁加重或誘發室早的反復發作,影響患者的預后。中醫論治室早注重患者身體及精神整體狀態,運用中醫學整體觀辨證論治,從多靶點、多通道治療室性早搏,較之西藥和中成藥療效顯著。因此,開發有潛力的治療室性早搏的中醫藥具有重要意義。
陳曉虎是江蘇省中醫院主任中醫師,江蘇省名老中醫學術經驗繼承指導老師。從醫30余年,博采眾長,守正創新,在治療室早方面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認為室早病程中總有陰血不足、心神不寧表現,治療上當重視肝脾腎,在辨證論治的基礎上將滋陰養血、寧心安神法貫穿始終,隨癥加減,靈活施治。
1病機認識
中醫對室早已有認識,考慮到“驚悸”字面上易解釋為因驚致悸,無法涵蓋非驚而悸,“怔忡”現又多表示此病之重證,因此現代采用心悸為病名。其病機虛實錯雜,歷代醫家多有不同見解,張仲景認為驚擾、水飲致悸[1],王清任《醫林改錯》有瘀血內阻心脈致悸之說[2]。劉完素則主張“凡五志所傷皆熱也”診治心悸病癥。朱丹溪認為驚悸怔忡主要責之血虛和痰飲[3],孫思邈有因虛致悸之說[4],隋代巢元方《諸病源候論》指出風為百病之長,心悸多風邪、虛勞所致。《景岳全書·怔忡驚恐》有陰虛及勞損致悸[5],治療以滋陰補血為主。
陳師總結其病機總屬本虛標實,本虛為臟腑之氣血陰陽虧虛,心失所養而致心悸;標實多有氣滯、瘀血、痰飲之邪等阻滯心脈,實邪擾心而發心悸;臨床中根據患者本虛之偏倚,邪實之輕重辨證論治,強調病程中總有陰血不足、心神不寧之表現,蓋因心藏神,為君主之官,心主神明的功能依賴于心之陰血充足,若陰血不足,則致心主神明功能異常,心神失去濡養,出現悸動不安,表現為心煩、失眠等。
室早通常病程綿延,日久耗傷陰血,加之多與情志相關,氣郁等日久而化火傷陰,進而耗傷陰血,終致心悸不安。心陰不足,心血失充,則心失去濡養,且心陰虛不能制約,陽氣亢逆化火,從而擾亂心神,心神不寧,而致心悸。如《景岳全書·怔忡驚恐》中言:“怔忡之病,心胸筑振動,惶惶惕惕……此證唯陰虛勞損之人乃有也”[6]。另陳師強調心悸為病,總有心中悸動不安,心神不寧的表現,其多與情志相關,焦慮、抑郁、恐懼等情志問題既是室早的病因及誘因,也是室早的重要證候及最終結果。
2治法特點
2.1 滋心陰,養心血
臨床常用煅龍骨與煅牡蠣滋心陰,養心血,另有熟地黃、麥冬、百合、當歸、阿膠、白芍等藥。此外,滋心陰、養心血時,當注重脾與腎二臟,蓋因腎,先天之本,屬陰精之根,與心同屬少陰,腎中之元陰滋養五臟六腑之陰,若腎陰不足,則致心陰虛,又有精血同源,腎虛者血虛,《景岳全書· 怔忡驚恐》述:“凡治怔忡驚恐者,雖有心脾肝腎之分,陽統乎陰,心本乎腎,……未有不因乎精”[7]。因此,滋心陰當重腎陰,臨床多用生熟地黃、菟絲子、山萸肉、全當歸、枸杞子等藥滋補腎陰,對于中老年女性,多以女貞子、墨旱蓮配伍以求補腎寧心。脾為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若脾之運化功能受損,氣血津液生化乏源,心血必不足,脾氣旺則氣血充盛,心有所養,心神得安;脾氣衰退則氣血乏源,心失所養,心神始亂。《醫學探驪·卷五》中所載“脾氣少為虛衰則悸……其氣復元,其悸自無”。故養心血當重脾氣,臨床中常用懷山藥、薏苡仁、茯苓、陳皮、白術等藥,以達健脾養心、益氣安神之功。
2.2 安其神、寧其心
《景岳全書·郁證》云:“……至若情志之郁,則總由乎心,此為郁而病也”。陳師認為,心悸為病,總有心中悸動不安,心神不寧的表現,其多與情志密切相關(尤重氣機郁滯),臨床中當重視情志與臟腑之間的聯系,主張諸情志變化之因,當首責之肝,正如《四圣心源》有“凡病之起,無不因木氣抑郁不生是以病也”。肝藏血,主疏泄,《薛氏醫案》有言:“肝氣通則心氣和,肝氣滯則心氣乏,凡心臟得病必先調肝”[8]。肝氣暢則氣機升降調順,表現為心曠神怡,同時血脈運行流利,心血充盛,滋養心神。
若肝郁氣滯則疏泄無度,氣機郁滯,心情抑郁難舒,同時血行瘀滯不利,血脈不充,故心神失養,發為心悸。臨床多以柴胡疏肝散、解郁合歡湯為基礎方酌情加減,另少佐活血藥物。同時,若氣郁日久,化火傷陰而致心神不寧,悸動不安。此類患者常表現為精神抑郁、脅肋脹痛、善太息、焦慮、煩躁不安等,臨床酌用清肝瀉火、養陰柔肝之品,如川楝子、赤芍、白芍等藥。若情志不舒日久,氣機逆亂,津液聚而成痰。則有《不居集》曰:“停積痰涎,使人有惕不寧之狀,其則心跳欲厥”。患者多急躁易怒、心煩失眠、口干口苦等,治宜清火化痰,以黃連溫膽湯加減應用。氣滯等實邪皆與情志相關,從無形之郁而致有形之邪,用藥時當從肝入手,調暢氣機為先,肝氣條達,則心之氣血調暢。
此外,以藥調其情志,屬治標未治本,雖可暫安其神,仍有復亂之嫌。因此探究患者心病之因尤為重要,此為雙心同調之根本,從根本上祛除或緩解不良情緒之源。中醫早在《黃帝內經》已經認識到心系疾病與精神心理之間的聯系,認為“心主神明”;“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心藏脈,脈舍神”;“人憂愁思慮則傷心”;“血者,神氣也”;“血脈和利,精神乃居”[9]。醫師在臨床診療中多詳細詢問病史及日常飲食睡眠、情緒狀態,鼓勵患者表達難言之隱,積極給予其心理疏導,告知積極治療預后大多良好,解答患者疑慮。如此,源既除,則心神得安,心悸自止。
3驗案舉隅
案例:患者,女,35歲,以“心慌間作兩年余”為主訴,于2023年5月26日初診。患者自訴:2年前無明顯誘因下出現心慌間作,伴頭暈不適,乏力,動則尤甚,汗多氣短,納可,夜寐欠安,易醒,無明顯口干口苦,易便秘,小便調。舌尖紅,苔薄黃,雙下肢稍水腫,勞累后明顯,胸悶氣喘偶作,納食尚可,寐欠安,二便正常。2021年10月21日查動態心電圖示:室性早搏有7582次。查超聲心動圖未見明顯異常。治療上予琥珀酸美托洛爾47.5 mg口服,未見明顯好轉,后因備孕自行停用,生產后自覺心情抑郁,煩躁難安,心慌癥狀加重。刻下:心慌間作,伴有頭暈不適,乏力口干,平素焦慮煩躁甚,納食尚可,夜寐欠安,多夢易醒,大便干,小便偏黃。查體:血壓128/76 mmHg,心率62 次/min,心臟瓣膜聽診區未聞及明顯雜音。舌質紅,苔薄黃,脈弦。中醫診斷:心悸病(痰火擾心證)。西醫診斷:室性早搏。治宜清火化痰,寧心安神。處方:黃芪15 g,當歸10 g,五味子6 g,麥冬10 g,茯苓15 g,紫草20 g,甘松10 g,豬苓15 g ,防風6 g,丹參20 g,生地黃10 g,黃連5 g,肉桂2 g,陳皮6 g,炒白芍10 g,桂枝4 g,甘草3 g ,浮小麥15 g,黃芩12 g,益母草15 g。14劑,每日1劑,水分煎服。同時安撫患者焦慮、恐懼等不良情緒,通俗語言向患者耐心解釋病情相關病因病機,詳細回答患者疑問,告知室早經積極治療一般預后良好,囑咐其放松心情,可用心理暗示方法減輕焦慮。
2023年6月13日二診,患者自訴:心慌發作較前減少,多于情緒激動時誘發,頭暈好轉,焦慮煩躁較前緩解,仍有乏力、自汗盜汗等不適,納可,夜寐欠安,多夢易醒,二便調。治法以益氣滋陰養血、寧心安神為主,去丹參、豬苓、茯苓、桂枝、甘草、炒白芍、浮小麥、黃芩、益母草,加熟地黃、山萸肉10 g茯神、女貞子、墨旱蓮以補肝腎,加強滋陰養血之功,茯神、酸棗仁改善睡眠,繼服14劑,再次加予心理疏導并多次電話隨訪。
2023年6月27日三診,患者自訴:心慌程度較前明顯減輕,頭暈乏力等不適較前改善,納寐可,二便正常。囑咐原方繼服14劑。
后定期至門診復診,2023年9月29日復查動態心電圖提示:室性早搏1728個。患者自訴:心慌明顯好轉,頭暈乏力好轉,心情較前暢達。繼予原方口服。
按:患者是青年女性,無明顯誘因出現心悸時作,長期不愈,心生恐懼,煩躁不安,行心臟超聲檢查未見明顯器質性心臟病,服西藥治療后效果欠佳。后又值生育,情感變化較大,情緒易激,煩躁難安,心情抑郁,結合患者臨床表現和舌苔脈象,認為患者的病機以陰血不足為本,痰火擾心為標,治以清火化痰,寧心安神為主,輔以滋陰養血。方中黃芪與當歸合用補血養血,麥冬養陰生津,茯苓健脾和中,五味子補腎安神,陳皮理氣;生地黃、浮小麥、黃芩與黃連配伍使用,以清心火、養陰除煩,緩解患者焦慮、煩躁等情緒問題;黃連、肉桂交通心腎,白芍斂汗,患者哺乳期,加益母草調經。現代藥理學證實,甘松、紫草具有抗心律失常作用,加用此二味藥以增強全方寧心定悸之效。二診時患者痰火擾心癥狀已明顯緩解,而以心陰血不足為主,故去清火化痰之品,加熟地黃,女貞子,墨旱蓮等補肝腎、滋陰養血,旨在安神定悸、改善睡眠、緩解焦慮[10]。
4 結束語
陳教授結合多年臨床經驗,在臨床治療室早的過程中辨證論治、病癥結合,注重脾腎二臟以滋心陰、養心血,注重中藥調理與心理疏導相結合以寧其心、安其神,將此二者貫穿室早治療始終,以期達到減輕癥狀、減少室早復發。謹守病機,靈活施治,臨床應用療效確切。
參考文獻
[1]張機.上海中醫學院傷寒溫病教研組(校注).傷寒論[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23,35.
[2]王清任.醫林改錯[M].上海:上海衛生出版社,1956:27.
[3]朱震亨.丹溪心法[M].北京:中國書店,1986:259.
[4]孫思邈.千金方[M].劉更生(點校).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189.
[5]張介賓.景岳全書[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59:55.
[6]張伯禮,吳勉華.中醫內科學[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7:89-91.
[7]張仲景.金匱要略[M].北京:中國古籍出版社,1997:141.
[8]佚名.黃帝內經素問[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7:49.
[9]薛己.薛氏醫案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3:78.
[10]陳無擇.三因極-病證方論[M].侯如艷(校注).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11:321.